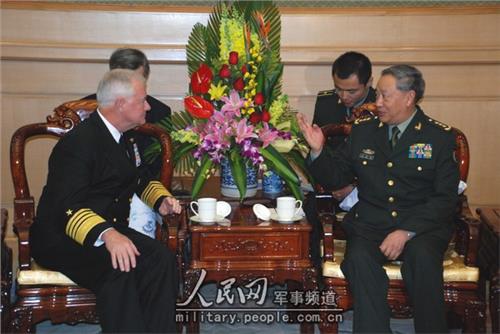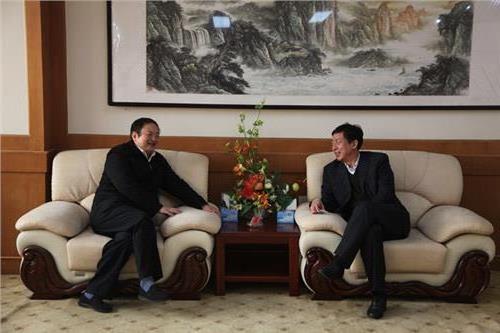余英时作品 余英时:一波三折的访美计划
本文选自《印刻文学生活志》(第十五卷第二期)。余英时先生在文中回忆了一九五〇年代他申请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曲折经历。标题为“新史学1902”所拟。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们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没有动过出国读书的念头。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进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关于这件事,宾四师曾有过一段简述,他说:

哈佛燕京社先于四十三年(编按:民国),来函邀请新亚派一年轻教师,在三十五岁以下者,哈佛访问。询之港大,并无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亚一校获此邀请。以新亚教师无年轻合格者,姑以年长者一人亦曾留学美国者,商其同意应之。

哈佛以不符条件,拒不纳。翌年又来函邀,遂以新亚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一年期满又获延长一年。又改请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师友杂忆》,全集本,页三二〇~三二一〕
钱先生所述大体正确,但细节仍不免有出入,让我藉此机会用我自己的记忆作一补充。
余英时与钱穆夫妇合影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镇雄先生奉宾四师之命,到研究所来找我。他在耶鲁大学读过书,也在新亚任教,但这时又兼任学校的英文秘书。他带来了哈佛燕京学社致新亚的全部文件,让我细读,然后决定是否愿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学进修一年。
原来哈燕社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访问学人计划”。根据这一构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韩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人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他们有听课和研究的自由而无考试的义务,一年之后仍可申请延长一年。
但访问学人在年龄上则有较明确的限制,即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可知此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中年学人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当时哈燕社每年计划招收十一、二位访问学人,多数来自日本,一两位来自南韩,香港和台湾则各有一人。(台湾最初只有台湾大学一处受到邀请,后来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师范大学两处。当然,提名并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进一歩告诉我:学校鉴于上一年的推荐因年龄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并无改变,仍是年长者过之,年少者不及,因此决定同时提名唐君毅师和我两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择。迓一年,君毅师四十六岁,我则二十五岁,恰恰是他过之,我不及,因此我虽然最后同意一试,并且为提名试写一篇很长的进修计划,但我对于去哈佛的事却未抱一丝一毫的期待。
我有两重很坚强的理由:第一、“访问学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学术研究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人,所以至少当在三十岁以上,而我当时则是大学毕业不久而刚刚开始接受研究训练的年轻学生。
第二、唐君毅师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学家,而我连一篇具有原创性的专题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如何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种荣誉和鼓励,没有再作进一歩的设想。
青年唐君毅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长叶理绥的正式公函,邀请我在秋季到哈佛访问。信中还特别注明,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况并增进英文说与写的能力,我可以提前两个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学校。这封信当然使我喜出望外,但当时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为什么能够入选?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几个月之后,才知道哈燕社的“访问学人计划”是把重心放在年轻学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们学与思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
所以我的年龄不足和学尚未成反而是这次入选的主耍原因。同时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绝了新亚的提名,这次又提名二人待选,出于对新亚特殊处境的同情与支持,他们才破例接受了我。
《现代学术季刊》创刊号
上引宾四师回忆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荐了“年长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这里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位老人便是陈伯庄先生。陈先生是和胡适、赵元任等同年(一九一一)官费留美的,他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但回国后转而在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京沪铁路局长,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难南下,定居香港。但从这时起,他的兴趣转向杜威哲学和社会科学。他一方面在新亚兼一门社会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则创办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现代学术季刊》,以研究和翻译西方最新的人文与社会思潮为主。
当时他已集中精神研读帕森斯新著《社会系统》一书。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讨论,而《现代学术季刊》也为我开了不少眼界。他因为编《季刊》的关系,很希望到美国访问,以便和各大学有关教授商讨译介新思潮之事。这是他同意新亚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与哈燕社计划不合,又兼年事过高,以致未能实现。关于这一经过,胡适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给杨联陞师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说:
新亚书院推荐的一位,我听说是陈伯庄先生。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国内做过许多大事业,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来他专心研究Dewey派的思想,读了无数的哲学书,所以想出来找些人直接讨论讨论。
他的年龄与元任同岁,我怕他不能合格。(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五五八。有关陈先生的生平与思想,可读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适的序,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杨联陞先生
杨先生与“访问学人计划”有关,胡先生特别和他讨论陈伯庄案,似有为他说项的用意。陈先生访美之愿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实现,因为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他编译新思潮丛书的计划。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畅聚了一两个月,我并且同意为他的丛书编译一部有关历史哲学的论集。可惜他回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时期对我发生过正面影响的一位前辈,所以补记于此。
从月尾开始,我积极办理去美国的法律手续,想不到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几乎不能成行。原来当时在台的国民政府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存在着一个协议,即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去美国,必须用中华民国的护照。依照这一协议,我不能不通过台湾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中请出国护照。
但台湾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员不经过任何调查,也不曾找我询问,便已秘密呈报台北政府,说我是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到美国后必将发出对台湾不利的政治言论。这样一来,我的申请便被搁置在一旁,无论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复,有如石沉大海。
宾四师后来了解到这一情况,还特别写了一封恳切的公函给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检一关不能通过,也没有发生丝毫作用。申请案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开学之后,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护照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几年虽在所谓“第三势力”刊物上写过不少文章,却从来没有一个字涉及国民党。我的作品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倡导民主自由的价值,上面已经说过了,不必再谈。
我的困局当时在香港传布得很广,最后连亚洲协会驻港代表艾维也知道。艾维很尊重宾四师,一九五二年亚洲协会出资试建新亚研究所便出自他的决定。因此他通过宾四师,传话要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在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自动地写了一封信给美国驻港总领事庄莱德(长期在台北任美国驻华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访问是一个青年学人一生难得一遇的进修机会,不应因技术性问题而丧失。
于是庄莱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个给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师,当面宣誓自己是“一个无国籍之人”,再由律师写成正式文件,签名其上,以代替护照,美国领事馆便可合法地在这一文件上签证。
这一“无国籍”的身份给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难。我每年都必须到移民局去申请延长,当时持有这一特殊身份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员每次必详细追问,并一再警告我不能离境,一离境签证便失效了。这一情况直到十几年后取得永久居民的身份才告终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