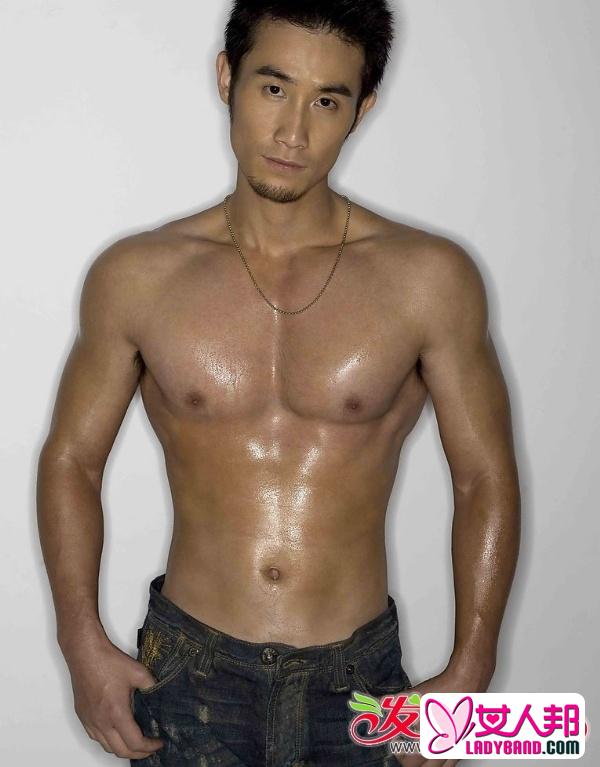无间道解析 电影《无间道》的叙事分析
刘建明恐怕是香港电影史上塑造的最耐人寻味的角色了。这样说,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复杂,更是因为他的身份困惑最终暗示了回归以后的香港一直面临的深切的文化认同危机。
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把刘建明读作关于今日香港的一个寓像。下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叙事分析,并联系香港今天的历史书写困境,来探讨《无间道》三部曲是如何改写其叙事主体的身份记忆的,以及这一改写最终是遭遇怎样的叙事难题而归于徒劳的。

一、时间/无时间 《无间道I》基本上还是一部港片。但是这样一个香港,却是以没有时间向度、失去历史背景的悬滞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除了影片开始时(英治下的)警校场景和结尾时的烈士墓地场景——我们肯定记得,这个场景是由一个从国旗、区旗、警旗摇落至陈永仁墓碑的镜头开始的——以外,我们从这部影片的画面里几乎无法捕捉它所讲述的故事的时空限定。

甚至我们不禁要抱怨,这部影片的外景实在太少,以致于不足以提供充分的信息来让我们指认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即便有了展现香港景致的机会,也是那样的千篇一律:无论黄志诚与陈永仁的接头,还是刘建明陪上司打高尔夫球,都是在摩天大厦楼顶的平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缺陷也可以视作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修辞策略,以帮助导演寻求一个更为隐蔽的身份认同——即把香港呈现为一座无名化的大都市。

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去中心的后现代城市景观更容易摆脱历史的重负呢? 这一点在《无间道》第二部(以下简称《前传》)的宣传海报上表现得更加明确:前景是黑白两道的主要人物,背景则是一片壮丽的都市丛林——我们可以称之为“香港”,也完全可以把它指认为别的什么地方。

有一篇网上评论敏锐地指出,配合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的题词,这幅海报隐含着对香港荣没今昔的无限感慨。
但是与《无间道I》不同,《前传》在影片叙事结构上的重要转变就是有意识地放置了时间的标尺,就象它的片头里所表达的那样:从“无时间”到“时间”——那些简短的字幕似乎在提醒着我们,时间才是能够改变一切的决定性因素。
细致地分析起来,不仅在情节层面上,黑帮和警局两方面的人事变迁都受到香港回归这一历史驱动程序的直接影响;而且随着镜头语言重新调整焦距,对比《无间道I》过多空旷的城市远景,《前传》则再度把更为细腻的香港街景呈现在观众面前:随之一同呈现的是这些街景中更为平常的市民生活——不管是夜宵排挡,还是粤剧票房。
随着香港回归的历史景片被重新搬演,一种抚今追昔的怀旧气息也愈见浓烈。
到了《终极无间》里,这种对于时间元素的放置和投入开始显影为一种关于叙事的真切的焦虑。在被时间或即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事实背后,人们仍然强迫症似的固执于对记忆的流连——在已成定局的现实生活中不能改变的,可以通过回忆与记忆的辨证交错来予以改变。
该片运用的倒叙、插叙的手法本身即已构成了对物理性时间的一种潜意识的抗拒,因为后者据说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而实际上,现代艺术以来,时间作为叙事主题所涉及到的正是生命意义中内在时间的延绵,任何基于这种回忆与记忆的辨证交错的历史书写都是为散落在时间坐标轴上的人和事赋予意义。于是,在一遍又一遍的重读和复写中,一些看似零乱、散漫的画面或句段被重新连缀起来,共同组成一条看似注定如此的意义锁链,以满足观众坐在电影银幕前为生活的空虚投放意义的快感。
——这至少是李心儿医生坐在她的电脑前十分专注却又漫不经心地翻看陈永仁病历时唯一能做的事。
通过这些病历,还有保存在黄警司电脑里的档案,陈永仁在牺牲之后获得了一种幽灵化的存活。而刘建明恰恰是由于这个对手的缺席在场,才尝试修订自己的身份记忆来使这幽灵附体,以期望最终改写他“没的选择”的命数。
《终极无间》的片头段落非常清楚地把电梯表现为“求出无期”的无间地狱:在那里,刘建明的人没有关在里面,可是他的身份却被永远锁在了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这部系列影片当中,《无间道I》的镜头语言通过空间化的修辞策略来取消时间向度,以期在最大程度上使香港绝对化和永恒化,从而解脱历史的重负和时代的羁绊。
而在《前传》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历史景片不仅自始至终支撑着故事的推演,而且实际上成为了暗含于影片中的主题线索。
这种从构造无时间的意象到重新投入时间元素并予以历史书写的叙事转折,在这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里则提升到了对叙事本身的反身自省的层面——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稍后的段落里再详加分析:在《终极无间》中,不是刘建明的双重人格或者他对自我身份的改写,而是叙事本身成为了主题。
二、父子恩怨还是兄弟情仇
《前传》在引入历史背景的同时,在叙事样式上也退回到一个更接近以往香港警匪片或黑帮片的类型上去了(它对《教父》的摹仿简直是一望即知——对早习惯于戏仿的香港电影来说,这一次却因为似乎真的是在临摹经典,而显得格外的尴尬、格外的失败,也格外地暗示出电影作者对于叙事的可能性的深深焦虑)。
这种类型片中,几乎必然要用浓墨重彩来渲染警匪内外的兄弟情仇。一提起这一已成套路的情节模式,恐怕第一个印入读者脑海的也是《英雄本色》吧?并非完全巧合的是,《无间道》的导演刘伟强、麦兆辉曾说过,最先给他创作灵感的就是吴宇森在美国拍摄的《变脸》——不难理解:“变脸”或是镜像式的角色分立与对映,其实都不过是兄弟情仇最极端的变奏形式罢了。
然而,香港这种警匪片中“兄弟情仇”的情节模式,实际上是对另一叙事主题即父子关系的转移、替换和遮蔽。因为父子关系一直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叙事难题,它表征的乃是香港的文化认同困境。这里没有时间做深入的探讨,但我们只需稍稍回顾一下一些香港类型片中的视觉表象,就不难同意笔者的上述观点。
在警匪片中,高鼻绿眼的最高长官总是被表现为固执、愚蠢、冥顽不灵的脸谱化形象(——在《无间道》里,只有《前传》中刘建明为升职进行面试的一个场景出现了英人面孔),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这种漫画式再现,似乎十分轻松却又略带自嘲地便打发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身份困惑;与之对应的另一情形是,在各种样式的古装片里,或者是无论天南地北一律粤语发音的对白,或者是似是而非、实在缺乏可信度的服装道具,更不用说一贯的后现代式戏仿和搅笑风格,都从客观上造成了与那个可名之曰“中国”的文化传统之间的间离效果。
——与这种“父名”的虚置相对位的,正是兄弟情仇的隐喻式修辞:通过这样的修辞,通过用这样的修辞来回避和遮掩关于一个贯穿的历史合法性的叙事难题,香港便被一劳永逸地书写为一个失去历史景深的当下了。
回到《无间道》三部曲上来,我们会发现,上述父子关系的叙事难题和兄弟情仇的策略性的解决方案,在这套系列影片的前两部中都有集中表现。《无间道I》并非没有父子故事:最具情感冲击力的场景就是陈永仁目睹恩师摔死在出租车上那一幕(当然此前他暗自敬礼目送叶校长灵车远去的场面也在传达着类似的信息);而反观刘建明,父子故事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复杂——因为不论是对黄志诚,还是对韩琛,他都犯下了弑父之罪。
到了《前传》里,这一俄底浦斯情结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刘建明是一个杀父娶母(不能忽略的是他对韩琛的女人Mary的迷恋)的俄底浦斯的话,那么陈永仁就是始终生活在父名阴影下的婴儿了——他的困境是他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社会身份,他永远无法被整合进入符号界,除非满嘴谎话,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失语者。
论及《前传》里陈永仁的父子恩怨和兄弟情仇,那个墓地接头的关键场景就值得花费些笔墨来详细地分析了。在得知黄志诚是杀死自己生身父亲的“同谋”之后,陈永仁对这位恩师的态度显得极其暧昧:因为后者帮助自己实现了弑父的梦想,却又从他这里攫取了父亲之名。
一方面,联系着他对自己亲生父兄的反叛甚至毁灭,带出的是整个影片叙事结构中对传统血亲家族的否定;另一方面,陈永仁并没有因此就真正成人,并没有就此获得他似乎应有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父亲”就是黄警司。
这就是那段对话中两个人并不投机的原因所在:黄志诚关心的是他们父子般的私人感情是否会受损害,所以才会问道:“为什么你还肯帮我?”;而陈永仁一心要索取的是本来就该属于他的那个社会身份——“我是警察。”接下来,陈永仁半开玩笑地再次发出弑父的威胁:“那我就宰了你!”黄志诚则回答:“那就好了,债就还清了。”
这一场景中的有趣之处还远不止于此。《前传》里明显增加了戏份的黄志诚还不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父亲,这个角色还处于另一组兄弟情仇的关系之中。在这部影片里,最煽情的段落变成了他目睹陆启昌被炸身死的那一场戏——于是,在陆启昌的墓碑前,就形成了一个交织、重叠的父子与兄弟关系网(这其中当然还要包括另外那位牺牲的罗姓卧底和站在远处汽车旁的叶校长)。
再有,黄志诚与韩琛的复杂关系也构成了对陈永仁和刘建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微妙的复沓——需要提示一句的是:他俩还联手上演了一幕杀子(倪永孝)的好戏。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父子恩怨始终是叠印在兄弟情仇之中的——这种繁复的情节构图,归根结底,还是导源于香港文化认同中父名的虚置造成的叙事难题。正是因为一个确凿的父亲形象实在难于指认,而那种父亲的阉割力却因无名化而更加的无所不在,所以除了通过手足之情来涂抹、改写或套编父子故事以外,的确再难想象能有什么更好的求解方案了。
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一场景的起笔和收笔都是迎风飘扬的英国国旗,那么上面的读解就不应该被指责为“过度诠释”了吧?——其实,父子关系经常在叙事艺术中充当历史转义的修辞功能。但是,只有在香港这样特殊的地方,因为先后由殖民历史和冷战格局造成对自我身份的创伤性经验、以及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危机,作为历史转义的父子恩怨才会在极大程度上服从于兄弟情仇的情节模式,以把无法接续的历史干脆表现为断裂的当下。
在后来的《终极无间》里,我们还会看到,这种手足之情是如何被用来暗喻回归以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的。杨锦荣和沈澄(“影子”)之间的兄弟情谊,以及这份兄弟情谊所表征的粤港合作,其实是在运用一种对等而非从属的图示来改写香港回归中国的事实。
三、精神分析与叙事的可能
“被遗忘的时光”这首主题歌,真的是把时间和记忆的主题贯穿在《无间道》三部曲的始终了。然而,这首歌并不是画外声源的怀旧氛围的点染,而是内在于故事情节的具有戏剧动作性的构成元素——毋宁说,它在时间、记忆甚至怀旧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主题的原型:即改写。
先是在《无间道I》里,陈永仁把刘建明与韩琛密谈的录音刻录在这首歌的光盘里面,送给他的妻子Mary;而到了《终极无间》里,杨锦荣则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方法让刘建明原形毕露。
实际上,在《终极无间》里,改写这一主题以多种变奏形式出现。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再是改写的内容,而是改写——更准确说,是叙事本身。因为改写身份记忆之于刘建明,就和写报告之于杨锦荣、精神分析之于李心儿一样,都是对叙事行为本质的疑虑和探询。
最为有趣的一场戏,是李心儿医生对着她的两个病人——陈永仁和刘建明——述说,她曾经如何通过改写记忆,来退避自己犯下过错之后的羞耻感;然后,她特意解释道,这种被压抑的记忆(“被遗忘的时光”)只要能够讲出来,就可以得到抒解。
这段精神分析的自我倾诉,其实正好表征了这部影片关于叙事的自反性的思考。因为对于刘建明而言,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他的问题绝无可能凭借倾诉得到解决。就决定他生命历程的那些事来说,一旦做出选择——象韩琛最开始所说的那样:“你们自己选啦!”——就注定要“没的选择”。对刘建明来说,叙事对时间(或者所谓“命数”)的抗拒仍然是作为一个问题,而远非答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刘建明竭力改写自我身份当然是《终极无间》的情节主线:他从镜子中看到的自我形象是陈永仁,而他向李心儿许诺要亲手逮捕的刘建明却被投射到了杨锦荣的身上。但是,刘建明对自己身份、对真实自我的困惑,在《前传》中就已确定:在向倪家告密说Mary是杀死倪父的幕后真凶之后,他以一种迷茫而疑惧的目光紧紧盯着反光镜里自己卑鄙的模样。
如果说在这套三部曲的前两部影片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刘建明这个人物的刻画——对他的人格究竟怎样得以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追索;那么到了《终极无间》里,他的身份、他的真实的自我其实已无悬念,导演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他对自己这一身份、这一自我的徒劳的改写过程。
(应该承认,杨锦荣和沈澄这两个新的人物的加入,在编剧技巧上构成了置换前一个悬念的新的悬念,他们两人身份的可疑促成了观影快感的新一轮延宕,好象不到最后的高潮段落这一谜底不能真的揭破。
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很早就已“暴露”给观众了:当刘建明第一次潜入保安部安装监视器时,楼道里就响起了腿已瘸了的沈澄特有的脚步声;至于杨锦荣,更是从他刚一出场的一个画面里,就可证明后面他主持的那次粤港合作确凿可信——当画框外的陈俊用枪指着他的头时,杨锦荣身后窗外的海面上,正缓缓驶过一艘货轮,上面标写着“CHINA SHIPPING LINE”的字样。
)
由李心儿的精神分析所提示的叙事本身的可能性,在刘建明那里实在很难成立。他也并非没有倾诉,他把自己“是韩琛的人”这一事实告诉了李心儿——但是这无济于事。并不是所有创伤都能够通过修订记忆来抚平的,并不是所有事实仅仅通过叙事就能变得顺理成章。
讲述或者倾诉确乎能实现一种想象性的解决;然而同时,这种解决也必然提供真实以一种再现性的呈现。这不仅是刘建明的困境,毋宁说这其实正是精神分析自身的困境——一种关于叙事模式的困境。
精神分析作为临床实践,端赖对话双方的主体间关系,倾诉不过是转移了症候,使之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显影。对于刘建明来说,不幸的是,那个与之对话的另一主体、那个曾有可能指引他进入符号界的他者(“mOther”)已经死去——那就是韩琛的女人Mary;他曾经找到另一个Mary来维系那种想象性的主体间关系,而本人即精神分析医师的李心儿扮演的只是那个他者的最后一个替身。
正是这个他者的缺席把他的自我永远地冻结在了那个反光镜映照出的躯壳里:不是别人,而正是刘建明自己害死了Mary。——在想象界与符号界之间不可弥合的断裂处,即有无间地狱。
当你的倾听者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当你的倾诉因那个对象的缺席而无法得到反馈,当你失去了那个对话的另一主体——准确说,失去了那个在符号界不断借他人的躯壳而显灵的他者,那么你的想象就永远不能应合于符号秩序,永远不能获得一个为这一秩序所认可的社会身份,你的匮乏的自我就不能从对话过程所实现的身份指认中得到任何补偿。
——这何止是刘建明这个人物的困境?他对自己身份记忆的徒劳的改写,难道不正暗喻着身处香港文化认同危机之中的电影作者所面临的主体位置的两难选择?对于这部影片的叙事者来说,他们的倾听者、他们的对话对象、他们的观众究竟是谁——香港,还是中国?就香港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论,中国显然不是那个适当的人选;但与此同时,中国毫无疑问又扮演着最重要的他者形象。
在香港与中国之间,就是想象界与符号界断裂的地方,就是只有“必是非常潜能”的主体才能游走其中的无间道。
逢此历史际遇,对于作为香港文化认同最主要载体的电影生产,叙事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这是《终极无间》提出给影片自身的难题,其困扰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也显现在影片的体征上。
那个精神分析的诊疗室,确乎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主体/自我/他者所构成的叙事自反的场景。这一场戏里,尤其令人疑惑的,是陈永仁和刘建明共同分享着李心儿的催眠的那个画面。这当然是一个想象性的场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那究竟出自谁的想象?是李心儿面对刘建明时,脑海里仍然时刻浮现着陈永仁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还是刘建明希望通过陈永仁的幽灵在自己身上附体,来改写他的自我、改写他的身份记忆?他把陈永仁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的确是贯穿整个影片的情节线索;然而从镜头语言上,我们很难相信上述场景会是出自刘建明的想象,因为他和陈永仁始终分享着画面空间,也即分享着意义空间。
这和整部影片的基本配置是相一致的:刘建明和陈永仁都是被叙客体。
从李心儿的角度上,这种含混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这一叙事段落是以她对陈永仁的回忆开始、也是以她对陈永仁的回忆结束的——特别是最后,黑白画面(陈永仁说:“过了今天就没事了。”)直接转而为彩色画面,(李心儿的)心理空间直接转换为(以陈永仁为行动主体的)故事层面,这表明李心儿的视角参与了影片的叙事,特别是主导着这一段落的叙事。
但另一方面,刘建明和陈永仁所共享的画面却不是由李心儿的视点提供的——镜头从门外进入(这是一个瞬间的画框构图),越过李心儿的头顶,推进到陈永仁和刘建明的双人中景,这显然是真正的影片叙事者的视点。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场景里在李心儿和她的病人之间没有形成任何真正的对切镜头——换言之,李心儿和刘建明都是在对着想象中的对象自说自话,他们彼此都不是对方的适当的对话人选。
至于陈永仁,尽管他显然从未成为影片内的叙事者,但他始终是叙事和镜头的焦点,许多段落都是由聚焦于他这个人物的怀旧式目光开始的。
一个有趣的段落是,在接受诊疗期间的无数次插科打诨之后,黑画面上先出现“第……次见面”的字幕,然后亮起定格画面,稍停,画面开始运动,陈永仁与李心儿热吻——这样的剪辑(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改写也即叙事手段)把这一场景完全处理成了想象。但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谁的想象?陈永仁,还是叙事者?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终极无间》的导演所面临的根本的叙事困境,是他无法找到切入影片内部的叙事视点。他无法真正地认同于剧情中的行动者(无论是刘建明还是陈永仁),也不能附身于故事中的旁观者(李心儿)——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他的主体位置的悬而未决造成的。
他或可游弋于这三个人物所能提供的视点之间,但是他绝无可能弥合横亘于叙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那道裂隙,因为恰恰是回忆本身阻断了任何的这样一种认同关系,也就从根本上阻断了插叙、倒叙等叙事手法和隐藏起摄影机位置的流畅剪辑之间暗相契合的真正可能。
就象刘建明之于陈永仁一样,叙事主体不过是叙事客体的幸存者,是他的幽灵似的存在,是被那个或曾真正拥有的理想自我所放逐的主体。
就象已经逝去的香港一样,它的过眼浮华并不是今天的香港真正恰当的追忆对象,那种怀旧、那首“被遗忘的时光”只会一而再地提醒:那个历史断裂将会永远内在于香港的身份记忆之中,那个叙事困境仍然不可免除,任何试图弥平这一创伤的书写,都只能重新唤起那份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