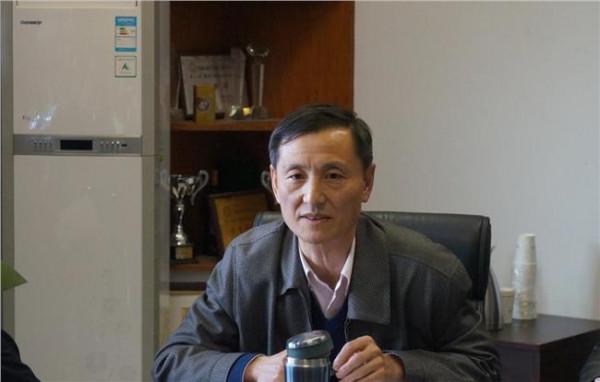巫鸿空间的美术史 评巫鸿2016年度系列讲座“空间的美术史”
作为术语的“空间”在美术史研究中非常广泛,传统美术史研究中的任何一条线索、方法、类型都需要用到。讨论一张画的空间构造与讨论雕塑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差异?器物的装饰纹样与其形制所占据的现实空间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存在于不同美术史类别中的“空间”概念,是否真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美术史学在“空间”概念问题上讨论得极为丰富激烈,造就了自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创作中针对空间关系的发问逐步取代了对于单件作品的关注与阐释。
究其原因,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论述为“19世纪之后的科技大爆炸”所带来的交通、通讯的便利,使得人类对于空间的体验愈发理念化、对象化,人(主体)与空间的关系是逐步剥离的。
曾经远隔重洋、山川横亘的空间阻隔被新式工具瞬间抹去。面对这些现象,巫鸿先生认为,美术史家若整合出一种空间观,把美术史研究从孤立对象扩展到图像之间、作品之间、多个空间之间的关系上来,就能打通美术史研究的内外之别、文化之别。讲座虽分三课,断然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空间与图像、物、总体艺术的关系。
处理完艺术作品空间的内外问题后,巫鸿先生在第三讲《空间与总体艺术》中借用第一讲抛出的“层叠、层累”的方法,把前文提及的视觉(物质)空间、知觉(图像)空间、经验空间整合,三者层层叠加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想象的、集成的大空间感,就是他提出的“总体空间”。
较之前两讲宏大的艺术作品内外和美术史两条线索的精彩双重奏,巫鸿先生并没有处理好如何把塔拉汉多夫、瓦格纳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观念移植到空间方法体系中所需要解决的“主体问题”。
他在本讲中,依然引用三个重要墓葬作为分析案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北保定刘胜墓、河北张家口张文藻夫妇墓。每个墓葬都引申出六个有关总体空间的议题。但是,有几个要紧问题,尚未“总体化地”整合在一起。
例如:层累机制的使用契机;艺术作品如何与所处空间发生关系,共同营造专属的文化功能;历经岁月之后,艺术如何连接起当下与过去,向研究者敞开两个时空。瓦格纳很明确总体艺术发生在剧场空间内,二战后经由博伊斯、黑山学院的努力,当代艺术已扩展到社会空间,换言之,他们把社会总体艺术化了,但终归总体艺术是针对当下的。
若空间的美术史研究借用总体艺术概念延伸下去,一种迷醉,一种被定义为人类制作艺术的本源冲动将弥散在空间中。原本,这种迷醉是被艺术作品包裹着的。依巫鸿先生的思路,需要对空间的主体边界再次定义,实质要处理的是文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问题。
作为具有大艺术、大历史视野和格局的学者,巫鸿先生当然意识到了以总体概念嫁接进入空间方法体系某些未尽如人意之处,如同他总结的图像学、符号学弊端一样。因此他在讲座内容完毕后又一次继续展开,提到了未来完善空间美术史方法的路径:结构主义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学界显学,生发出强大的文本概念和作品概念,与之相关的“语境”(context)概念成为了理解作品与社会整体关系的纽带;后结构主义的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引入符号学中发送与接收信息的媒介化叙述模型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议题也纳入其中。
看起来,美术史研究早已建构起类似“总体化”的研究范式,但无所不包的作品概念使得我们对待“作品”总是把它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妄图对作品内部的解读建设出完整的世界。
古人对待今人所理解的艺术并没有如此结构主义式的作品意识。对于今人而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称之为作品,地下的墓葬可以理解成作品,地上的陵园也能理解成作品,甚至同一时期的多个陵园或建筑形成的空间布局也能纳入作品的范畴。
可在古人那里,这就是礼器、宗庙、秩序的显现。模糊缥缈的“总体”建设中会形成一种缺乏约束力的空间意识,在巫鸿先生的工作内,空间的大小主次是主体思辨的首要问题。
他也在问:什么是敦煌艺术?如果仅是莫高窟的佛教绘画和造像,那些世俗题材的壁画是如何在总体空间中生发意义的,那些莫高窟周围的墓葬、寺庙、建筑群落遗址、十几公里外的敦煌城,该如何处理它们与敦煌艺术当中每个作品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还需思考,如果“总体空间”的概念如果可以无限扩展,那么边界在何处?我们该以什么原则划分空间,确定功能与秩序呢?看似巫鸿先生的工作只在空间一处着力,背后仍玄机处处。
这种主体性建设的焦虑并非巫鸿先生一人所要面对,艺术作品(目前我们还无法扬弃作品概念)在时间性的叙述中形成了艺术史,空间意识也需要历史观作为支撑。时间性是处理“主体”问题建构中一项根本工作,把艺术作品呈现出的传统形态赋予当下解读出的意义才能构筑起文化认同,致力于面向共同的未来。
巫鸿先生虽强调空间的美术史方法可以用以分析各个文明影响下的艺术,但我们依然相信他的关注点,他躬耕的事业,是面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
中国美术史研究(若精确些,可表述为除去书画体系的美术考古)肇始于“五四”后以顾颉刚、钱玄同掀起的疑古风潮,在文化政治层面,也具有深层的特殊性。“古史辨派”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考察、质疑中国古史,幸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教育部等机构于战乱中考察民俗,勘定古迹,发掘文物。
中华古史的真实性才逐步被认可。当年的工作方法遗留给当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问题便是以图器证国史——单独的绘画、器物孤立庞杂,难以与文献信史产生实际的关联。
巫鸿先生以墓葬美术为质料,引“位”之概念入美术史空间问题,想必早已意识到丧服与礼制、空间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毕竟空间大小之辨一日不完成,我们还真难以判断旧帝国的制度认同与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二者是否有着同轴同辙的关联。其中蕴含的道理直接指向了当代艺术未来的展示可能,我们非常期待先生的后续工作。
注:吴天,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