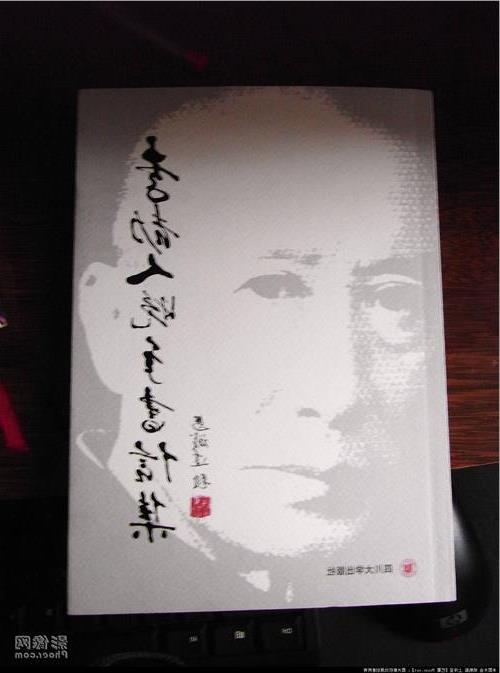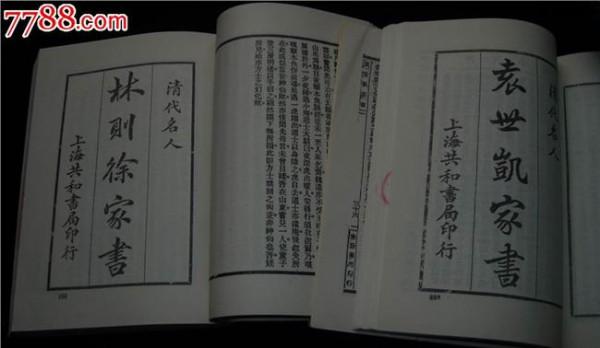李劼是谁 日暮乡关何处是——李劼《上海往事》读后
近半年来,一直与李劼先生的著作缱绻,如其所言:“人与书之间就像人与人的交往一样,是有缘分的。”忽然想到,尚存于世且进入我生命的三位作家,虽然现在身处各方,却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先后在书本里,遇到周国平、张远山、李劼,这三位上海人。
看来我和上海人还是颇有缘分的,虽然我并不喜欢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李劼在早年的一篇评说上海朋友的文章里,说自己没什么地域概念,对自己的出生地上海既不感到骄傲也不感到沮丧,他将上海人定义为有着平常心的人,他虽然喜欢上海人,但觉得自己并不是正宗的上海人。
而在时隔十余年的这部《上海往事》里,他重新定义了上海人:“真正的上海人,不在乎生生死死,而在乎能否获得自己想要的活法。
哪怕是因为那样的活法而遭致令人惊悚的悲惨结局,也在所不惜。” 李劼眼中最为典型的上海人是人称海上春申的杜月笙,也就是小说里申常德的原型:“虽然本地人当中也同样不乏势利之徒,但区区却愿意将上海本地人看作是黄歇的传人,是那个就算知道李园图谋不轨、也不会挥刀杀之的春申君的传人。
杜月笙的行事留余地,春申君的为人不设防,应该成为上海本地人行事为人的圭臬。倘若说,高贵通常要付出代价,那么只能说,正因为有了代价,才能叫做高贵。”(《乡音·申曲·上海本地人》) 前后两种对上海人的定义并不相悖,而是相通的,只是具备平常心的人在普遍沦丧平常心的世人面前,才需作后一种阐述。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往往视平常心为异常想,而不知道是自己的生命被太多东西给充塞了。
纯白之人,在这个颠倒迷乱的世界,反而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形象,成了山海经式的神话人物或者小王子式的童话人物。 当李劼流亡异邦,他明白了上海的本真意味。
“就好比莎士比亚不管走到哪里,英国文化始终在其脚下。担当着文化命运的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文化以及经由文化而获得定义的祖国,始终在其脚下。”(《康正果和他的正果之作》)毋宁说,他只是在地理上被放逐出了上海,而他们却早已在文化上被放逐出了上海。
曾随父母经商去上海的妻子,因为我而回到我们的家乡,浙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龙泉,她曾问我,是否愿意为她去上海奋斗,我很为难地说,那对我来说,是地狱,是噩梦。
我喜欢生活在家乡,原因除了我对家乡粉干和烧饼的热爱之外,就是我生性贪图安逸。然而小地方虽然安逸,却难遇同道。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许多年以前,我在家乡的论坛发了几篇帖子,妄图钓到同道。其中一篇我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语言的民族”,我这样写道:“苏格拉底说:‘凡人之善皆在于智慧,凡人之恶皆在于愚昧。
’老子却认为‘智慧出,有大伪’,而主张‘绝圣弃智’。其实并非二者观点相悖,而是二者对‘智慧’的定义不同。西方人定义中的智慧是指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而中国人定义中的智慧是指获得世俗成功的谋略。
所以西方人眼中的智者多是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哲人,而中国人眼中的智者多是帝王附庸下狡黠机巧的谋士。西方哲人,以智慧(真义)本身为满足,他们喜欢自称为爱智者而非智者;中国谋士,以智慧(伪义)带来的成功为满足——如果不能带来成功便不是智慧了——他们只是膜拜成功而不是爱智慧。
”乡人除了随便附和凑热闹的,就是声称自己虽然不懂哲学也不懂逻辑但为我崇洋媚外的奴性感到悲哀的,还有表示不能理解如果不能带来成功智慧有何意义的。
林语堂说:“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就时间、空间而言简直就被监禁于周遭环境中。生活完全公式化,只限于和几个朋友接触,只看到生活环境中发生的事,无法逃脱这个监狱。
但当他拿起一本书,立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代,讨论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实际上真正使我出于崖涘的,是互联网,它让我欣喜于“德不孤,必有邻”,也让我望洋兴叹,自惭形秽,为以前的懒散懊悔不已。
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这辈子可能就与李劼以及其他师友无缘了。李劼曾在微博上写道:“当世人哪天醒过来突然发现:思想在网上,学问在网上,智慧在网上,勇气在网上,逻辑思维在网上,艺术审美在网上;思考在网上,交流在网上,学习在网上,新闻在网上,文化在网上,最新人文成果在网上,良心良知在网上,不上网成了不读书不看报没文化的同义词;人人都会豁然开朗:学府文科,已然虚设。
” 同事朋友们有时会问我:“你平时晚上都干什么的呀?”我说:“读书,上网。”然后他们就会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岂不是很枯燥很无聊?”甚至还有担心我会与社会脱节的,我只能对他们傻笑而无法解释什么。
不能说我厌世,正如不能因为我不吃猪食就说我厌食。本真的世界不会存在于群聚之中,而只存在于孤独之中。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意味着自我与世界的分隔,而是意味着自我在这种新的建构关系中可以不再通过‘我们’而直接与世界对话。”(《文学是人学新论》)我不会永久地将此身闭守一室,只是,我要先寻回我失落的东西,从这位上海人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发现世界。
这位上海人,此时却在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度漂泊,并做着文化义工。我一直认为,“文辞终与道相妨”,李劼先生以泪以血著书,对他自己的修持而言,未尝不是莫大的牺牲。
我等又怎能不满怀热忱地打开他的书分享他的思想芬芳。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人情同于怀土,李劼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即便有朝一日被允许回到上海,也必会生出“家山已改昔时妆,茫茫天地吾何有”之慨。
小说里,芬妮对她的友人说:“我和阿瑟·鲁宾斯坦不一样。
他是为全世界演奏的。我只向我心爱的丈夫倾述肖邦。”是的,真正的艺术不需要功名,甚至不需要观众,而只需要知音。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日暮乡关何处是?命运给了李劼配得上他的苦难,但我相信,他不会永远漂泊,他终有一天会回到他的家乡——他的知音、他的爱人那里。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