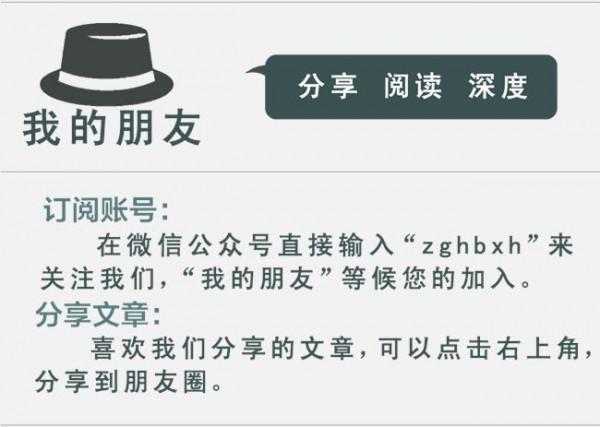二泉映月震惊外国人 《二泉映月》文革中为何被禁:竟因美国人叫好
常州幼年班后来被称为“音乐少林寺”,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之时,幼年班贡献了7名各声部首席,而在最重要的第一小提琴声部,12名从全国招来的乐师之中,幼年班便占了5席。吴伯超是把这些孩子作为未来国家级乐队成员来培养的,孩子们的表现后来也确实不负老院长所望,但他们或许都没有想到,一支国家级乐团所要承载的,远远不只是音乐。

甚至,音乐只是其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读到远方那个“中央管弦乐团”的招考公告,对此或许能多少有一些思想准备。不过他们不用等太久,因为很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成为同事。而无论来自何方,他们也都必须面临选择的困境,如何在努力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同时,保持住音乐艺术之美。

2 要民族创新,还是要西方古典
乐团1956年成立时首演的是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音乐会,1996年最后一次公演的曲目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而中间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乐团不能公演西洋音乐作品,包括德彪西、贝多芬在内的诸多作品更是被点名批判。乐团曾经奉命创作演出大量民族音乐风格的管弦乐曲,《穆桂英挂帅交响诗》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可是当代的听众,有多少人会知道曾经有这样一部作品存在过?

1956年7月3日,中央乐团举行了它的第一场音乐会,纪念莫扎特诞辰两百周年。那天的曲目包括《费加罗的婚礼》序曲,《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演奏小提琴的是15岁的中学生盛中国。事实上,乐团正式的成立大会,是在一周后的7月10日。

在此之前,这批音乐家作为中央歌舞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参与了多次外交与联谊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参加1953年和1955年两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至于1951-1952年间音乐家们长达一年的旅欧演出,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个奇迹,音乐家们躲过了第一场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对《武训传》的批判。
更重要的,一年的旅欧巡演,为年轻的音乐家们提供了一种与世界接轨与交融的可能性,也切实为他们带来了演奏技术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或许也让他们对归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更加感到格格不入。
但那都是后面的事了。至少,在那个1956年的7月,一切还都是美好的。中央乐团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莫扎特演出,有了自己面向公众的“星期音乐会”,甚至,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北京音乐厅。
在当时,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音乐界,似乎隐隐承担了一个任务:向世界证明中国音乐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能够拿进来,以高水准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一是能够走出去,创作并演出中国特色的交响音乐作品,并被世界接受。这两个指标看上去似乎并不矛盾,却与中央乐团几十年的“土洋之争”暗合。
事实上,音协主席吕骥早在1948年就曾经表示,“今天是群众的时代,音乐也是群众音乐时代,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是以西洋的钢琴、提琴等独奏乐器为主。”而音协副主席贺渌汀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代表某一民族特性的音乐,主要不是乐器,而是音乐的内容,音乐越进步,表现的力量越强而音乐上最主要的作品还是要用进步的西洋乐器来演奏。
这样的斗争,当然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在中央乐团40年的历史当中,既有祥和宽松的艳阳天,也有暴风骤雨的阴霾,而乐团便在贝多芬、莫扎特与群众歌曲、革命歌曲之间,蹒跚前行。
历数中央乐团土洋两个方面的成果,《凤凰咏》附录有中央乐团40年的演出曲目和主要录音。与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合作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严良堃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小泽征尔指挥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等,都堪称耀目,特别是贝九,更被看做是中央乐团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79年年底与小泽征尔合作的版本,更堪称时代的强音。
但若以录音论,中央乐团留下的声音当中,更多的还是《黄河》、《梁祝》、《沙家浜》、《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等等,这些作品是否成为了世界交响音乐的经典,见仁见智,但它们已经成为国人的文化记忆,则是不争的事实。回想起来,两条路线的斗争难以评说,倒是这些声音,成为一种意外的音乐财富了。
1999年,深圳。有幸跟指挥元老李德伦大师和作曲元老吴祖强教授见面,我表示对中央乐团深感兴趣,谁知李老劈头一句:“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就这一句话,让我下决心访查和研究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发展足迹。后来拜读吴教授的文章,其中一篇把中央乐团画上休止符的改革比喻为“集香木自焚”的“凤凰涅槃”。如此悲壮的描述,更引起我追寻“神鸟”历史踪影的兴趣。周光蓁
一支完整齐全的交响乐队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通过演奏中西管弦乐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让中华民族亦可以管弦乐昂然步进世界音乐殿堂。用音乐先驱曾志忞1904年所说的话:“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吾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然欲达目的,则今日之下手,宜慎宜坚也。”周光蓁
3 中午的黑暗
在甚至还没有完成全民文化扫盲的时代,一支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的乐团多多少少是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为此,乐团领导只能变着花儿去适应一次次的运动潮流。放卫星时期,中央乐团的卫星是一年的演出场次要数以万计,为此乐团化整为零,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奏上两首曲子就算一场才能过关。但即便如此,当清算的时刻来临,工人代表一句从来不喜欢也听不懂那些交响乐,就足以让乐团的“革命”努力毁于一旦。
1973年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内部演奏会,为到访的美国客人基辛格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文革”以来,中央乐团首次被允许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虽然仅仅是内部演奏事后证明,《田园交响曲》并不田园,中央乐团就将迎来新一轮的暴风骤雨。
其时,中央乐团的身份是“无产阶级革命样板团”之一,主要的演出任务,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
以今日的观点看,彼时的中央乐团,被剥夺的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自由,音乐家们在人格上,可能都处于一种被压制与控制的状态。但以当时的现实来看,这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处境。
事实上,从反右到“文革”,十几年间中央乐团数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乐团能相对平安地走过那段中午的黑暗,既与团长李凌等人的努力有关,恐怕也有相当程度的幸运与偶然因素。至少在一开始,无心插柳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最后能成为乐团的护身符,大概是连创作者们都没有想到的。
当然,在那持续十多年的惨烈斗争过程之中,中央乐团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文革”之中,乐师们纷纷组建造反派、战斗队,在斗争过程中,1968年4月,乐队队长陈子信自杀,之后又有陆公达、门春富、依宏明自杀身亡。乐队首席、小提琴家杨秉孙因言获罪,被判十年徒刑,而乐团创作组的作曲家瞿希贤则入狱六年七个月瞿希贤的名字未必为大众熟知,但她的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乌苏里船歌》,可谓脍炙人口。
对中央乐团来说,压力最大的,或许是乐团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战场。1973年,为基辛格演奏《田园交响曲》之后不久,指挥大师奥曼迪率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中央乐团献上的演出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交响版的《二泉映月》。在随团而来的著名乐评人勋伯格那里,《二泉映月》是一首优美的作品,奥曼迪本人更对这首曲子惊叹不已,甚至把总谱带到美国准备在美国首演。而《黄河》,则被勋伯格称为“黄热病”。
结果,由此引发了一场对西洋音乐的总批判,《二泉映月》则被禁演,甚至以国家渠道要求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不要在美国演出这首作品。对于乐曲的改编者吴祖强来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了一回这样的决定,该是怎样的一种遗憾。
4 要固守专业,还是要市场活力
中央乐团的重大转变,出现在1975年,当年10月的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十年来第一次上演了带有原版歌词的《黄河大合唱》,“革命样板团”由此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到1978年4月,韩中杰指挥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由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实况转播到英法两国,漫长的黑暗时代终于过去。不过,中央乐团的斗争史却并未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层面的“斗争”与分歧。曲高,和寡。
1989年6月2日,中央乐团又完成了一部首演曲目,布鲁赫的《希伯来悼歌》,一个月之后的7月18日,乐团创作组组长张文纲作曲50周年音乐会,则以混声合唱作品《爱好自由的人们》开场。曲目的选择或许能偶然契合乐团成员的心境在此之前,乐团已经经历长达三个月的“不排练,不演出”时期,包括1989年春节期间的罢演。
这是连“文革”期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究其原因,时任副团长的谢明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演出,心里过意不去,可越演越赔钱……一场演出下来,累得精疲力竭,瞅着那四块钱(演出费)心里发笑。”当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一句“最多不过乐队解散而已”,是中央乐团40年历史当中收获的最灰色报道。
其实,以市场为诱因的观点分歧,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1979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为电影《小花》伴奏,李谷一的演唱风靡全国。第二年,部分团员开风气之先,组成“太平洋乐队”,录制了一系列的轻音乐作品,更是风行一时。
在这个基础上,乐团原有的大编制古典乐演奏风格与轻音乐的市场潮流,产生了不小的冲突。最终,李谷一与小乐队于1983年脱离中央乐团,另组为中国轻音乐团。而在一年之后,中央乐团本身,也开始出堂会了,第一场纯商演,是“庆祝长城饭店开业交响音乐会”。
但中央乐团的商业演出之路,是难称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乐团似乎连原有的专业也失去了。1994年,中央乐团在为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协奏曲决赛进行伴奏时出现失误,引起极大争议,加上之前媒体上《中央乐团只是一块招牌了》的批评,乐团的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余韵不仅仅是交响乐
中央乐团的声音,已成为历史。而中央乐团亲身见证的那场斗争、那些问题,则还是我们的课题。这,也是我们要重温那四十年历史的出发点……
1996年2月3日,李心草指挥中央乐团演奏威尔第的《茶花女》序曲、门德尔松的《钢琴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随着马一的最后一个音符休止,中央乐团的演奏历史也就此画上句号。中央乐团改制为中国交响乐团,加上2000年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改制为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的新时期就此开始。
如今中国的几大交响乐团,已经有了与世界类似的演出季形式,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等的高水平演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至于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吸引世界顶尖乐团的盛事。但在这样的辉煌后面,中央乐团40年历史当中所面临的那些斗争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答案恐怕仍不乐观。
对于早期的草创者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先驱来说,交响音乐引进中国,多多少少带有一种西方先进文明的意味。但这先进文明与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却艰难万分,抛开种种的政治风波不谈,仅仅以公众对交响音乐的接受和认知程度而言,百年来的进展可能是相当令人尴尬的。
而在这尴尬背后,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对交响乐世界的参与,更是尤其艰难这简直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扎根过程的折射,先进文明与本土文明既争斗又融合,互相之间到现在为止,也还在摸索各自的位置。
身处京畿政治风暴眼,乐团面对连绵不绝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论争,以及国家大起大落的政治、外交动态,既是对外的橱窗,又是对内的箭靶,荣与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令人惊讶的是,乐团涉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首演莫扎特一刻开始,历经“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出国潮、艺团改革等。
周光蓁 虽然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但乐团的生命力顽强,靠的是团队精神和强烈集体荣誉感,一次又一次保住垂危的乐团,还创造条件演出中外古典管弦作品,反映乐师们爱乐精神和对交响视野的执著,一直到1996年乐团进行改革、更名、解散为止,“凤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