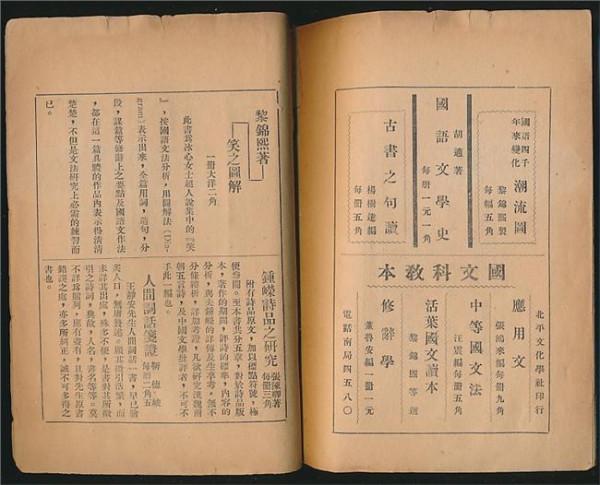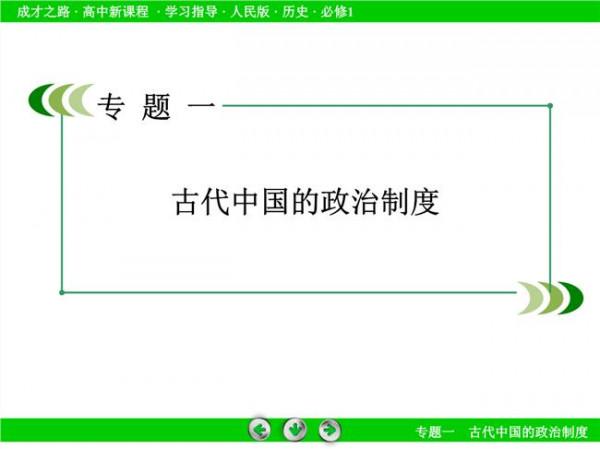顾炎武治学 梁启超谈顾炎武的治学与人格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史学家。原名绛,子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学者尊为亭林先生。青年时参加复社。在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退而读书著述。
1635年清军南下,顾炎武先后在苏州与昆山参加抗清斗争,后辗转太湖一带广泛结交抗清志士;以匡复明室为志的他,对翰林院学士熊赐履推荐其赴京修撰《明史》表示拒绝。四十五岁时,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北游,行踪抵达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

其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出了《日知录》等五十余部著作。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实学,革除了晚明王学末流之弊,开启了清代实学的先河。清代学者主要是承传、发扬了他开创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才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并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的丰富成果。

梁启超评价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他的"学者人格"表达出由衷的钦佩和赞扬
何谓"学者人格"?梁启超指出,"所谓‘学者的人格’者",就是以精力专注于学问,"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说,像顾炎武这样的学者在学术史上"能历久而常新者,不徒在其学问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靠着一批又一批这样专务于学术的学者,靠着这种崇峻的人格和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才推动了各个时代文化的发展。

怎样才能具有学者人格?梁启超引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耿介》说,"读屈子《离骚》篇……乃知尧舜所以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淤世,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炎武所说的"耿介"是指士大夫不"同乎流俗,合乎淤世"的正直操守与气节。

他的《谒夷齐庙》诗云"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终怀耿介心,不践脂韦径。
"(《顾亭林诗文集》)。"脂韦径"指的是柔软、平坦之路。顾炎武通过这首诗诗,赞扬古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蕨首阳的高士之风,在表白自己耿介高洁的志向、忠于明室的气节的同时,流露出在治学上不同流俗、不畏艰苦,甘于奋进的态度。
正是立足于这种学术操守,顾炎武对明末以来空疏的士风、学风十分反感,指责其"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针对明学空疏之弊,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治学之道。
梁启超对此十分欣赏,认为,"博学于文"旨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揭示的是"做学问的方法"要博览群籍,熟通经史;"行己有耻"揭示的是"做人的方法",士人当以"知耻"作为"树人格的藩篱" (《清代学术概论》),划定做人的底线。
在顾炎武看来,明末世风日下是由于士大夫人格不立,人们无是非之心、羞辱之心,于是顾炎武力倡树立人格来改变社会风气。梁启超强调说,顾炎武修养的方法扼要讲就是"行己有耻"这四个字,他力图通过自律从根本上校正晚明士大夫颓废的人格与学风,人要检束自己,"归根到底是知耻二字。
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不被己泽;不耻地位不如人,而耻品格不清,"这样努力下去,才可以实现人格的重塑,从而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儒家哲学》)。
梁启超指出,鉴于明末堕落、颓放的学风,顾炎武十分注意著作家的道德问题,他对将前人著作改窜为己作的剽窃之风尤为反感,认为自晋以来这种现象日益越来越多,明代最为严重。为此他提出,凡所著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
"(同上) 他以顾炎武致友人书为例,说明著述《日知录》的艰辛:一年之内,"早夜诵读,反复究探,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其中每一条,都是顾氏亲自"采山之铜"(矿)所铸得,是辛劳和汗水的结晶,它们见证了顾炎武不蹈袭、依傍前人,实事求是、谨慎自守的治学精神。
梁启超谈到《日知录》成书经历了二十余年漫长的时间。究其原因,是由于作者秉持"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原则,在长年累月中反复不断地修改。该书初成之后,顾氏门人潘耒请予刻印,顾回答,须再过十年。
顾炎武本人在初刻自序中说"旧刻此八卷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之学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是。""盖天下之理无穷……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
" 梁启超对此深有感慨地说:"我常想,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老而不衰?觉得自己学问已经成就,那便衰了。常常看出‘今是昨非’,便会常常和初进学校的青年一样"(同上);"见其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兴奋向学","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 (《清代学术概论》)为此,梁启超赞扬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表达出他对顾炎武的深深敬意。
梁启超在对顾炎武的学术精神表达钦佩和赞扬的同时,对清末至民国以来学术研究的情况,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现状进行了检视和对照,他对后者深为不满,指出这一时期的学人普遍缺乏顾炎武那一代学者"善疑"、"求真"、"创获" (《清代学术概论》),脚踏实地的学术精神,不少人甚至是在靠"剽窃些余绪过活"(《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数十年间学术研究的苍白和贫血,优秀学者与成果的缺失。
他勉励年轻一代学者将传统的治学精神与近代先进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即既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方法",又同时"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和其它科学的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将灿烂的中华学术发扬光大。
梁启超在表达上述观点,抒发对顾炎武如此仰慕之情的时候,他本人早已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以变法维新、思想启蒙驰名天下,也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位踞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首席。梁启超这种敬重先贤、虚怀若谷的风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的这些观点及提倡的治学态度,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