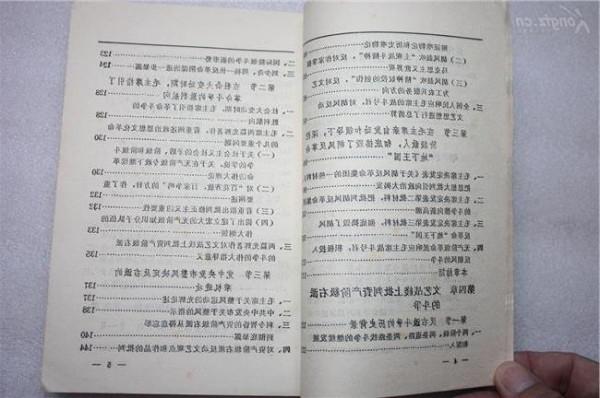胡风和周扬 姜弘:胡风与周扬——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清楚地反映出两种文艺思想和文艺传统的主要分歧,即:承不承认文艺有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承不承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其实,批判胡风的那些理论家们比胡风更重视主观精神,不过他们重视的不是作家艺术家自己的主观精神,而是“人民的”、“阶级的”、“党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些抽象群体的领袖和领导者自己的主观精神,而且把它说成是“客观真理”(绝对精神),这就是他们十分重视并不断强调的“世界观”、“政治性”、“党性”。

《后记》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本是鲁迅那个“国民性”的另一个说法,并无什么新义,然而,正是在这里,突显出一个巨大的思想理论鸿沟,这就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与此相关,还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问题。

所以,胡风在提到这个概念时,紧接着就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拔高、美化农民并贬低、丑化知识分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兴起的那股革命思潮的主旋律之一,后来的“文革”灾难就是在这种旋律的伴奏下到来的,可以说,知识分子的遭难是和全民族的灾难同步的。

在这中间,知识分子自身的互相残杀和自贱自侮起了很大作用。胡风没有卷入这股历史逆流。在这个问题上,他虽没有鲁迅那样深刻,却能保持清醒,一再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早在1940年,他就说过:农民是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自己的,必需对他们做启蒙工作。他反对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反对那种掩盖在“大众化”、“民族形式”口号下的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提出“文艺,只要是文艺,就不能对于大众的落后意识毫无进攻作用。”与此同时,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作为启蒙者的他们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胡风在“后记”里提到这三个概念,没有重新解释,只是在简单说明当时论争情况的同时,加了这样一句:“关于内容,因为我与社会隔绝了二十多年,思想上没有进步,只好由文章本身来说明。”这就是说,他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
复出后的胡风与复出后的周扬如此相似又如此的不同,相似的是他们都没有变,都坚持原来的观点和路线;不同的是,他们所紧跟的两位巨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路线。胡风在回顾历史,总结自己一生的文学活动时,反复强调鲁迅的教诲和影响,却根本不提毛泽东及其《讲话》。
周扬后来的讲话和文章,无论字面还是精神都离不开毛泽东及其《讲话》。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左翼文化界的元老宿将都在反思,向五四回归,而周扬却没有,这是为什么?除了延安时期和“十七年”的显赫地位与卓著功绩需要重新估定之外,还有更深的历史和思想的根源,同样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他同胡风的分歧与矛盾,就是从历史上,从左翼文艺运动中开始的。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头看,把上世纪世界性的“红色三十年代”和中国的“左翼十年”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如马克思所说,那是历史走错了房间所带来的特殊现象,今天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在中国,这场文艺运动也是被一股极左思潮所推动的,一开始来势凶猛,喧嚣一时,却只有政治高调而很少文学实绩,创作和理论都乏善可陈。
倒是负面作用影响深远,至今犹存,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所称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过,左联从一开始就不曾统一过,一直有分歧和斗争。在鲁迅的影响下,一些人程度不同地克服了极左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以往的文学史笼统地颂扬左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左翼文艺运动和左联时期,指的都是“革命文学”论争以后的那几年,因为这场文艺运动和这个组织,都是由那场论争引起和促成的,而且那种极左思想一直贯穿了整个左翼时期,所以应该把“革命文学”论争的那两年也包括在内,这就是从1928年到左联解散的1936年,共九年。
前两年可称为“前左联时期”,左联成立后的1930年到1934年为前期,1935—1936年为后期。——从冯雪峰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止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在“休战”状态中成立了左联,到1933年春天丁玲被捕(她当时是左联书记),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冯雪峰是文委(文总)和左联党团的领导人。
这是左联的发展时期也是全盛期,先后出版了许多刊物,文学史上所记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也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批判“民族主义文学”,与《新月》派、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五烈士牺牲等。
当时鲁迅、瞿秋白、冯雪峰都是站在最前面的。1933年春丁玲被捕后,冯雪峰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但依然由冯雪峰领导,和鲁迅保持联系。
同年七月,胡风从日本回上海,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不久后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左联书记。胡风任职期间,建立了小说、诗歌、理论三个研究会,出版了内部刊物《文学生活》。
因为胡风和鲁迅接近,所以鲁迅和左联的关系得以维持。这一年多的情况虽不如冯雪峰、丁玲担任领导的时期,但组织和活动都还正常。到了1934年冬发生了穆木天告密事件,胡风因受到怀疑愤而辞去左联一切职务,鲁迅与左联的联系基本中断(雪峰已离开上海)。
此后就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领导的时期,是为左联后期。后期左联有两件事特别重要,那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和解散左联。
这三个时期各有一次大的文艺论争,这就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1932年关于“第三种人”和“文艺自由”的论争、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三次论争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对五四传统的看法和态度问题。
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学和文化,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和命运。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是后来一系列论争的开始,只是提出了问题,暴露了矛盾,并未深入展开论辩。
1932年的论争进一步触及到了具体理论问题,实际上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当时提出的“艺术价值”、“创作自由”和“五四衣衫”问题,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三个关键问题。
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争的是文艺与抗日救亡的关系。当时所说的创作方法、世界观、创作自由等等,也依然是那三个问题。由此可知,整个左翼时期的文艺论争,全都是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中心,从政治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这是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教条向五四新文学思想和新文化传统的挑战。
以上事实说明,左翼文艺运动是和极左思潮一同兴起,却又是在不断的纠左过程中发展的。左联成立以后,原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并不服气,论争不再进行,如后来胡风所说,是处于“休战”状态,他们与鲁迅的分歧并没有消除。
那种极左思潮在其他左联成员中同样存在,即使是冯雪峰也不例外,而且就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里,也存在着左的观点(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判断上)。胡风也受过“拉普”的影响,他的早期批评文章同样有左的教条(如《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一文)。
当时,胡秋原、苏汶等所说的左翼批评家的“横暴”和“左而不作”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是历次论争中参与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而且后来关于这次论争的议论也分歧最大,最混乱。
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的历史情况确实复杂,如周扬、夏衍所说,二是过多的牵涉政治问题,特别是中国党内的路线斗争。多年来人们往往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评判这两个口号,而忘记了这是文艺论争。
当年鲁迅的文章和书信,冯雪峰的文章和后来所写的材料,都没有多谈政治问题,都是集中在文学思想和文化思想上:从文学思想上批评周扬们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文化思想上批评他们的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所以,“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本分歧并不在口号本身,而在口号背后的深层思想理论分歧,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冲突。
这次论争的结束,同时也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结束。左翼文艺运动是从论争开始,又在论争中结束的,而且是以围剿鲁迅始,以围剿鲁迅终。这一始一终表面看来都是鲁迅的胜利,极左势力受到了批评,有所克服,而实际情形却复杂得多。
鲁迅答徐懋庸的长信和吕克玉(冯雪峰)批评周扬的长文,并未令“国防文学”派的极左人物心服。迫使论争终止的,是抗日救亡的客观形势,还有左联解散和鲁迅逝世这两件大事。鲁迅逝世在国内外激起的强大精神冲击波,使得许多人,包括一些国民党政要也不得不表面上改变对鲁迅的态度。左翼内部的极左派当然也只有沉默,再一次“休战”。
鲁迅在三十年代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本人的形象,并不像以往那些按照“最高指示”敷演的文学史所说,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主将”,“民族英雄”,“共产主义者”等等。事实上,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复杂,所谓“盟主”,也只是在一个时期和一部分人中间。
鲁迅的加入左联,既不像极左派所说是思想“转变”的结果,也不像另一些人所说是“投降”、“上当”,而是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与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苏联的成就,使他站到了左翼一边。
然而他并没有简单地“一边倒”,而是依然以独立的、理性批判的目光,审视他所加入的这个群体。左联成立前夕,他对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纲领持保留态度;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反左演讲;一年后,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继续批左;再一年,又发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还是批左;到了1935年,劝阻萧军、萧红加入左联,说在外面还可以做事情有成绩,一进去就会陷在无聊的纠纷之中;接着就是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彻底的决裂。
——事实上,鲁迅的加入左联,是既勉强又有保留的,并不那么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出席了左联成立大会以后不久,他就在给友人的信里明白地说出了当时的心境,说十年来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帮助青年们而不断失败、受欺,因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致章廷谦)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鲁迅的这一看法,30年到36年,从貌合神离到彻底决裂,这中间,鲁迅体验到了更大的失败和受欺的苦痛,也耗去了他更多的精力。以往的文学史对此或略而不提,或轻轻带过,却全力去附会毛泽东的“反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之说。
——“围剿”是有的,而且是鲁迅自己首先使用这两个字的,不过,这不是什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国民党没有真正的作家,几个御用文人在文化上根本布不成阵,除了造谣之外,他们只会用书报检查、警察、监狱来武力镇压,哪有什么“文化围剿”?鲁迅是在《三闲集序言》里谈到对他的围剿的,说的是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还具体提到了李初梨、成仿吾、郭沫若等人。
到了后来,更有从背后射冷箭的田汉、廖沫沙,在上面做工头、总管的周扬、夏衍,以及最后直接打上门来的徐懋庸等等。
怎么能无视、抹煞这更重要的真正的“文化围剿”呢?——毛泽东无视这一切,把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复杂形势简单地“一分为二”,说成仅仅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敌我斗争,以掩盖和否定左翼阵营内部的严重分歧和长期斗争。
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否定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和鲁迅的反左斗争。1949年以后一直把“革命文学”开始的极左倾向奉为正宗、正统,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的这些说法为依据的。
《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论述也是违背事实的。在上述“围剿—休战—围剿”的过程中,鲁迅既反左也曾一度受左的影响,但他始终是独立的、自由的。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他倾向于共产党,这是很明显的,但说不上是“共产主义者”、“党外布尔什维克”。
从思想信仰方面说,启蒙主义立场和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曾承认创造社“挤”他读书而“救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却并不是不再信进化论而“只信”阶级论。他研究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并未放弃原来的思想,他“拿来”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并未独尊哪一家、哪一派。
在政治态度上,他并没有“抽象地看党”,他热爱敬重柔石、白莽和雪峰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憎恶周扬、徐懋庸式的党员。除了冯雪峰代笔的文章和书信电文以外,他本人没有在文章里正面谈到过对中国和毛泽东的看法。关于鲁迅与中国关系的种种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