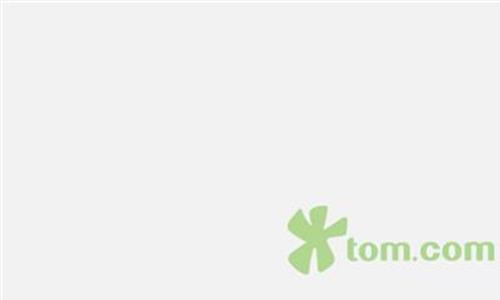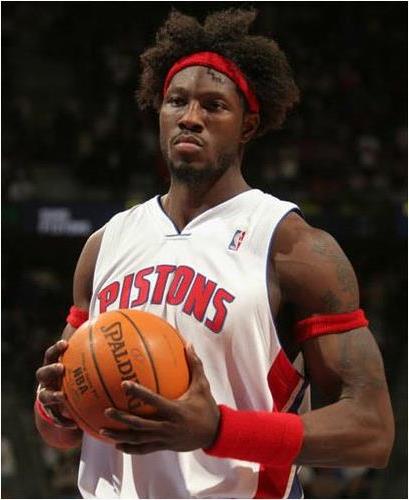华莱士谈笑风生 如何才能与华莱士谈笑风生
近期一些文字,谈及一些与西人交往的经历,一些朋友很喜欢。不仅喜欢,还有打赏,有些打赏实在是很慷慨。虽不知道打赏的朋友是谁,想到这些不孤独的文字,很觉安慰。
这还引出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些朋友想学习如何与西人打交道。有位学者特意发信来问,如何提高英文、如何与西人学者交流。我和她说,你是否要我开个班,教大家如何与华莱士谈笑风生?大家知道我教逻辑不错,以前就要我开线上的逻辑课,现在居然又要求开华莱士班。

我其实对交际没有兴趣,也对国人西人一视同仁。我很安静,对没有意思的人,和自己无关的人,不管国人西人,尤其名流大佬,都没兴趣更不套近乎。虽如此,在学界也算见过一些场合和人,大陆学者能够与西人谈笑风生的,恐怕不过一掌之数吧?虽然华莱士班当然是玩笑,却涉及一个重要主题,即中西文化交通。

一个中国读书人与西人学者交流,如何才能畅通无阻?这里再限定一下范围,不谈很专业的如土木材料、金融法律等,只讲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不敢说能教会大家与华莱士谈笑风生,这篇文字只是简要讲一些个人体会。

我说过,和西人学者交往,逻辑和钦定本对我很有帮助。这有些不完整。逻辑固然重要,但哲学以外的大多数学者并不习惯step by step的严格论证。首先重要的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很多国人学者和西人交往,往往寒暄几句就没有内容可讲了,如果大家专业不同,就更加鸡同鸭讲。

这就是人文知识的欠缺。我读书驳杂,这确实有助于和西人交流。比如,我自己是保守基督徒立场,但和一些白左、世俗化的不信上帝的西人有来往。
有一个白痴级别的白左,价值观念满脑糨糊,我们却很谈得来。有一次不知怎么谈起了Carmina Burana,这个作品是我听得很熟悉的,不觉拉近两人距离。他就津津乐道讲他念拉丁文时候,学这些中世纪修士的风花雪月的情诗,饮酒作乐,悲叹虚空。
他吟诵了一段大体这样的句子:“Why bury yourself in books? Why not enjoy wine and women? O, Fortuna!
All your grant are vanity and chasing after the wind!”(啊!命运之女神!你所赐的都是虚空。与其埋首书本,何不醇酒妇人?”据我所知原文并没有这样的句子,是他自己改编的。这样的交往,所依靠的是人文知识的积累,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毕竟,一个人爱不爱读书,恐怕是预定的。
讲到英文,尽管我在外面生活过,我并不是洋博士,没有正式留学过。口语语法、习俗用语等很多我不熟悉。我的英文发音,从来分不清楚play or pray,美国人的I can or I can’t我也分不清,我就从不说I can’t,都是说I am not able。后来我发觉这是童子功,以后用功没有用的。我家Jacob在密西根上学期间,很快就嘲笑我的发音。我根本听不出区别的发音,他一下就能辨认出来。
英文上我唯一的优势是熟悉King James钦定本。这个很重要,可说是西方,尤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基因。这就像论语和唐诗宋词之于中国。我曾多年不在学校,那些年没有什么书可读,每天读的就是king James。
教会生活也是我能够和西人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普世教会,都是一家人,教会里总会有各种机会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交往。不觉间和西人交往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另外,教会生活是一个稳固的、可交托信赖的共同体,教会礼拜前后,大家握手拥抱、问安交流,这不觉间成为习惯。
但这种习惯,在没有教会生活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人际交往能力了。我自己实在不是擅长交际的人,还有些心不在焉、迟钝木纳,总沉迷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得有一次和一些非基督徒学者见面,我到之前大家都各自沉默着。
我到了以后和大家问候,这在我是当然的事情。后来有个朋友说,你的交往能力太厉害了,一到场就不同。这下轮到我大吃一惊,我说在教会里都是这样的呀!我没想到这成了人际交往的事情。
愿意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西人学者,往往都对中国传统感兴趣。我还算比较熟悉中国传统。但熟悉传统还不够,你要熟悉西人所熟悉的中国经典。西人学者肯定鲜有和你那样读中文原版的孔孟老庄,你要熟悉他们读的中国书是那些。
这就进入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西方汉学。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西方汉学,但西方汉学最主要的部分其实就是传教士的著述翻译。教会史我还算读过不少,利玛窦、马礼逊、理雅各等一路下来的东西,都有些接触。我手上也有不少英文版的孔孟老庄。
一般西人学者不会这么系统,他们人手一册的就是陈荣捷的A Sources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我很早就知道这个Chan Wing-tsit和这本Sources Book,这是我每次上中西比较哲学都要给学生介绍的。
这本书是作为reading使用的,六十年代一出来就成为标准,那些西方汉学、或想了解中国的人,都有这本书。这是上课用的书,很多中国研究的课程,都必备这本,相当于中国大学的一些“原著选读”。
这本书选录了从孔子到冯友兰的重要文献,很多都是陈自己翻译的。这不是一般的reading,还有陈自己用英文写的大量注疏。熟悉了陈荣捷的术语,和西人学者谈汉学就没有隔阂。
补充一点,陈是新会人,和梁任公同乡。陈在当年教会的岭南大学毕业,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陈后来一直在美国的Dartmouth College哲学系教书。他西学中学都很好,晚年对朱子学用功很深。
当代的汉学家,他们的中国学问是隔了一层的,很难和晚清民国时候的传教士相比。那时的西人学者才真正在中国学问上自由无碍。道理简单,当年西人在中国与在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生活工作、传教教书,买地建房、生儿育女。
有些传教士本来就在中国出生成长,他们的中国学问自然没有障碍。现在则是重重关卡,处处设防,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并深入了解中国,实在很不容易的。见过一些可说最懂中国的外国学者,他们距离晚清民国的传教士,应该还是有距离的。
读书的机遇,可遇不可求。逻辑、钦定本、西方汉学、基督徒等,我并没有刻意追求,回头一看,这些都成为自己理智世界的一部分,能够比较好地与西人交往就不出奇了。最后有个建议。最近双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成为中国也许最出名大学了。
若干年前,我重返双鸭山大学读书,张宪老师邀请不少西人学者来讲课。我和这些教授谈新旧约,谈得很好。那时我还从未出国。一次就有西人教授问我,你在哪里留学过?你的英文哪里学的?我说,就在这里学的呀,双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西人教授很吃惊。也许,想要和华莱士谈笑风生,真该到双鸭山大学读书。
天不丧斯文,我手写我心。欢迎关注本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