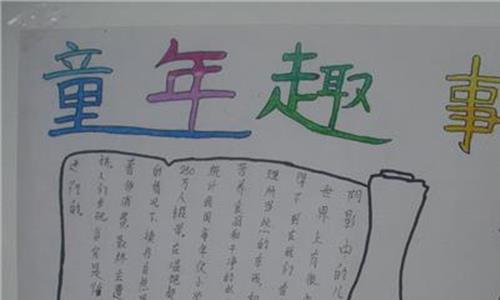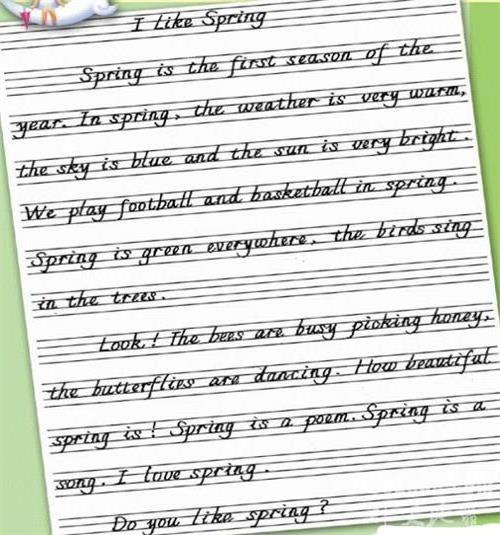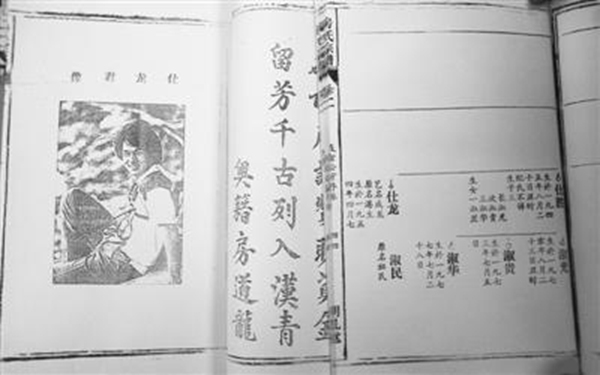童年趣事开头 童年趣事——绞把子
寒冬腊月(编者注,收到此文时,正值腊月),又到了农村杀年猪、腌腊肉、烫豆丝、打糍粑、准备年货的时候。
当我有幸坐在土灶前,用火钳往灶膛里添上一把柴禾的时候,看着红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氤氲着扑鼻的土猪肉香味的热气从锅盖的边缘腾腾升起,我的思绪随着跳跃的火苗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农村,回到了那个用瓦罐在灶里煨鸡汤、利用灶中余火烤红薯花生荸荠干豆丝等的年代,回到了那些似乎永远有绞不完的把子的岁月。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到了第一位,而那个时候农村里用的柴就是把子了,所以绞把子的活一年四季都是不可少的。
春天,当麦子打完以后,家家户户就开始绞麦秸把子;夏天,早稻收割完毕,少部分稻草(大部分要用来喂牛)也成为绞把子的主要原料,当然,如果原料不足,可以掺杂从山上挖回的、从树下耙回的柴禾。

而绞把子最多,时间最长,也最集中的,应该是秋冬季节。
秋天,当金黄的稻穗被收割完毕,当饱满的谷粒从稻穗上被彻底地分离,当一捆捆的稻草被分到各家各户,当一个个草堆高高地耸起,那就意味着绞把子的黄金季节到了。

绞把子的活必须由两个人来完成,基本上是妇女和儿童的专利。通常是大人坐在自制的小马扎或小靠背椅上放草,小孩拿着竹制的像弓一样的中间用麻绳勒紧的绞筒(我的老家叫“搞子”)顺时针不停地转动。

小孩子先退着走,绞到三尺左右长的时候,再快速地走向大人,此时大人将绞好的把绳以三分之一为单位迅速重叠,并像扭麻花一样一扭,再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穿进来。这样,一个稻草把子就大功告成。
一个天清气朗的日子,一大早妈妈就用挑草头的冲担从草堆的顶部“杀”了几大捆草下来,把门口铺得满满的,连路也没留。经过一上午的晾晒,干瘪的稻草明显变得蓬松,还有一股太阳的味道。
妈妈中午一放工,就和姐姐绞起把子来。妈妈一边放草一边说:中午已没把子可烧了,先绞几个对付着把中饭吃了再说。她们动作熟练,配合默契,一会的功夫,二十来个把子就绞好了。姐姐抱着把子,妈妈收拾着马扎和“搞子”急匆匆地去厨房烧火做饭。
我见状心里有点不服气:不就是绞把子吗?又不是没见过,天天看你们绞,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叫我绞,小瞧人不是?于是,趁着妈妈的脚还没跨进门里,我大声喊了一句:妈,把“搞子”留下,我和妹妹来绞!
妈妈听到我的叫声,略微迟疑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我紧接着用比前一次更大的声音又喊了一声,这一回,妈妈仍没有应声,但回头了,她把手里的“搞子”用力地甩了出来。“搞子”在空中转得飞快,并呼呼作响。
我捡起“搞子”示意妹妹过来,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坐在马扎上准备放草,妹妹则拿着“搞子”准备绞。我从身旁抱了一大抱草过来,从里边抽取一小把,手握两端,中间空着向前伸出,等着妹妹把“搞子”伸过来勾住并开始旋转。
第一步似乎并无差错,可是接下来,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妹妹刚用“搞子”勾住稻草并转动,我这边的稻草就脱手了——后续的稻草没跟上,速度慢了!吃一堑长一智,吸取教训,重来!我让妹妹动作慢点,而自己则快点。
这一次确实比前一次要强一点,绳子绞得稍稍长一点点。正在得意之时,绳子还是从我手里跑掉了。再次重来!大概绞了一尺左右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地方鼓鼓的很粗,有的地方又细得像一根线,似乎稍一用力就要断掉,有的地方松松垮垮像随时都要掉下来,有的地方又太紧。
妹妹开始抱怨:看你放的什么把子?粗的粗细的细,像个丑八怪,我不绞了!话音还没落,她已气呼呼地把“搞子”扔在地上了。我努力了半天,手也戳疼了,正烦着呢,见妹妹生气了,我也气不打一处来,对着地上的“搞子”使劲用脚踹。
下午两点钟,妈妈和姐姐要出工去了,临走前,妈妈又用冲担“杀”了两大捆草下来,要我把草铺开晒好,并把上午晒的草翻个面。看着沐浴在阳光下通体金黄精神饱满的稻草,感觉它们都在嘲笑我。哼,等着瞧,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们!我自说自话,并抬脚请人传授技术去了。
秋秋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挖柴,一起打猪草,一起玩耍,除了吃饭睡觉基本是形影不离,她比我大两岁,比我能干好多,在我心里她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找她绝对没错。
远远的,我就听到了他们家绞把子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果然姐弟俩正在进行中,只是所剩无几正要结束。我帮着他们把把子统统搬到柴房摞好,然后提出让她教我。她一开始并不答应:你看看我的手,都是红的,疼死了。你细皮嫩肉的,不疼死才怪!还很容易弄破皮,到时候大人还会怪罪我!
我不停地求她,并主动提出陪她玩、拿好吃的给她、帮她打猪草等一系列条件,并保证大人批评跟她无关,最终她才答应。
先陪她玩吧!我喊来另一个好朋友红梅(比我稍大几个月),我们仨跳了一会绳子。来到我家门前时,看到地上铺满的金黄稻草,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上面打起滚来,进而压起了摞摞,然后又擂拱子,反正是在稻草上,擂倒了也不疼,此时妹妹也加入进来。
终于玩累了,大家都躺在稻草上不肯起来。稻草软软的,还有一股夹杂着阳光的淡淡的香味,好闻极了,我不停地翕动着鼻翼使劲地吸着。可我不明白,如此柔软的稻草为何放把子的时候那么扎手呢?不想它了,好好享受一下阳光和草床吧!
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我赶紧把稻草通通叉到一处堆起来,然后开始学习绞把子。
这一次,我坐在小凳子上,红梅转动“搞子”绞,秋秋在旁边手把手地教,妹妹在一旁观察学习。“送给搞子勾着的第一把草很重要,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多了把子太大,灶膛放不进去;少了把子就小,不经烧。你的手比较小,应该多放一点。”说完,秋秋随手抓起一把草示意我该是多少。
我照着葫芦画瓢,第一把草顺利送出,可“搞子”刚转动了两下,秋秋就喊停了:“你看你的手和草都离开草堆了!放草的时候绞动的草不能离开草堆,它能带动后面的草不停跟进,手只需扶着草就行。”
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草老从我手里跑掉了,原来放草的方法错了。遵照老师的指导继续放草,可没一会秋秋又喊停了:“你看看你绞出来的这一尺多长的绳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个妈呀,后面的比前面的粗好多!
她帮我分析道:刚开始你不懂方法放得比较慢而她绞得稍快,后来你摸出了道道放快了一点而她还是那个速度,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手扶着草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对方绞的速度,喂进去量的多少也要稍加注意。我突然发现看似简单的放草还有这么多技巧。绞把子继续。
我的第一个把子作品终于诞生了!尽管耗时过长——是一般人的四五倍,尽管个头偏小——是一般把子的一半多一点,尽管丑陋无比——又短又松松垮垮,但我没舍得拆散它,因为它毕竟是我们仨精诚合作的成果。
我高兴地把它抛到空中,秋秋很快抢了过去并高高地举起,我们俩怎么也够不着,于是我们就跳起来去抢,并偷偷去挠她的痒痒,可还是够不着。我们俩自己笑得直不起腰,秋秋却丝毫不为所动。
玩闹了一会开始绞第二个把子了。秋秋搬了把小板凳坐在旁边,她除了喊“停”,一句多余的话都不会说,要我自己琢磨。
不用说,这个把子绞的时间更长,因为我既要关注手、手底下的草,还要关注放草的速度,关注绳子的粗细……总之,手、眼、脑并用并尽量保持协调一致。不论是大小还是外形,第二个把子明显比第一个好看很多。
绞了三四个把子后,秋秋直接换下了红梅,亲自上阵转动“搞子”了。一开始比较平和,跟红梅的速度差不多,我还算应付得过来,可接下来她突然加快速度,我一下就乱了阵脚,眼睁睁地看着绳子从手里跑掉而无计可施。
秋秋马上把绳子绕着在空中飞转并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啊,这是某某人绞的把子!我的脸臊得通红,一心想着快点将把子拿下来,于是让红梅和妹妹来帮忙。她们俩各抱住秋秋的一条腿,我使劲朝秋秋的膝盖窝拱了一脚,这一下秋秋没有防备,身子一歪,我顺利地拿下了把子。
接下来继续绞,她时而快时而慢,我慢慢大体适应了。
等绞到七八个把子的时候,秋秋高兴地说:出师了,及格了,可以收工了。然后趁我没注意快速把我扳倒,并喊红梅和妹妹各抬我一条腿,齐声喊着“一二三”把我扔到草堆上,开心地说:一报还一报,我报仇了!然后我们拿着把子,你扔我我扔你,又疯闹了一会。
太阳已经下山了,可妈妈和姐姐还没有回来。天黑下来了,她们终于回家了,原来因为接下来可能连续几天有雨,队长要求把麦子和油菜赶着种下去。
妈妈慌着又准备和姐姐绞把子,这时候嘴快的妹妹马上把我们下午绞把子的事抖出来了,看着大小不一、粗细不匀的把子,妈妈终于笑了:个小女人,还有点本事,奖励你们拿两把荸荠在灶里烧着吃!得到妈妈的肯定,我们俩高兴得跳了起来。
柔和的月光,静静地泻在门前的稻草上,借着皎洁的月光,我们家绞把子的工作正式开始!吱吱嘎嘎单调的声音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一会,秋秋和红梅都带着“搞子”来了:这么多草,一个“搞子”那要绞到什么时候?
她们是特意来帮忙的,我好感动啊!三个“搞子”同时转动,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倍!而且先前单调的绞把子的声音现在也变成了美妙的协奏曲,好像从来没有今晚好听。
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地绞把子,妈妈也非常开心,于是讲起了我们百听不厌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还带着我们一起唱起了“月亮走,我也走……”的童谣,我们也不自觉地唱起了“……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听着说着笑着唱着,所有的把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绞完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秋秋、红梅组成了一个绞把子的小分队,三家中不管谁家里要绞把子,其他人就一起出动,我们家的草堆很快就消失了。不久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雪,湾里好多人把子烧完了到我们家借,隔壁湾还有人出五元一担的高价买我们家的把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姐妹仨当年过年都穿上了新衣服。
厨房里锅碗瓢盆在演奏着和谐的交响曲,蔬菜倒入烧热的油锅发出的“嗤嗤”声和锅铲翻炒时撞击铁锅的声音似乎特别悦耳,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的思绪。
“半天不吭声在发什么呆呢?赶紧出来吃饭,饭菜都上桌了!”堂哥见我在灶下半天没有言语,催促我起来吃饭,顺手丢了一把荸荠在灶膛,特意用余火盖好,并嘱咐我一会记得捞出来。
看着满桌用土锅土灶烹制出来的家常菜,闻着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锅巴稀饭,我突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本文作者孙斌华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孙斌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六十年代出生于黄陂一个普通的乡村,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常常梦回故乡,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忘不了故乡的父老乡亲,不时写点文字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