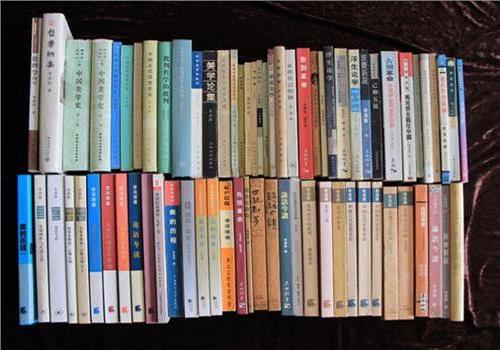李泽厚论权力 李泽厚:再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问:你在《试谈》文中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它真是马克思主义么?它究竟是以马列为主还是以传统为主呢?
答:这是个复杂问题。有人说毛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搬用(苏绍智),有人说毛只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李慎之),有人说毛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金观涛),有人说毛是“儒家列宁主义”(Lacian Pay),有人说毛是“列宁主义,并非中国传统”(B.

Schwartz),有人说毛是农民民粹主义(包括本人),等等。其实这三个方面(列斯体制、专制帝王、农民民粹)以及马恩空想都有。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组成结构的?亦即这一结构的形成是如何可能的?这才是关键。
问:对。重要是这个思想构成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答:虽然国内外也有论著直接间接论述到,我在《试谈》文中和其他地方也着重讲过,但这结构的关键点依然没被足够重视。
问: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答: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军事战争中发展形成的。这是不同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地方。毛本人也首先是以其领导军事斗争即革命战争的才能和地位而获得拥护,并逐渐取得党内的最高权力的。毛在延安称张闻天为“明君”而自封“大帅”(何方《党史笔记》上册第53页,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他至死不放手的是军权。

而他的“思想”也首先正是通过战争经验的总结,获得了军内党内的信任和信服。从三十年代的三次反围剿到1949年前的三大战役,毛运筹帷幄,取胜千里。
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我以为是他最成功的著作。他以后那些“以十当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人海战术”、《矛盾论》中“抓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都首先是从战争经验中提升出来的。

他由军事而政治,搞了一整套战略策略,包括“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奏而不斩”“有理、有利、有节”,……等等等等,都是在与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中(首先是战争中),所总结的思想成果。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他抓得极紧的是“党的建设”,具体办法是“支部建在连队上”,即紧紧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广大的基层。这就大不同于俄共红军只派政委而已。毛以“支部建在连队上”来彻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以后又把军队中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扩展一直笼括整个社会,使人们的一切生活和思想都无所逃于“党组织”掌握之中。党组织成了整个社会的骨脊血脉,上下贯通,坚固持久,效率极高。只要控制了党,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中共党组织力量之强大,是任何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不能比拟的,而这却正是产生在长期战争的军队基础之上的。
问:刘少奇一直做党组织工作,他拥戴毛而被毛选为接班人。文革打倒刘,毛也打碎一切党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文革初期的著名口号。文革批刘时,军队干部积极,地方干部也就是地方的党领导不积极。正因为军队的党组织,刘是直接管不到的。
答:文革下面还要讲。中共党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并不简单只是具有军事特征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而且它还具有某种宗教性的功能。
问:这如何说?
答:这是说党的组织远不止是政治团体、军事组织,而且它已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依托。党组织是自己的“家”。在组织之内如沐春风,尽管遭受委屈以至牺牲,也心甘情愿。“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同志胜过兄弟”,“同志之外无朋友”这些在大量文献中所描述的情况,是非常真实的。
这真实来源于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中的信念一致、理想相同、生死与共。从而使得“组织”“同志”的关系超乎寻常,其价值和感情远远超过和优越于任何其他关系和情感,包括日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党组织在这里既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而特别是宗教的,即人们为信仰一个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在这里,宗教(共产主义信仰)政治(党的一元化领导)伦理(服从组织、同志平等)三位一体。
这个“三合一”也恰好可以与我所说的中国传统中宗教、伦理、政治的“礼教三合一”相衔接(“礼教三合一”见拙作《说巫史传统补》一文,《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要求党不但管政治,而且管个人的一切,而特别是管思想和情感。即不但私人事务从恋爱到家庭要管,而且个人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每周必开党小组会即“生活检讨会”,来检查、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人的行为、活动、思想、情感。
“统一思想”成了党组织的轴心任务。所以把毛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成不过是抄袭或搬用斯大林主义,是非常不准确的。斯大林没有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和理论。
斯大林是肉体消灭、特务专政,毛是思想消灭、群众专政。毛汲取了他在苏区肃反AB团的教训,以后历次整党和搞各种运动都不搞肉体消灭,也极少“开除党籍”,而是强调“改造思想”,即以“整风”方式解决问题:不断地严格地要求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以所谓“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判断、考察、衡量和裁判自己和一切,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再复称之为“心灵专政”。虽然这些形式的一部分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来自苏共,但毛和中共却全面、长期、彻底地实行了。
问:所以好些学术论著以为毛的“思想改造”是儒家化的马列主义。刘少奇《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便引用了大量孔、孟。
答:但刘只是援用知识分子所熟知的经典语句来引导如何“改造思想”,与孔孟原意并不相同,刘自己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所以那只是表面的相似。因为儒家强调的是个人自觉,儒家讲的修养是士大夫个人主动的“正心诚意”,朋友的帮助止于“切切磋磋”,而根本不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体帮助”之下,完全扫除个性尊严和个体自信的“脱裤子”、“割尾巴”(这语言也是下层民众的)。
儒家尊重个性,“整风”则是泯灭个性。我曾说,这与其说是儒家传统,不如说是墨家传统,亦即中国下层会党和农民起义的传统。
所以我说,与其说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金观涛),还不如说是“墨家化”。在行动上,毛在军事--政治上起家特色、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山区红色武装割据,也主要是下层社会“落草为王”的传统。
苏区肃反的残酷肉刑也与下层会党的传统惯例有关。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的流氓习气、痞子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也都与这个下层小传统有关。我以为,毛的“思想改造”表面上像儒家,实质上是墨家,虽然都是中国传统。
问:那么,毛和毛思想是以中国传统为主?
答:但毛毕竟搬来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大小传统无论儒家、墨家都没有的。毛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极端化,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烙印尽人皆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从而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这又是马、列所没有的。
这是以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长期军事斗争的经验为依据,来了解、接受和阐释马列的。
毛在哲学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努力发扬人的思想、意志、“干劲”“精神”,便能“改造世界”,便可达到目的,他一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不断通过“运动”来“推进”社会等等,这实际都来自他在长期战争中的经验。
在建国后,毛把它搬到各方面,包括“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三大改造”“大跃进”“鞍钢宪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这种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质上与墨家的“非命”思想倒是相通的。
所以,尽管毛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整个思想亦即毛式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列其表,小农其里”。毛自以为得马列真传,理直气壮,实际上却是民粹空想,殆误甚大。我以为这一点才是重要和深刻的。
问:那么,毛结合马列,所承接的是中国小传统而非大传统?
答:基本如此。是以造反——革命的小传统为主。1978年我写《太平天国思想散论》文中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在经济上,太平天国的“圣库制”与毛念念不忘要取消八级工资,回到红军时代官兵平等的供给制,便很相似。在政治上,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思想教育,每周必作“礼拜”,由“老兄弟”“宣讲道理”,说的是打下江山如何不易,年轻后辈要记取这艰苦传统。
其他军事上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知识分子利用而不重用,以及强调劳动、“力田”等等也都相似。
毛和中共领袖们并不熟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却居然如此接近,所以这个“马列其表,小农其里”的“其表”,并非欺骗。他们(不仅毛一人)忠诚地自认是马列,但实质上却不然。这才是悲剧的深刻性所在。
毛思想之所以长时期内能得到这么多的人的赞同拥护,便正是这种悲剧深刻性的表现。有如论者指出,从1927年陈独秀与吴稚晖争议是20年还是200年建成共产主义时开始,“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时间内的普遍愿望”。
(杨天石《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载《192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出版,2002年)毛之所以总要讲“马列”,并总能以此来使人追随他,也以此故,小农革命的急性病以为可以一步便建成太平天国。
本来,马、恩对作为消亡阶级的农民估价甚低,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一大批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农民的支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农民战争和农民意识竟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在内容。
问:但毛思想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全是中国的小传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