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少年林嘉文 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自述最后的话 值得深思!
你们知道吗,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我给除刘雅雯外的每个人——包括我的亲人与学友——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遗嘱见下:
3、希望我的父亲能知足,珍惜我的母亲,同时改掉自己家长制的脾气以及极差的饮食追求,认清自己实际的生活能力和状况。太爱出去跟别人骑自行车,其实是不够挂念妻子和家庭。不要再保持那种单身宅男才会有的饮食习惯了,不健康,且这种饮食习惯是对性格和责任心的投射,说明人活得浑浑噩噩。

4、希望我的母亲能振起精神来多抓抓工作,多去挣钱。这样若我父亲先离开,至少还可以维持生活。一个志在过小日子的人,精神也会很脆弱,要学会找些东西依靠。金钱是可以依靠的,另外还有志业也可以支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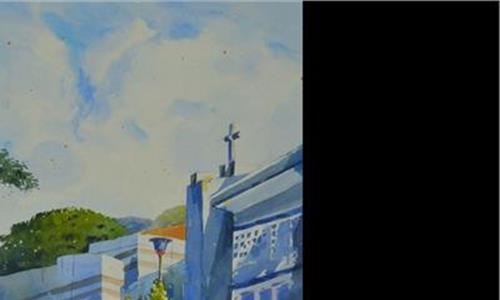
5、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责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6、感谢西北大学招生办刘春雷主任邀请我报考西北大学,很抱歉辜负他一片诚意。谢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将我评为夏令营的优秀营员。谢谢邓小南老师的关照。
7、每次去李裕民老师家都能感受到平日很少能体会到的温馨和安稳感。我对不起李老师夫妇对我的关爱。
8、谢谢李范文老师一年多来对我的提携,答应给李老师整理《同音研究》的事也做不到了。恩情难报。
9、向我的“朋友”们致歉,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但我天性敏感,总是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的发生的小小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让你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人耽误了些许时光。
10、我要承认我对历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岁长进而被我习惯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后,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
虽然我的两本著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对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去缩进历史研究的世界。
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并非能让我拥有尽善的生活感觉,因为有太多虚假的“研究”,还因为本质上少有其他人会对研究爱得纯粹。一个人喜欢追索,哪怕是对任意领域的,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迫。
问太多、想太多是种折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起来。好像说远了,其实仅就对做历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游,拘泥在一门学问之中,那样活着也是很庸碌的。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林嘉文
2016年2月23日 于西安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新观察传媒”)
因为叛逆才爱上了历史
文
林嘉文
1998年5月,我出生在西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在一所法律院校工作,外公外婆都是中学的理科教师,外曾祖父教过中学的语文,勉强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但没什么大知识分子,更谈不上家里有人从事和历史研究有关的工作。
上小学以前,我背过很多诗词卡片,这可能是和我同辈的许多孩子都有过的记忆——那时候背这些东西完全是自愿的。每次家庭聚餐,家里人都会让我起来背诵几首诗词来表现所谓的早慧,在那样的年纪里我自己也判断不了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只是从大人们的赞誉中感受到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这已足以激励我记诵更多的诗词。
真正开启我阅读兴趣并引导我走上读史之路的是我的小学班主任钱瑞老师。也可能是升学压力小,我觉得当年我就读的西安小学实行的是素质教育。
小学时的史学启蒙
记得低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总是开展背诗词和文言的活动,我在这方面就很擅长,大概背了几百篇吧。另外,学校每学期还组织我们去书店读书买书,所以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也和多数人一样是从读注音的四大名著开始念书的。
我念小学这几年,正是社会上读史、讲史之风高涨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有很多学术明星。一开始是我母亲还有姥姥、姥爷很喜欢看《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我也跟着看。
我父亲并不喜欢历史,他是政教系出身的,后来转换到邻近的法学领域,是因为厌烦政治的虚伪,他曾长期把历史当作为现实背书的工具。后来因为我孜孜于翻检故纸堆,他才弄来一套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那时我还在念小学,他常会在饭桌上谈起他的阅读心得,尽管后来我们交流渐少,但这种因读史而生的父子情大抵是别的家庭难有的。
有一次学校组织汇报读书的演讲比赛,我便几乎照着电视上的讲课内容和说话方式表演了二十多分钟,结果在班里引来掌声雷动,我当然很受鼓励。后来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看电视节目。
记得那时《百家讲坛》的播出时间是六点四十,我总是六点就起来收拾收拾,吃过早餐就看电视,直到七点二十节目播完。现在我已很多年不看了,连电视都很少开,但很怀念那时单纯、执着的劲头。
坚持每天看《百家讲坛》,给我带来不少益处。我感觉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耳音灌得熟,主讲人念文献时抑扬顿挫,本身就训练断句,加上必要的解释,所以我后来对文言几乎无师自通;二来是熟悉职官,真正学历史的人大概都能明白职官对史学研究有多重要。
《百家讲坛》,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的讲座式栏目
小学时我特别爱展现自己。全校的阅读课由王琦老师一人承担,我跟王老师关系特别好,所以经常翘本班的课,到各年级的读书课上讲演历史方面的内容。我忘了在念几年级时,跟钱老师带的两个师大的实习生关系特别好,拉着两个姐姐轮着听我给不同的年级讲课。我全然不懂学术规范,但那时已经开始看一些今人著作,也读白话节选的《资治通鉴》《吕氏春秋》《三国志》等。
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如今想来,我仔细阅读过的第一本和我现在的学术兴趣相关的学术著作应该是李锡厚和白滨两位先生合著的《辽金西夏史》,那应该是在小学高年级。当初买这本书应该是很随意的,就是纯粹看书名,没意识到它是枯燥的断代史。
我对民族史的兴趣完全来自于小时候的叛逆,那时候觉得,凭什么汉族政权打少数民族政权就是“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而少数民族政权打汉人政权就是“侵略”?加上那时看到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对秦桧、岳飞的评价,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关心起民族史来。大概就是在六年级、初一这段时间,我买了好几本林干先生的书来读,如《东胡史》、《匈奴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等,一下对北方民族史有了一套基本的知识底子。
小学毕业后我曾到云南旅游,走览崇圣寺等地,很喜欢西南的风光,回去后就买了谷跃娟教授的《南诏史概要》,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从那里面知道了尤中先生,进而了解到方国瑜先生及其弟子林超民先生,本想找他们的著作来读,但方先生的书不好买,加上少年人的兴头总是一阵一阵的,遂作罢。过了一年,虽然买下了《尤中文集》,却没怎么细读。
李锡厚和白滨合作的《辽金西夏史》对辽、夏、金的语言文字只作了极为粗浅的介绍,可能是那时给这些民族古文字排版不易,正文里连例字都没有。恰好插页上有西夏文佛经的图片,那种整齐排列的感觉令我觉得太惊艳了。
所以初一时我给班里的同学讲辽、夏、金的历史,大概是说宋辽、宋夏的交往基本平等,那次我就专门抄了李、白二先生书前照片上的那些西夏文给同学们看,回家后就有点少年人赌气的心理,打算正式开始认真学西夏文。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以后的学术方向会是西夏学,之前都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史泛泛阅读。
在家庭学校的支持下自学史学
念初中时,我还经常在微博上看时贤晒他们参加什么会议,也会留心这些会议的议题和参会的嘉宾,甚至留心他们偶尔在网上闲聊的学林趣谈,连掌故和牢骚话都能被我从中榨出有关学术和学界的信息。
慢慢地,我也变得经常参与讨论,像今年我参与讨论“新清史”,就被《东方早报》转载;过去应编辑之邀写过一两篇小书评,还曾引得几位老师的批评指教。后来发现他们大多更重视读一手文献,这才启发我在史学研究上上了道。
我粗略地自学了文献学、目录学以及学术规范的知识,开始大量阅读关于宋史的一手文献,有时刚回家身上发懒不想换衣服,倚在墙上就能抽出本笔记史料看上一两则文献记载。我不做卡片,但读书时喜欢折角,有时折角的地方过一阵就忘了要点在哪里,一开始还有点懊恼,后来也就洒脱地适应了我的“忘性”,大不了就把那段史料再看一遍。
平日多在书架前“巡阅”,仅仅是望望书名便也能勾连起些有用的回忆和联想。我出版的两本著作都引证了不少参考书,但这并不意味每本参考书我都从头到尾认真读过。我藏书不算少,但我根本答不上来自己一年的读书量,因为我觉得自己平常写作更多是在“用书”,往往只精读有用的章节,然后会用到很大量的书籍。
好在我父母舍得花钱让我恣意买书,特别是我后来有了一定水平,在选书上变得讲究之后,他们几乎从不给我设限,只要我想买书,他们都会答应,大大满足了我购置史料文献的需要,最后弄得家里但凡有个角落我都要用纸箱在那里垒上藏书。
从小到大,只要在应试体制下的成绩不出太大问题,父母一向全力支持我的兴趣,无论是购置很贵的大部头古籍,还是送我参与活动,他们都没有意见。我家住西安北郊,经常要跨大半个城市去陕师大长安校区查资料或者听报告,父母对此从来都不打绊子地配合。学校对我也比较宽松,有时我跟老师讲自己赶稿紧张,偶尔请上半天假,班主任也就批了。
高一时的历史老师刘雅雯与我亦师亦友,甚至友的关系更重一点,以致我从不叫她“老师”。我是她师范本科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刘雅雯很保守,但同时单纯且理想主义,这时常让偶感疲于世俗交际的我感到惭愧。
高二、高三的历史老师刘文芳被我叫作“刘姐姐”,其实她快五十了,我从不会故意发难于学校的老师,但“刘姐姐”偶尔打趣说自己讲课很怕被“林老师”挑错。
我的学术训练完全是在中学教育以外自成的一套,然而父母、师友、学校给予我的宽容还是起了些作用的。
把史学研究当作熟悉的工作
一般人都认为我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过去我自己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但后来一度怀疑自己,就是我突然不清楚什么样的感受叫真正喜欢历史,进而怀疑自己的选择。对学术体制和学界生态有所了解之后,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动摇自己的选择。
那段时间我虽然坚持学习,但跟别人说起这个学科,总有点菲薄之意,以致文理分科的时候,同学如果问我选哪科,我都跟他们讲选理科好,当他们反问我为什么选文科时,我就说自己在这方面有了一点积累,不想重头再来。
后来自己想明白,即使弄不清是不是喜爱史学,几年来我也把它当作一份熟悉的工作习惯下来了,因为当初与史学结缘本就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
我现在很满意自己这种把史学研究当日常工作去习惯的状态,很多人看起来狂热地热爱历史,这样的人若是孩子,那他可能只是热爱故事;要是稍微大一点的人,那他可能喜欢的只是他想象中的学问和学界。
总之,真实的学术生活十有八九会让他们尴尬,而我有颗平常心,可以处之坦然。另外,我也不用像一些学历史的人遮遮掩掩、底气不足还得对别人吹捧自己的志业有用,那样子有点窝囊。
史学就是纯粹的,它那点现实功用比不过专精的各门社会科学,坦白史学的无用,那才是真正克服了心中的不自信。
对自我价值的困惑
2014年6月,《当道家统治中国》出版,我提出拒绝配合出版方和学校的任何宣传,并要求隐瞒年龄、不要炒作。
其实《忧乐为天下》出版后的舆论反应,完全合乎我高一出《当道家统治中国》时的担忧,从初中起就熟悉网络舆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的社会上很多人不太欢迎别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对年少有才华的人并不看好,会顺理应当地认为其中有作假,或者想当然地料定别人会“伤仲永”。
我那时已未卜先知地畏惧媒体的压力以及被捧杀的可能了,所以实在不愿让自己白白成为这些舆论泡沫下的牺牲品,不想自己宁静的读书生活被打扰。更何况,《当道家统治中国》是我自己都觉得有不少遗憾的通俗随笔,所以更不愿炒作了。我为我当时自私的选择而对读客公司和西安中学都感到抱歉,以致出第二本书时我没再好意思推脱出版座谈会。
受到对自我价值的困惑,加上高中学业的负担,还有我一向糟糕的身体状况,去年夏天我为《当道家统治中国》的出版丝毫高兴不起来。去年暑假集中撰写、修改《救斯文之薄》时,身心压抑感极强。
林嘉文著《当道家统治中国》
随着知识的积累,我反而越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无法伪饰自己,在被谬赞时感受不到心安理得。那段日子里灰心的样子看似高傲,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偏向于消极、压抑的冷静,一如苏舜钦的诗,“青云失路初心远,白雪盈簪[zān]壮志闲”,看似有淡然的豁达,背后何尝没有失望与苦闷。
虽然自己不是罗福苌[cháng]那样的天才,但前辈学人也有不少都是很早起步的,我无非是没有依从现代社会里很多人的观念,并未以年龄和身份限制自己学术进步及社会交往的可能。
(本文转自慧田哲学的博客-Via:慧田哲学人公号「philosophs」编
林嘉文的一次座谈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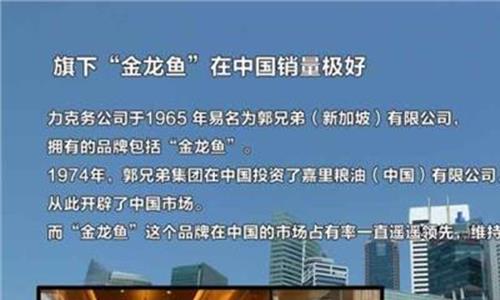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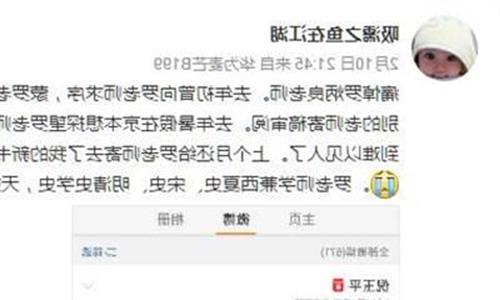




![>窦文涛喜欢俞飞鸿]窦文涛锵锵三人行](https://pic.bilezu.com/upload/4/79/4792a9337ffa42cafec7280517dcb93e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