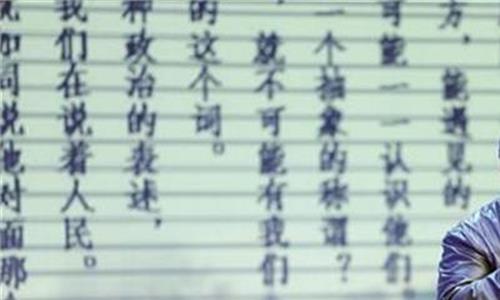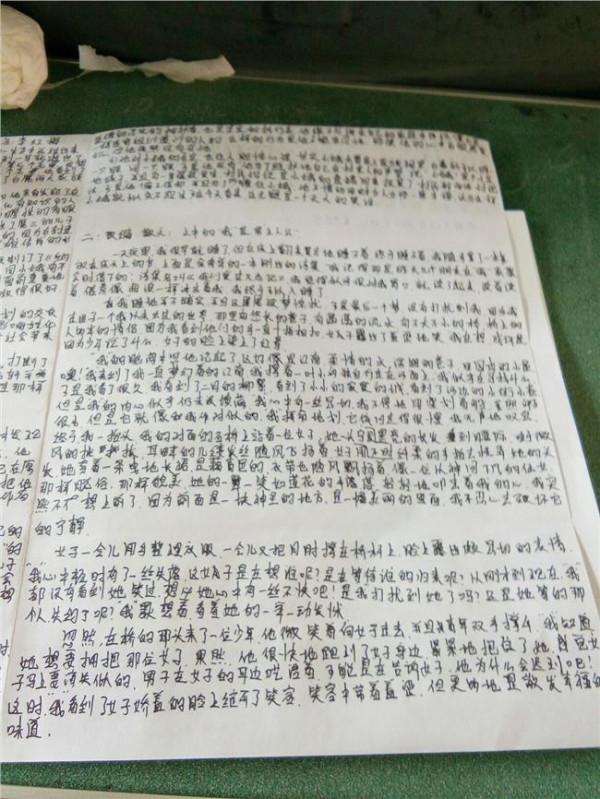错误郑愁予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诗人郑愁予访谈
郑愁予先生少年早慧,十几岁就开始写诗(现代诗)。虽然生长在北方,但他的诗是南方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是打江南走过的。这个"江南",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江南,还是文化的江南,唐诗宋词的江南,既古典又现代的中国的江南。

郑先生在今年深秋打江南走过时,我们把他请到了乐清可楼。我们在迎来送往间、在宴饮间,有过一些零星交谈。现将这些谈话片段稍加整理,以飨读者。
(下文"东"为东君,"郑"为郑愁予)
东: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诗名总是跟达达的马蹄声联系在一起。每当人们提到你的名字,总会谈到《错误》那首诗,而且总会提到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

郑:这些年我马不停蹄,走了不少地方。有人问我,累不累?唔,我如果觉得累就不会满世界跑了。我现在已是一个86岁的老人了,但你们不能总是把我当做一个86岁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要扶上一把。我走路有自己的节奏,你一扶,我的节奏就乱了,反倒容易摔倒。

诗歌也是讲究节奏的。现代诗的节奏是内在的。《错误》这首诗,一般人的理解是,它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游子经过一个地方,留下了他的情。表面上可以这么说,其实内在的层次不是这样子的。
我写这首诗的灵感跟儿时的一段记忆有关:1937年,我跟母亲离开南京浦口去山东的时候,一匹马拉着一辆炮车打我身边经过,那股声音带来的力量一下子就把我冲撞到马路边,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场景,记得那达达的马蹄声。我后来要表达《错误》这首诗时,就记起了这事,于是就把"达达的马蹄"写进了我的诗。我写诗时,一直很注重语言的节奏感。所谓节奏,其实就是内在情感的一种表现。

东:记得你谈到《错误》时不仅提到了上面这段往事,还提到了莫愁湖的莲花。在你的记忆中,一边是美丽的莲花,另一边却是战争年代的烽烟。你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几乎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你后来每每谈到童年往事就把自己称为"抗战儿童,内战少年"。两次残酷的战争过早地在你心底里埋下一种忧患意识,这是否就是你诗歌创作的缘起?
郑:我的名字里有一个愁字。这就注定了我的性格里面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我出生于山东济南,五岁到南京,住在离莫愁湖不远的黄泥岗。父亲在军中担任要职,追随张自忠部队,去了湖北,跟家人聚少离多。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我跟母亲投奔二伯父所在的峄县。
峄县有两个庄,一个是枣庄,一个是台儿庄。二伯父时任警察局局长,管着这两个庄。当时二伯父见到了我们母子俩,紧张得不得了,他告诉我们,这里也很危险,你们还要向北走。
于是我们去了河北,投靠五叔。那时候,铁路桥梁大都被日军炸毁,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1940年,张自忠所部与日军在襄阳激战,全军覆没,张自忠战死,我父亲音信全无。我和母亲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我常常对人说,我是抗战儿童,内战少年。
我写诗的冲动,是从读北大暑期文艺班开始的。第一首诗写于北京,题目叫《矿工》。有一天,我去门头沟玩,看到一座煤矿,一些小孩子正在那里徘徊着,我就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等爸爸出来。我听了眼泪就刷刷流了下来,回去后就写了《矿工》。
我所读的中学是英国式寄宿学校,叫崇德学校,老师多半是英国人。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我读来读去,几乎把里面的藏书都读了个遍。我读的小说类的书大都是俄国小说,诗歌我记得读过马雅可夫斯基。
当然,我也读到了欧美一些现代诗。有翻译的,也有原文的。国内有两本诗刊,一本叫《中国新诗》,一本叫《诗创作》,我也时常读。1948年,我在《武汉时报》发表了第一首诗《爬上汉口》。次年,我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那一年,我16岁。我在大学读的是理工,没读过一年中文,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了不少后来被人称为"愁予风"的诗。
东:唐湜先生曾经用十四行体写过温州的山水。你上次来温州有没有留下一首诗?
郑:我在写一首跟雁荡山有关的诗,但还没有完成。我以前写过不少山水诗。我大学毕业后在雨港基隆上过班,每天面对的是大海,因此写了不少跟大海有关的诗。后来因为喜欢登山,又写了不少跟台湾的山有关的诗。有人说我是游子诗人,也有人说我是山水诗人。这都是标签。
山水诗的鼻祖正是在你们温州当过太守的谢灵运。他是真正的登山家。他有专门用于登山的道具,比如竹杖、鞋子。此人恃才傲物,后来被处以极刑。这样的人,身上有一股贵胄之气,皇帝怎么不提防?"人杰地灵",这四个字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不出人才那就奇怪了。
温州这地方,是江南的江南,它跟杭嘉湖的冲积平原不一样,这里的山,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水从地底一直贯通山顶,所以,你看,每一座山的山顶都能抽长出茂盛的树。
它的生命力不是来自于雨水,而是山里面的活水。这就让我很震撼。我以前也喜欢登山,现在即使不登山了,我还保持着一种登山的愿望。我有时登上一级台阶,就感觉是对地心引力的反抗。登山跟登台阶一样,都是一种对地心引力的反抗。如果说,诗人身上还有一种狂,那么这种狂,也类似于一种对地心引力的反抗。我现在还在写诗,我想我回去以后可以把那首写雁荡山的诗续完。
东:你不到二十岁就来到台湾,刚好碰上了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你能跟我谈谈那个时代的诗人吗?
郑:我到了台湾之后,认识了纪弦、方思、商禽他们。纪弦是现代诗派的开创者,我是九人筹委会中的一员。纪弦比我大十来岁,他的本名叫路逾,他受《现代》诗风影响,所以把它的风气带到了台湾,成立了现代诗派。我们那时对纪弦都很推崇,他那些具有真正现代精神的作品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
那个阶段,也是我的创作高峰期。那时的台湾,有以纪弦为主的现代诗派,以覃子豪、余光中为主的"蓝星"诗派,还有以洛夫、痖弦为主的"创世纪"诗派。
东:因为你不持门户之见,所以在台湾跟其他诗人都保持着一种比较融洽的关系。你的好朋友中就有我喜欢的诗人商禽。1968年,你去了美国之后,还跟台湾诗人联络或交流吗?
郑:我在美国,很少参加诗歌活动。我的朋友大都在台湾。洛夫、商禽、痖弦、管管、张默、叶维廉,我们都很熟。我的年龄比洛夫、余光中他们小,但我的写作时间比他们略早一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阿兵哥。洛夫是海军部队的军官,痖弦和张默也是海军出身。
我跟商禽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商禽本名叫罗砚,早年的诗风,跟洛夫差不多是一路的。有一回,我给他推荐两本外国诗歌理论的书。商禽读了,很有启发。他对太太说,郑愁予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而我如果要引人瞩目,就得长成一棵歪脖子树。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写出了一种散文式的诗,诗风大变,是我之前所不曾见过的。他发表这些诗时,没再用壬葵这个笔名,而是用了新的笔名商禽。商禽的确是个鬼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台湾很多诗人都会画点画。纪弦原本就是苏州美专出来的,像商禽、管管和我,都喜欢画画。我画的是油画。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随陈半丁先生学画。有一次,陈先生带我去拜访一位老画家。他就是白石老人。我在齐白石的画室里看过他的画,也听他聊过书画艺术。
东:我很喜欢你《燕云集》里那十首短诗。你写北京郊区的小螺贝、雪后的西山、白塔、四合院,都给人一种清新可喜的感觉。你的中学时期应该是在北京度过的,对那里也同样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据说你后来去了台湾或美国,仍然对北京的风土、饮食念念不忘。
郑:我在北京住过一阵子,所以我到了台湾之后就写了《燕云集》的组诗。我很高兴,你居然也喜欢这组诗。当年保罗·安格尔就很喜欢这一组。他编选一本中国诗选时,挑来挑去,后来还是选了《燕云集》中的十首短诗。
我是在1968年去了美国。我那时拿到了诗创作学位,也就是国际认可的艺术硕士学位,简称MFA。在美国,我的诗集是可以代替论文的。像余光中、王文兴、白先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学位。我拿到了这个学位,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和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
那时候,我仍然坚持写诗,但很少拿出去发表或出版。我在美国期间,一直很关注中国,惦记的也是国族、生存、兴旺等等这些事情。我刚到爱荷华大学时,夕阳西下,展现眼前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我思念故土,禁不住向着中国的方向跪了下去。那天,我写下了一首诗:《我在温暖的土地上跪出了两个窝》。我一直喜欢周游世界,我每到一处,总是把乡愁装进自己的背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