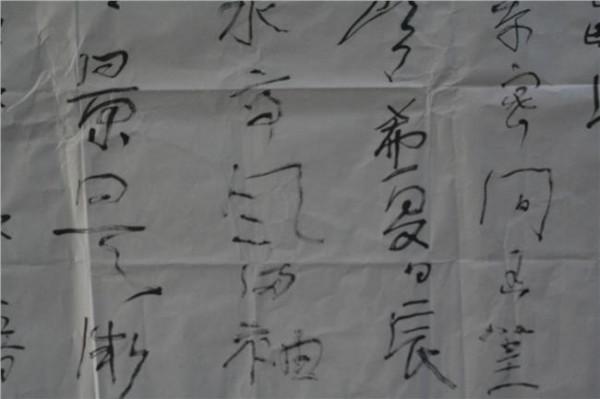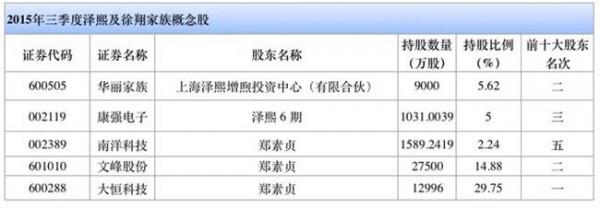阿翔是什么意思 阿翔:故乡是一种远离丨实力诗人访谈
阿翔: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这时候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养,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
阿翔:真名虞晓翔,生于1970年,安徽当涂人。系安徽省文联《诗歌月刊》杂志社编辑。现深圳生活十年。1986年开始写作,曾获2007年《草原》文学奖、2009年第6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一朗读者”2013-2014最佳诗人奖、2014年首届广东省诗歌奖、2015年第二届天津诗歌节“精卫杯”奖。

参与编选《70后诗选编》(上下卷)、《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深圳30年新诗选》等。2011年《少年诗》列入臧棣主编的“70后·印象诗系”丛书,由阳光出版社出版。
2015年《一切流逝完好如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一首诗的战栗》列入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身份的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丛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传奇与诗》列入“读诗人89”丛书,由台湾“酿出版”出品。

隐约的光亮
花语:阿翔好!掐指一算,和您也算认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了,记忆里您对酒情有独钟,那年在北京,一帮诗人聚会您喝多了,被诗人曹野峰和白木架着背上六楼,一晃十一年,现在还喜欢酒吗?对您来说,酒是海水还是火焰?

阿翔:花语好。那年我在京,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见到我醉酒场景,应该是我的第二次。我记得第一次在京大醉,是和广子、安琪等小聚后,广子架着我回去的。而你见到的则是第二次的事了,不过我还真不记得是谁架着我回去的。

那个时候啊,我对白酒情有独钟,与友开怀畅饮,把酒言欢,不亦快意。其实你不知道,我皮肤对白酒过敏,容易出现红斑,虽然这种过敏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适。现在白酒已经戒了,改喝啤酒了,彻底成了一个啤酒主义者,有时候我觉得,啤酒简直就是大海,生命中的永不枯歇的大海。
花语:记得2007年在北京“老故事吧”一次活动中,您含糊不清朗诵一首诗震惊全场,您说话确实有语言障碍,很多时候和您交流需要靠纸和笔的帮助,我也知那是您4岁时发高烧误打链霉素造成耳神经中毒,从而影响发音能力。后来您居然能慢慢能清晰说话了,是怎样做到的?能否说说!
阿翔:天知道。我本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聋哑人,我连手语真的不会。这得感谢我父母在我小时没有把我送到聋哑学校学习哑语,否则我真的不会说话了。我小时候父母不停地培训我说话能力,但最终因为弱听问题,发音就失去了准确性,长大后就定型了。
现在是我太太有足够的耐心纠正我的发音,并强化我的发音记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倾向于沉默,不众声喧哗,唯有沉默给予我内心的强大,给予我慰藉。或者说,不说话,才是一个人的完整。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这时候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养,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
花语:这些年你获奖,似乎2007年离开北京以后,您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小爆发,是因为爱情的滋润,还是深圳那片土地更适合您本身?
阿翔:当年“北漂”生涯,是我陷于写作的低谷期,心态比较浮躁,没有办法专心写作。虽说环境并不是唯一性问题,但影响到心态而如何调整则是个问题。2007年下半年我撤离北京,在湖北十堰隐居了半年,主要调整心态和潜心读书。
2008年春,南下深圳,写作迎来一个高峰期,我觉得并不是爆发,而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的转型,或者说前期的沉寂做了足够的准备。的确,深圳更适于我,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写作上,仍然处于低调而平稳,这才是我要的理想状态。
我的深圳
花语:您始终活跃在南方,深圳的诗歌环境如何,哪些诗人活跃在当下?
阿翔:深圳的诗歌环境氛围很好,深圳除了“第一朗读者”外,还有“新诗实验课”、“诗歌人间”等系列活动。很多诗人、艺术家愿意在“旧天堂书店”、“飞地书局”小聚。要说“活跃”,也许应该说深圳诗人并不是很热衷“活跃”的,而是安静、独立写作,不刻意去扎圈子,不混熟脸,我可以列举深圳诗人有几个:张尔、憩园、颖川、李三林、太阿、樊子、朱巧玲、杨沐子、吕布布、袁行安、田晓隐、刘郎、楼河、骆家……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移民,带有“永恒的乡愁”的意味,永远是“在路上”,他们在深圳形成了群体广泛、创作风格多样的良好局面和文学氛围。
至少,诗歌作为小众艺术能做到这样广泛的包容实属不易。当然,它与深圳这个城市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与这个城市的人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城市特质,深圳诗歌生态才得以获得健康、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花语:诗人从容把诗歌搬上了诗剧场,如何看待她创办的“第一朗读者”?诗歌与朗读是什么关系?
阿翔:可以说“诗剧场”最早出自从容,时间是1999年。2009年从容在深圳音乐厅推出了中国诗剧场《我听见深圳在歌唱》,彻底震撼了观众。从容创办的“第一朗读者”是从2011年开始的,地点最初是从美术馆小型沙龙每年慢慢过渡到胡桃里音乐酒吧、书城中心、深圳大学以及中学校园,能够坚持到7年则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么说吧,“第一朗读者”成了深圳的文化品牌,深圳的一道风景线。最近央视“朗读者”比“第一朗读者”要晚6年呢。
“第一朗读者”成功在于,从容作为深圳市戏剧协会主席利用自身的条件和资源,引进了戏剧元素,朗读与戏剧并不是简单的互动性,而是融为一体,戏剧就是让不同的诗歌语言、肢体语言互相阐释演绎,多方面拓展了文本、身体和空间的表达方式,在与观众尽量做到“零距离”,所以容易吸引了观众。
另外,朗读与朗诵有着很大的区别,朗诵不可避免带有千人一面的旋律式语调,容易令人厌倦;而朗读回归到诗歌的原声,也就是说,如果朗诵就是做作,那么朗读就是要让声音的释意、抒情功能降到最低。诗人于坚说过,“诗歌的声音是隐匿的,它反而是诗歌的原始形式。”
花语:方便的话,介绍下您参与编选的重要年选。
阿翔:相比我参与编选过云南人民版《深圳30年新诗选》、海天版《面朝大海——2012年深圳诗歌大展》、花城版《深圳文学双年选·诗歌卷2014-2015》以及合肥工大版《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等选本,我更愿意提一下《70后诗选编》上下卷,最初是广子、赵卡和我于2010年开始着手准备,并经历了呼和浩特、银川、北京、深圳、长沙等往返交接、讨论和沟通工作,6年后才得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吕叶既是主编也是出品人,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套书不可能做出来的。
我作为编选者之一,与广子、赵卡和吕叶,通过不停的争论、推翻、妥协和最终确定,彼此经历了那一段辉耀而又峥嵘岁月。
编辑的担当
花语:介绍下《诗歌月刊》以及你的编辑工作。
阿翔:《诗歌月刊》复刊于2000年初,它的前身是安徽省文联主办的《诗歌报月刊》,其中“先锋时刻”“隧道”“颠覆”“国际诗坛”“本期头条”等品牌栏目被继承过来,每月一期。在我之前,杨键、庞培、祁国等做过短期的编辑工作,然后经历了曹五木、小荒、余怒、韩少君、黄玲君、余笑忠的编辑工作,使刊物保持稳定水准。
我是2004年春进入《诗歌月刊》的,一直主持“国际诗坛”栏目以及一年一度的全国民刊社团专号,没想到一做就是14年之久。
现在这个杂志目前情况是,李云担任主编,主持“本期头条”和“隧道”,黄玲君主持“现代诗经”,李商雨主持“先锋时刻”,樊子主持“新青年”,刘康凯主持“诗论”,我主持的仍然是“国际诗坛”。《诗歌月刊》今后在风雨中持续前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它。
花语:您是《诗歌月刊》的老编辑,在您看来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和担当?
阿翔: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具有独特的眼光和判断力,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嗜好去影响刊物整体的倾向性。无论是喜好口语诗还是泛学院诗的编辑,容易出现自己的倾向性编辑现象,这样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编辑。既然做了编辑,就该有自己的担当,后退到幕后,你应该是刊物整体的一部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嗜好”去照顾什么,而是敏锐地去发现。
花语:《诗歌月刊》曾集中推送过民刊好诗,您心中的十大民刊有哪些?
阿翔:这些年做了一年一度民刊社团专号,积累下来,我可以列举我个人心目中的十大民刊:四川《存在诗刊作品集》《独立》、湖南《锋刃》、海南《新诗》、福建《诗大型丛刊》《陆》、北京《诗参考》、上海《活塞》、广西《自行车》、深圳《大象诗志》等。也许不止十大,尚有内蒙古《中文》、四川《圭臬》《诗70P》、福建《靠近》、江苏《先锋诗报》等等。
花语:近年来,您在国内大刊上发表了多组作品,能否列举十个您心中的诗歌重刊(官方)?
阿翔:没有什么十个诗歌官方重刊。对我来说,我反而看重公开出版的MOOK(杂志书),比如作家版《诗建设》、长江文艺版《汉诗》《读诗》、上海文艺版《中国诗歌批评》《新诗》、文化版《当代诗》、河南文艺版《先锋诗》、海天版《飞地》《光年》等等。如果非要列举官方重刊,那我只能列出:《山花》《大家》《花城》《钟山》《十月》《红岩》《作品》七大名刊。
故乡的怀旧
花语:您生于江南水乡安徽当涂,虽耳失聪,您的童年和少年是否也如常人般充满丝绸般水质的快乐?当涂的美是怎样的?
阿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乡。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
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
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去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去疯。我的故乡当涂,现在怎么说呢?我离开家乡太久了。“故乡”对我意味着是一种远离,只存在两种意义,一个是在诗歌上的写作,是基于怀旧,那是因为我所熟悉的气息;另一种是意义上的认识,是基于陌生。
实际上,只要打开故乡的百度地图,那个小镇已经面目全非,我实在连大部分的街路都不认识。我生长于故乡的河畔,但地图上河流已经消失了。也许,所谓故乡,就是最终与你毫不搭界的一个名词。
花语:您真名虞晓翔,让我想起虞姬这个悲壮的历史人物,您的姓氏有什么来历吗?
阿翔:我不晓得我这个姓是不是跟虞姬有关。很久以前,我隐约知道我这个姓来自江浙一带,在《百家姓》排名第162位。据说源于姚姓,是姚姓的分支,出自上古三皇五帝最后一位禅让制舜帝,而舜帝号称虞氏,故舜帝又称虞舜,是虞姓人的始祖。
花语:您最早写于何年,因何与诗结缘?
阿翔:1985年那年我16岁,借到一本春风版《朦胧诗选》,里面的那些诗让我感到惊奇,这与我在学校所接受的诗歌教育完全不一样,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诗歌的奇妙,这本书三个月后舍不得归还,这可是我最早第一次接触到的诗歌选本啊,正是这本《朦胧诗选》在我内心埋下了种子,也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惊醒了在内心中沉睡的另一个我。
可以说,我仿佛用另一种方式听到了天籁般的语言之音,敏锐感受到它的奇异,1986年我开始写诗,并以“阿翔”作为笔名,那一年,我父亲给我订阅了《诗歌报》(《诗歌月刊》的前身)、《当代诗歌》、《星星》等期刊;那一年我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写了厚厚的《阿翔的诗》,幼稚得很,两年后搬家遗失了,要是那本手抄诗集还在的话,拿出来你们肯定酸掉大牙。
时间的消逝
花语:必答题,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阿翔:读到一首诗,有所顿悟;读到一首诗,妙不可言;读到一首诗,拍案叫绝;读到一首诗,回味深长,都即是好诗。好诗的标准不在于你写出了什么,你表达了什么,而是可意不可言,这个标准不是“好”与“坏”这么二元对立的分明,你得理解“标准”主要针对期待中的理想读者。我读诗的口味很杂,因为编辑职业原因,决定了我是不带偏见或者有色眼光地去阅读口语诗、学院诗。
花语:“在浮躁而焦虑的时代,为幸存的诗写作而不回避自己的病情和现实的黑暗,当代诗才会完整地暴露缺陷”,这是您在创作谈里的一句话,诗歌确实需要真实,但过份暴露是否会让人感到沉郁?那么,如何暴露,暴露用什么底色,是不是一个很难把控并拿捏的度?
阿翔:这里“暴露”指的是不装饰不粉妆的本色,比如一个诗人,生活在底层,或者经历了现实的黑暗,写诗却一味风花雪月,难道不觉得虚伪吗?说到底,诗歌不可能脱离政治,哪怕一个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观(包括独立思考、判断、信仰),“不回避”恰恰说明很多诗人刻意回避了“诗人何为”的拷问。至于是否让人感到沉郁,那也未必,毕竟真实不一定都是沉郁的,取决于读者怎么去理解。
花语:您在创作谈里说“通过眺望时间的消逝,或许,时间上的过去决不是水流去向的目的,而诗歌处于辗转、衰老的消磨中,才能是内心缓慢的倾述,即使倾述有时在缺陷上不完整。”时间对您意味着什么?在时间与诗歌的拉锯中,您是否感到了苍老?
阿翔:时间对我意味着消逝。就拿一首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一首诗的完成即成为消逝,谁也挽留不住,即使稍稍停留一下,却已失去了当时写作的冲动、构思、激情,就像失去了一道闪电那样。如果想重温,无非是剩下一片依稀的记忆。就年龄上来说,我真的老了。但我希望内心永远年轻和朝气。
花语:推介下您的重要诗集。
阿翔:我公开出版过《少年诗》(阳光版)、《一切流逝完好如初》(长江文艺版)、《一首诗的战栗>(山东文艺版)以及《传奇与诗》(台湾“酿出版”)。但我愿意把《一切流逝完好如初》视为个人重要诗集,这里允许我套用广告语偷懒一下:“该诗集收录了阿翔自2010年以来的部分作品,内容涉及东西文化、写作阅读、身份、生活、异乡人经历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诗路历程及其在诗歌写作上的追寻与探索……展示出一个优秀诗人如何在纷繁的当代新诗进程中有力地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性、有效性。
诗人丰厚的学养和语言敏感,助力他对诗艺的深入考量,使其语言实践中的书写模式和文本细节,即使放在多年以后再看,依然具备写作现场的鲜活性和竞争力。”
花语:马不停蹄地奔走、写作,是否也有写穷的时候,对于写作,还有哪些期许和目标?
阿翔:我肯定有停顿期或者是停滞期,我觉得顺其自然为好。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不断提高一个标准,标准是自我修炼的层次。在有限和尊重的少数朋友当中得到高质量的交流和有效性。这些年,从“拟诗记”系列到“剧场”系列,再从“诗”系列到最近的“传奇”和“计划”两个系列,这几个系列意图很明显,就是在写作更新中使我从琐碎化状态脱离出来,也许朋友们会意识到,对于未来的消逝而言,它就是一个漫长而又踏踏实实的写作计划。
不忘初心
花语:王家新有这么一句:“终于能够按照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照内心生活”,这是很多诗人的现状,现在的您,内心与现实是否还有反差?
阿翔:当然有。“不能按照内心生活”其实不只是受到环境的条件限制,更多的是为生活奔波你得做出选择。永远不要把生活想象得太诗意,否则失望越大。你首先要把生存搞好,搞不好自己的生存而一味地写诗,无疑你是失败的。在生活中你必须放下诗人这个蛮可笑的身份,难道你吃饭、出恭时还不忘诗人身份?那累不累啊?也许,内心与现实的反差,可以成为诗人继续努力的必要的动力。
花语:是否相信爱情?如何在平庸的生活里让爱情保鲜?
阿翔:我仍然相信爱情,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让爱情保鲜的,也许因为是不刻意,或者说我和我太太在生活上、交流上达到高度默契吧。结婚这么多年,我和我太太仍然处于恋爱状态,这话听起来有点酸,但事实如此,别的就不多说了,请允许我保留一点隐私。
花语:我印象里您是一个朴素、实在又容易亲近的人,在您看来,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如何做到人品与诗品的合而为一?
阿翔:其实骨子里我是一个矛盾、迟疑而又怀疑的人。在我看来,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不忘初心,很多人出发在路上,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但我认为,人品不能决定诗品,毕竟,人品展现“美好”的同时,也有“黑暗”的一面。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到人品与诗品的合而为一,生活中我是丈夫、儿子或者一个啤酒主义者;写作中我是一个冥想者,或者说是另一个的我。这么说吧,我终究是一个隐秘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诗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诗歌圈,我这个身份是公开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的现实中,我却刻意隐瞒了这个身份,就像灵魂在人群中不轻易外露出来,我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低调而平稳地生活。
这样说并不是强调诗人的分裂,而是说,诗歌是一种自我的修养。
简评三则
阿翔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后民间诗坛的活字典。他继承了汉语诗风中游吟、登临、宴饮、唱和、赠答、艳情等传统里迷人的部分,同时又融入了繁复、抽象、迷离的现代元素。他袖子里有魔术,耳朵里有钟,眼睛里有大美,胃里有一个江湖。
——朵渔
尽管我们不能这样解读一个诗人,但对于阿翔也许是个例外。特殊的身份、经历和体验,使阿翔的诗歌总是处于被书写的漂泊状态。无论语涉途徙或还乡、宿醉或独醒、情或性……都呈现出一种不可模拟的奇异与诡秘。
——广子
阿翔早年诗歌中的才情,在新近的写作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诗人在人生经验的积累与对事物的洞察中找到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出口,并通过质朴的言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中年气象。
![连晨翔的歌 [40P]连晨翔的女朋友连晨翔图片||晨翔图片](https://pic.bilezu.com/upload/4/4e/44e7ac325747f793f5933c660ae36a89_thumb.jpg)

![湖南何报翔最新任命 何报翔李友志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2/a6/2a6f02e8e87a641d6b4d61826b3d861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