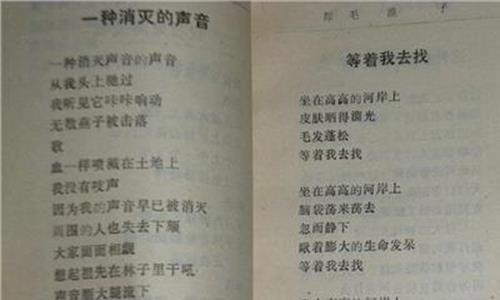钱玄同双簧信 钱玄同和刘半农唱“双簧”
《新青年》安家于北京大学之后,为了吸引众人围观,扩大社会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并由此演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从书斋推广到大众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新青年〉图传》还原了这场自导自演的“双簧”。
《新青年》迁到北京之后,不论编辑方法还是内容形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尤其第4卷第1号,堪称“改头换面”的一期:从这一期开始,杂志只刊载白话文,并且采用了新式标点。

这时,《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有点尴尬,除了自己这边在锣鼓喧天地“呐喊”,还没有一个“敌人”出来迎战,传统卫道士们还没有看见他们的热情和魄力呢。身怀绝技,斗志昂扬,却没有对手,这是何等寂寞。
独角戏唱起来没劲,那不妨攻打一下假想敌。就好像双方辩论一样,必须一方陈词,一方反驳,双方互争互斗才能热闹好看。于是,新文化阵营的刘半农和钱玄同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

自导自演唱“双簧”
“双簧”的经过是这样的。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

而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由刘半农执笔,通篇所举观点都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钱玄同很有旧学的底子,模仿旧文人的口吻惟妙惟肖。他在化名王敬轩的信中通篇攻击新文化人,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也曾任教北京大学的林纾:“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而针对“王敬轩”的言论,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可以说,由钱玄同、刘半农执笔的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形成了水火不容的论争之势。这样一来,林纾算是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骂战旋涡。
林纾跃身上阵
其实“双簧信”向林纾挑衅的意思很明显。给“假想敌”取名“王敬轩”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大有深意。林纾,字琴南,号畏庐。从字面意思上来说,“敬”对“畏”,“轩”对“庐”,“敬轩”其实就是隐射林纾之号“畏庐”了。钱、刘二人给守旧者命名“王敬轩”,等于把战斗火力直接瞄准了林纾。
为什么偏偏挑选林纾充当头号敌人呢?作为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成就,林纾是公认的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激进”“求异”的新文化运动,老成持重的林纾本来一直保持着沉默静观的态度。但在“双簧信”的明显挑衅之下,他终于按捺不住,跃身上阵了。林纾不仅直接写信给蔡元培要求校长主持风化,还通过撰写小说来指名道姓地痛骂新文化人。
林纾利用小说回应
1919年2月和3月,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了林纾的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这两篇小说以文言的仿聊斋体写成,都是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镇压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以及刚从美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正饮酒作乐。
他们一边喝得兴高采烈,一边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施展武力制服了三人。
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不断,简直丑态百出。《妖梦》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居然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
只见学堂中熙熙攘攘,全是魑魅魍魉。其中校长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为鬼怪中的突出者。他们高挂着“毙孔堂”的招牌,大肆妄谈废除古文,毁弃伦常。终于,白话学堂中鬼怪们的乖张狂妄言论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被他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在种种关于暴力与杀戮的幻想之中,林纾似乎获得了最大的快意。
1919年3月18日,林纾又给蔡元培写信,希望他以校长的身份约束教员的“胡闹”。林纾指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说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对于推行白话文的主张,他痛心疾首,危言耸听地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林纾那边的回应多有谩骂攻击之词,这边新文化阵营却不免又惊又喜。期盼中的敌人终于出现了!“骂战”必然引起社会关注,何况又是林纾这种已有盛名的人物。为打退林纾,他们纷纷揭露林纾在《荆生》中呼唤的“伟丈夫”就是手握兵权的徐树铮——段祺瑞政府中的安福系干将。
《荆生》见报后,陈独秀在自己主办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说“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评价这篇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从此,荆生被阐释为武人政权或军阀的化身,而小说作者被斥为专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这样一来,林纾被置于倚靠权势的无耻境地,而新文化阵营因成为被压迫一方轻易获得了公众的同情。
另外,针对林纾指责北大的言辞,蔡元培的回答义正词严。在名为《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的复信中,蔡元培不仅反驳林纾,也向整个社会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对林纾这样的遗老而言,提倡白话文动摇了儒教传统当然大逆不道,但蔡元培看来,在主张个性,学术自由的当今之世,新文化运动自有发展之道,何必拿着礼教、道德的威名加以打压?蔡元培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响当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着蔡元培流传青史,不知被后人转载引用多少次。
发展成为公共话题
林纾和蔡元培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他们之间发生的问答、争辩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恰好,那时候坊间又流传说教育部要驱逐大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等人。许多报纸纷纷报道并刊登林、蔡的言论往来,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
而且,各报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把“林蔡之争”冠上“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原先只是囿于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在新闻媒体的煽风点火之下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众声喧哗,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林纾没有预料到,他对新文化人、对《新青年》的一番批判、攻击会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并且发展成为公共话题,无形中又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事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林纾还是颇有君子风范,后悔自己怒火中烧时的口不择言。
他亲自写信给各个报馆,承认自己骂人的错处。可见,林纾还是一个敢作敢为、颇有担当的人物。然而,林纾只对私人意气用事认错,他仍倔强地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他说:“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在新潮涌动的民国,年纪老迈的林纾实在难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