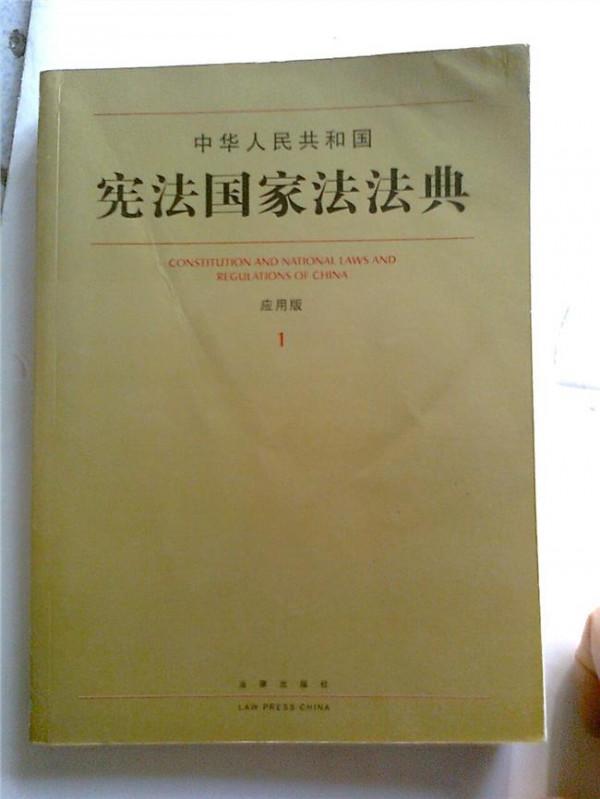叶澜教授名言 《社会科学报》:叶澜:构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叶澜是个可爱的老太太。短短的卷发,无拘无束,一如她的思想,不拘一格。她的穿着向来简洁干练,很多时候都是行色匆匆“在路上”,如果你这时候打电话,一定对她的快人快语更加印象深刻。她喜欢丝巾,有时候在随意的装扮下,一个小小的点缀,会恰到好处地透出她的精致。

在叶澜的身上,我们很难嗅到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太太通常会有的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相反,她给人的感觉是那样清新,透着理性的光泽,这是一个常年从事思想事业的人所特有的深邃沉静的韵味。

当她谈起倾注毕生心血的教育事业时,你能很容易感受到强烈的赤子之心和追求理想的激情。无论是在谈话、还是在微笑的时候,她的嘴角都是微微下压,显示出一种有力的轮廓,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和无法动摇的坚定感。但是,当她和你打开话匣子,你能立刻感觉到她的热忱和亲近。

生活经历给了她浓浓的平民情结
叶澜先生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之后留校任教至今。按照她自己的意愿,本打算本科毕业之后,继续攻读北师大的硕士,追求自己的理论梦想。

或许那时候的叶澜已经对自己的理论天赋有了朦胧的自觉,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从事教育实践是最好的选择。或许可以说,那时的叶澜对教育实践并不了解,更谈不上所谓爱好。然而,系领导劝她还是先留校,因为研究生毕业同样还是回高校任教。就这样,叶澜留在了华师大小学学科语文教学法教研室。
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新任教师必须到教学实践岗进行锻炼。叶澜被分到了华师大附小任教。然而,第一次的教学实践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她接手了一个五年级班的班主任,而这个班是当时附小有名的“乱班”,在叶澜之前,已经有三位班主任铩羽而归。
爱笑的叶澜时常被顽皮的学生弄哭,这让她有了深深的失落感,也让她反思:“教育系的高材生,学得算不错,为什么到实践中就没有用呢?”但叶澜反思的结果是自己并没有问题,而是学生太顽皮,自己本来就长于理论,如果任教于大学,肯定能胜任。叶澜没有怀疑理论的价值,没有因为实践的打击而丧失对理论的信念和兴趣,这无疑又是幸运的。
第二年,叶澜在附小二年级继续任教,她逐渐适应了教学的生活,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真正开始有了体悟。“文革”中,她被下放到大丰干校劳动锻炼一年,结束后正好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叶澜的大学教学生涯就是从教工农兵开始的。1974年,作为上海第一批援藏教师,叶澜凭着一腔热血走进了西藏,西藏的贫穷和基础教育条件的落后让她深感震惊。
基层教学实践、干校劳动、接触工农兵学员、援教西藏……这一系列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天马行空”的岁月,几乎荒废了叶澜系统的学术思考,但也正是这种复杂的基层经历,让她渐渐有了浓浓的平民情结,正如她曾经写过的一篇短文——《我的基础教育情结》所示:对苦难的同情和对平凡的关注,正是她几十年后献身基层教育实验的原动力。
同教学实践“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挫折,让她体会到了小学老师的辛苦,使她对小学有一种感情,她觉得这些老师是不应该被轻视的,小学是不好教的。
她也真正理解了那些琐碎得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的基层“园丁”,“他们真的是不错的人,他们有热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有追求的,所以是可以改变的。
”这种贴近和理解给了叶澜一种信念和信心,使她不仅始终以乐观的态度观察和参与饱受批评的中国教育改革,更能够沉下心去和小学、中学的老师打交道。“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从来没有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那种情感”,叶澜如是说。
在教育中发掘生命的价值
1980年,叶澜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南斯拉夫,她在南斯拉夫的导师,第一次见面时就向叶澜介绍说自己在城市、山里和海边都有房子,这完全出乎叶澜的预期,因为那时的中国通行的观念是奉献,个人价值微不足道。
南斯拉夫和中国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一直强调教育的重心是为社会服务——从原来的为政治服务,到现在的为经济服务;而被我们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却能够如此突出个人价值。中国的教育之关注人,是因为人将来要到社会中去,教育的出发点是把人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对象;南斯拉夫的教育理念则关注个体的内在生命价值。叶澜直言,“这个观念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1982年叶澜回国后,就开始潜心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个经典的问题。传统观点解释影响人的发展是“三因素论”,即遗传、环境与教育。叶澜发现,人的发展和动植物的生长有着很大的区别,人的发展首先是他生命的发展,人类个体的选择、他的一切经验,都会参与到他此后的发展之中。
1986年,叶澜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一文。
文章突破了传统“三因素论”中人被非自主因素左右发展的教育理念,第一次提出,教育中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在促进其自身发展方面的作用。文中强调:遗传因素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随着一个人主体力量的增强,他对环境的选择和改变能力会越来越强;最后真正决定一个人发展命运的因素是人自己。
“因此,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使得人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观点在个性尚未解放的80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
即使今天,在教育学著作中也不多见,教育实践则离得更远。(下转第5版)到了90年代初,一场更伟大的变革正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悄然发生。1993-1994年左右,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教师队伍中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也纷纷“下海”,甚至同叶澜进行合作研究的一所小学,校长都被区教育局派去搞房地产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叶澜再度看不懂中国,感触为什么政治、经济的浪潮一起,首先就冲击到教育?于是叶澜开始研读中央文件,“我突然悟出,一个大时代,中国发展的大时代到来了!
”叶澜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开始关注个体的价值,让有能耐的个体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时代需要独立的个人,需要善于抓住机遇的个人,需要敢于挑战的个人,这些品质就是时代需要的新品质。
时代精神要求教育培养的新人应具有新时代的新品质。一篇《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教育研究》,1994年第10期)宣告了叶澜新基础教育的开篇,“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开篇,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对‘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整体性认识与策划是从1994年开始的。
”也可以说,叶澜的新基础教育改革是从对时代的重新认识,从时代对人的要求的重新认识开始的。“对个人发展的关注和尊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这个标尺同样可以应用在教育身上,教育的现代性就看它对个体的尊重程度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多少空间,而不再仅仅用人力资源的观念来衡量教育的社会功能。
”“这是我的起点,绝对不是个人心血来潮,而是对大时代的感悟以后,才意识到教育的革命性大变革的必然。”
随着教育实践的逐步深入,叶澜认识到,把课堂教学目标局限于发展学生认知能力,是传统教学论思维局限性的突出表现。在这种课堂模式下,老师着力于完成教案,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职业倦怠和课堂沉闷成为普遍现象。
叶澜提出: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重要构成。对于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其学校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当下及今后的多方面发展和成长;对于教师而言,课堂教学是其职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它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师对职业的感受与态度、专业水平的发展与生命价值的体现。
总之,课堂教学对于参与者具有个体生命价值,每一堂课都是教师和学生生命活动的构成。从这个高度,叶澜写成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教育研究》,1997年第9期)。
叶澜在文章的结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向:我们把教学改革的实践目标定在探索、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师生才是全身心投入,他们不只是在教和学,他们还在感受课堂中生命的涌动和成长;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才能获得多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教师的劳动才会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也只有这样的课堂才不只是与科学,而且是与哲学、艺术相关,才会体现出育人的本质和实现育人的功能。
这篇文章迅速在理论界传开,特别是在一线教师中产生广泛共鸣,课堂教学中生命角色的缺位问题受到大家重视,此后,“生命”一词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大众语言,成为不少教育理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
“二十年磨一剑”扎根教育实践
1989年,上海市普陀区中朱学区的领导找到华师大教育系,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帮助他们总结十年教育改革的经验。叶澜称这是她“读实践智慧”的开始,“我只是去解读他们,认清里面的规律,我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实践智慧。
”叶澜将心得写成《学区系统终态变化的整体反思——中朱学区近十年教育实践与经验研究的总报告》(《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而整个调查报告形成了一本书——《走出低谷》(教育科学出版社),“刘佛年校长(时任华东师大校长)评价说,绝对不亚于西方的教育研究,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用研究的眼光去读实践,是对叶澜基本功的一次锻炼,也让她看到了学区领导、老师和校长的智慧。
而叶澜不经意的一句话,促成了她用理论指导教育实验的真正开始。叶澜说,我们现在做完的还只是“走出低谷”,我们怎么通过改革取得教育质量的提高,进一步“登上高峰”呢?登上高峰一定要开展教育研究。洵阳路小学的校长就凭着叶澜这句话,请她继续帮助推进改革。叶澜说:“我发现有的时候实践工作者对你的一句话真的很在乎。”
叶澜有了机会真正相对独立地从事教育实验。根据自己的“个体发展理论”,叶澜认为,过去的教育都强调对外看,而忽视一个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建构和寻找自己的人生发展道路。而中小学教育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是使他知道自己是谁,将来要成为谁,他还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谁,因此如果新的教育能把学生的潜能和自我意识发掘出来,孩子将会有突破性的进步。
这种理论分析,看起来有道理,实践中能做得到吗?于是叶澜设计了一个课题: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课题的核心就是验证我已形成的理论在实践中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将这个理论转化为实践。”
从学校实践的基本构成出发,要从教育中找回生命,一个是课堂,另一个是班级,所以叶澜的改革从课堂教学和班级生活开始。原来的课堂基本都是老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学生几乎没有时间自己读书或者思考。
于是,叶澜提出,首先要把老师的讲课时间减到一节课的三分之一,留下大量时间让学生自己看书、朗读和交流,“当时来看,所谓讲课占三分之一并没有根据,只是感觉三分之一足够了。”接下来作了很多探索,包括教材的重组,怎么来教等,中心是如何让学生主动。
班级活动的改革同步展开,从学生自己组织班级活动,到小干部轮换等学生自我管理改革,这些实际上都是新基础教育在班级层面改革的雏形。这项研究大概进行了三年多,最终写出《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上海教育科研》,1996年7、8期连载)。
这个实验是一次探索,并不精细。然而叶澜后来广受关注的“新基础教育”改革就以这样一种简单得甚至有些粗糙的方式开篇了,1994年叶澜到外高桥小学正式开展了更加系统的试验。“这是学校教育全面的整体的转型,用什么词都难表达,我说就叫‘新基础教育’,这个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清楚。”
“教学、班级活动和学校管理构成了完整的学校实践”。更让叶澜欣喜的是,教改不仅没有影响学生的学习,他们的考试成绩反都大幅提升。叶澜深信,只要真正把孩子教好了,考试必然会好,“现在是用最笨的办法在搞应试,把孩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主动学习,成绩不可能差。”
1994年,外高桥的实验刚刚进行了一年,叶澜被聘为华东师大副校长,她在积极利用“职权”为教改实验创造条件的同时,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离不开业务,离不开研究,“我觉得做一个副校长,大概很多人可以代替,但我头脑里的东西没有人能代替,我想形成学派的理想也没有人能够替代。”于是叶澜下定决心,主动离任,这在当时的教育学界成为美谈。
初创阶段的成功没有让叶澜止步,她开始思考:上海地区有效的做法,在其他地区是否可行?“新基础教育”很快进入第二个阶段:发展性研究阶段,叶澜又用五年时间扩大参与实验的学校规模,并进行理论的深度形成。他们用成果发布会的方式吸引了愿意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学校,江苏、福建、山东、广东,甚至海南都有学校专程找来,共有50余所学校,“这让我感觉到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改革的渴望!”
改革全面拉开之后,叶澜感觉到研究团队的理论准备已经相对成熟了,但是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的完全转型还没有实现。于是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又一个五年的成型性研究阶段,确定十所核心学校,全方位地对学校领导与管理体制的变革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从探索到发展到成型,经过十五年的探索,叶澜终于可以自信地宣布,找到了一条在现实条件下通往理想的学校改革之路。“我的价值就是踏出一条路来,它特别艰难,但是它可行。十五年来,这条理想的道路越来越清晰,改革成型的这十所学校就命名为‘生命·实践’合作学校”,叶澜动情地说。
成型研究后本来可以退出了,但是叶澜觉得心里不踏实。她说,从沙漠变成绿洲非常艰难,但是绿洲要退化到沙漠却很容易。她不希望自己十五年的心血无疾而终,于是决定再作三年扎根性研究,“就是要把根深扎到学校的泥土里去,要带出一支智慧、自觉的校内队伍,从学校领导到团队、到教师骨干,整个系统形成一个内部的研究力和生长力!”
终成正果:“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还有一个更深的梦想潜藏在叶澜心中,那就是形成自己的教育学派。2004年前后,随着叶澜及团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逐渐成熟,她感到理论形成本身也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系统化的。“我突然悟出来,光有生命的教育理论还不完整,还要加上实践,所以我提出就叫‘生命·实践’教育学”,说到这里,叶澜的眼中有一种母亲谈及自己儿女的深情。
叶澜在一次重要采访中,决定把自己的学派称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这既树立了奋斗目标,也为这个团队近二十年辛勤付出所收获的精神成果正式“注册”。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叶澜的理论越来越清晰,在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比较中得到澄清;改革的试点学校越来越成熟,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商标”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009年完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论丛(“回望”、“立场”、“基因”和“命脉”),叶澜称,“在扎根阶段就开始系统梳理教育学研究的一系列前提性问题,像清理地基一样出了四本书”,论丛的标识是“冬虫夏草”,这是叶澜内心深处西藏情结的流露,她觉得,冬虫夏草是最中国的,而且有动植物间的转化,就像教育的作用之于人,“转化就是教育的创造”。
从去年开始,叶澜团队又在策划出三套论著系列。
第一套是“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第二套是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研究的系列丛书,主要跟“新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相关。第三套是“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学校的学校变革史,每个学校一本,加上叶澜跟一部分校长的访谈录,“这个访谈录,我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创造教育新天地的人们》”。三套丛书30本。
“2014年是我们提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第十年,三套丛书同时出版,呈现出我们‘生命·实践’教育学从理论探索,到对当前学校变革的整体研究,到最后一个一个学校转型研究的系列形成了,同时也呈现出我们学派的独特品质与风格。”
叶澜说,她不大喜欢圣化、英雄化的东西。一个人的改变要通过自己日常实践的改变才能完成。同样,靠一次、两次运动是不能解决教育问题的。埋怨,不会出一个新世界;你要去改革,要去做,精神面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叶澜先生是一位君子,践行乾道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做事情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定力。这在当今浮躁的时代背景下,殊为难得。他们这一代学人,可能大多数已经停止了专业的学术生涯,安享天年,而叶先生依然以古稀之躯,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东西奔走,左思右想,“上天入地”,乐此不疲……(实习记者潘圳对本文亦有贡献)
■学者档案
叶澜,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她从事教育学研究已40余年,1994年她首创并持续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致力于学校整体转型变革研究,至今已近20年,各类合作学校百余所;2004年她提出并持续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致力于当代中国教育学重建,已从专题研究进入专著研讨阶段。
在理论与实践交互创生的过程中,叶澜教授提炼形成了多部(篇)学术成果,其中专著:《教育概论》(1991年)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1999年)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新基础教育”论》(2006年)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论文:《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1994年)、《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理论与实践》(2004年)、《“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2009年)等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