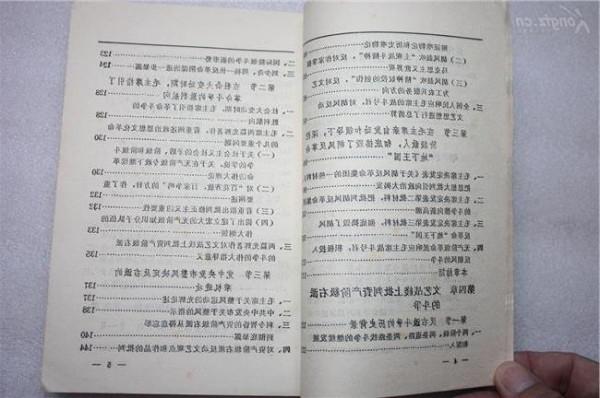周扬与丁玲 对峙半世纪周扬与丁玲为何至死互不原谅
如果说周扬的悲剧,是权力意志下被纠曲的悲剧,那么丁玲的悲剧是政治吞噬的悲剧。
丁玲是我国惟一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代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协副主席,任《文艺报》主编,建国以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

这是各种丁玲传记中所附的丁玲年表。不难看出,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其显赫、何其辉煌。我感受到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从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里,看出她是一个忠实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从她的抗争史中,她的创作生涯、她的坎坷人生,感受到她是一个未完成却受到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

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到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乃至后来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把她“流放”到北大荒多年。多次的政治运动都冲击了丁玲,给她带来了许多精神甚至肉体的磨难。

在十年劫难中,长期受怀疑、受歧视,备受打击。纵观丁玲一生真可谓是一波三折。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是一个挫折,1955年至1957年是再次挫折,1979年返回北京,平反后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重新发表作品。因反自由化受到冷落,这是最后一个挫折。
在我感叹着丁玲的悲剧,又将书架上那套多卷本的《丁玲文集》翻读了一遍。丁玲早在1928年写成的《莎菲女士日记》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杰作,几乎成了后来检验、评说、衡量、评论她以后作品的标准或前提。
这部极富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众多争议的小说几乎陪伴她一生,使她成名,使她失意,使他靓丽,使她灰色,使她好评如潮,也使她谤言四起。《水》、《韦护》、《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形成了丁玲创作转型的标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被标志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丰硕成果。平反复出后的《杜晚香》也显示出老一辈作家的宝刀未老。直到1986年3月4日病逝。活了八十二岁。作为一位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十六年了。
据报载,丁玲的故乡湖南省常德市修建一座丁玲纪念馆。读着,由此而诱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些思考,不妨从《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和《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两部书目中,开列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女作家名单(按出版时间为序)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海音、杨绛,在“双百”名单之外还有冯沅君、苏青、林徽因、庐隐、白微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每位女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创作成果的不同,文化含量的不同及生命长短的不同一生的际遇是绝然不同的,即是女性作家的不幸而又是女性文学的幸事。
将丁玲放到这串名单里来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写出才气诗情喷发的《生死场》的萧红,与鲁迅先生曾有着父女般的关系,曾与萧军有着生死之恋而与端蕻木良的情感纠葛,写出《呼兰河传》、《马伯乐》。
当大量的作家艺术家奔赴延安,萧红终没去成延安,而31岁客死香港。五四才女冯沅君20岁就写出《卷箷》一举成名,倍受鲁迅先生赞赏,30岁转入古典文学研究、教书一生,几乎被文学界遗忘。
而世纪老人冰心,终身不入官场,以作家身份活着,以文坛老祖母慈祥的公众形像活成了一代大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活化石。
而丁玲处于政治旋窝之中,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就很有典型的意味。尽管丁玲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中历次受到冲击,恰好提供了她频繁的亮像给公众,其间包括以《莎菲女士日记》开始成名,多年后又旧事重提受到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讲话》发表后的硕果活标本,近年又被认作是红色文本的作俑者与女性文学毁灭者的教训,被指责为丁玲女性作家视野消失,被异化的典型。
正反也好,左右也好,是非也好,故使她的声誉保持或上升。
在稍事平和的时候,丁玲自己却又旧事重提,致使与沈从文的恩怨再一次成为一桩公案,丁玲一辈子总是搅在各种是非里面,但让人感觉生性好斗!客观地说,这是丁玲的不幸,也是丁玲时常被人提起的事因。
无论丁玲身为作家要革命,还是先说丁玲右,再说丁玲左。丁玲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被置于政治旋窝的中心没有找到一个充分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创作被迫中断,艺术受到沾污,需要表达而不敢表达或无力表达,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做悲剧,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丁玲逝世以后的十六年的今天,我们来深入地反思,并非没有意义。
将丁玲的悲剧归结为政治吞噬悲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丁玲的不幸与苦难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分不开,二是在真理与缪误 ,善与恶的斗争旋窝中,在自我被毁灭的过程显示出有价值的东西。丁玲的悲剧使联想起巴黎公社社员墙中的那位女神,那一道悲壮的景象。
尽管人们总是习惯看到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的相争相斗 ,以为没有这样的情形,丁玲也许会永远平安无事,而事实上,凡与政治权力意志相左的人,不管是谁,丁玲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时,几乎令所有文化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但党中央的一声令下,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要理解。
尽管左联时期,鲁迅诗悼丁君,尽管丁玲是延安的宝贝,“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正是毛泽东题赠的诗,那又能怎么样。丁玲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
任何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及文化形态,总是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与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阶段,先是高度的封闭统一,后是“文革文化”的极度愚昧狂热,再是多元但脆弱混乱,始终伴随着新旧碰撞的动荡迷惘。
而处在政治旋窝当中的丁玲就很难逃脱“社会政治悲剧”的结局。丁玲吃尽苦头、历尽劫难,重新回到文艺岗位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以超常的宽容与惊人的自省,重新对自己进行了审视定位,这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丁玲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见《原上草》第342页至344页)。丁玲说:“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
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泽东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
’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
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
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
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
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
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
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至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到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看来,这段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是真实可信的。然而遗憾是,至今没有发现在周扬的文章中见到过有关他与丁玲关系的文字。 四周扬与丁玲之间为什么会鸿沟横亘,难以逾越,水火不相容呢?半个世纪的对峙,至死彼此互不原谅呢?周扬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
周扬与丁玲本应该是朋友,而不应该是对手,都是湖南人,都是毛泽东的同乡,毛泽东历来看重同乡、同族、同学之类的关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毛泽东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地成为两派,什么是他们两个结怨的原因呢?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
性格,这才是许多时候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整个进程。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纪律更为内在地决定着人的行为。周扬与丁玲是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
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名作家、大作家效应。
丁玲作为女作家,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结合,这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
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来与周扬抗衡。1948年周扬邀丁玲一起做文化领导工作,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
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矛盾激化,而导致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
正好说明丁玲是周扬的对立面,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
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公正地说,对一些人认为“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说法有失公允,陈明写《事实与传说》以此辩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完全是周扬的责任,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