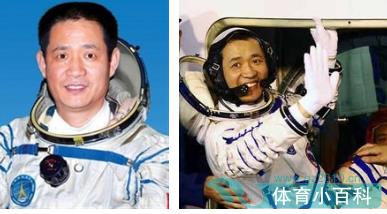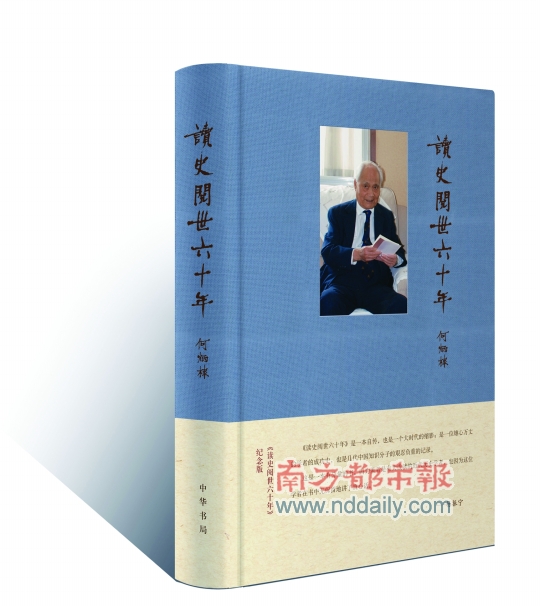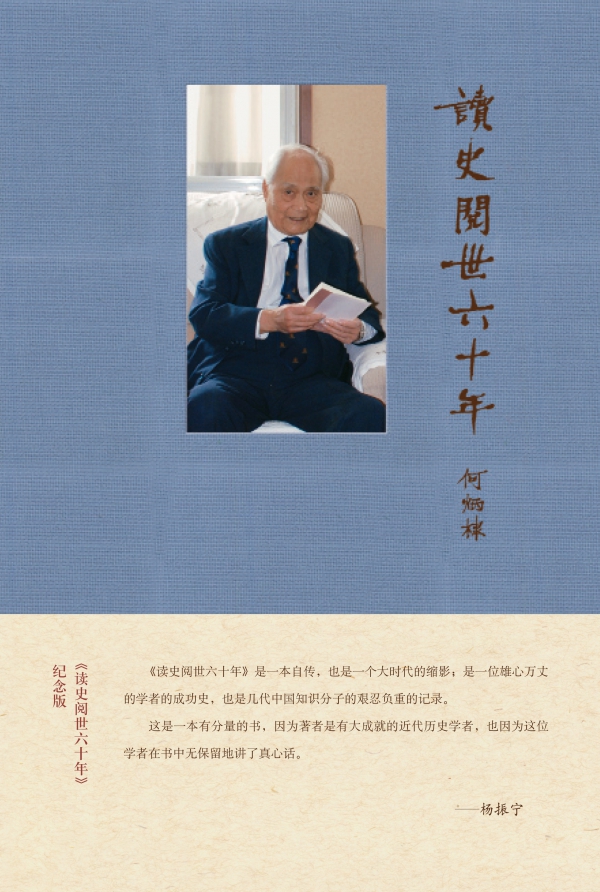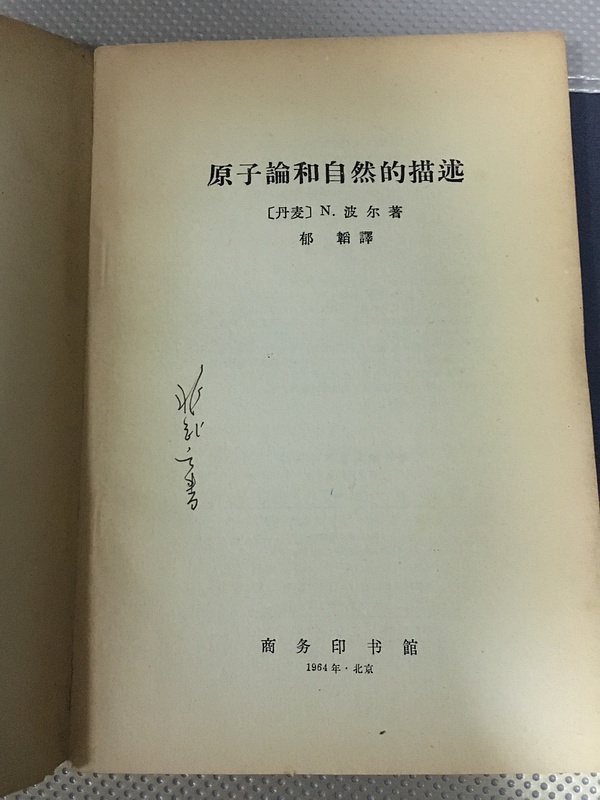聂绀弩与西安 冷眼阅世:世间已无聂绀弩
《冷眼阅世——聂绀弩卷》,聂绀弩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版,20.00元。
和同龄人提起“聂绀弩”这个名字,许多人不知道。聂绀弩却是我和文化老人拉近距离的“法宝”,屡试不爽。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提起聂绀弩,老人家总会觉得你和他并没有代沟。在北京黄苗子家里,我第一次看到聂绀弩的手迹,字写得清雅,又听黄苗子讲“三红金水之斋”的故事,像电影镜头一样记住了。
在香港罗孚家里,听罗孚讲聂绀弩和梁羽生下围棋下到忘乎所以的趣闻,我们都笑了。罗孚曾在人生最困顿之中全心地编《聂绀弩诗全编》,只因明白聂绀弩的诗是百年一人。
聂绀弩写过杂文小说,也写新诗旧诗。聂绀弩的小说没有杂文名气大,夏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罗孚回忆,那篇文章是他按夏衍的意思代写的。聂绀弩的新诗显然不如旧诗,罗孚编的集子收了聂绀弩的新体诗集《山呼》,最费心研究聂绀弩的侯井天也许有感于此,才自费编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聂绀弩写旧诗,本属游戏。1959年他在北大荒劳动时,上级指示每个人都要作诗,说是中国要出多少李白、杜甫。聂绀弩遵命而作,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交上去,领导宣布他作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一场荒诞的游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聂绀弩生来有诗人的气质。一个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一个老共产党员,只要他稍稍屈尊,在哪一边都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他不是当官的好材料。他甚至也不是当报人的好材料,据说,他在桂林编《野草》月刊,好吃好喝,入不敷出时,竟挪用稿费。
《野草》关门大吉后接手《力报》副刊,后来帮储安平编《观察》“文艺版”,老毛病还是没改。在香港《文汇报》当总主笔时,和梁羽生在《大公报》下围棋,晚上只顾弈战,不想回《文汇报》写他分内该写的文章。
在北大荒劳动,因为抽烟,把房子给烧了。胡乔木诚心诚意为《散宜生诗》写序,以他的个性,把胡序臭骂一通的传闻,外人信以为真不是无缘无故的。日后罗孚在《聂绀弩诗全编》中再收热情洋溢的胡序,和聂绀弩放荡不羁的个性是不相配的。
阮籍、嵇康、金圣叹如果生于斯世,相信会和聂绀弩称兄道弟。他的人生苦难和不羁个性仿佛是为了写诗而准备的,万事俱备之时,等到北大荒吹起诗意的东风,此时的聂绀弩已经56岁了。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写诗却随心所欲而不违背诗的格律。在格律上,聂绀弩虚心向同龄好友钟敬文苦学。钟敬文为学为诗一丝不苟,“严师出高徒”,聂绀弩青出于蓝,终于诗名显,而钟敬文更为人知的还是学术。
我最爱读的聂诗,是他和朋友吟咏相赠的那些,诗外有酒意,有笑声,更有患难与共的深情。他哭周总理、挽雪峰、悼胡风,字字有泪痕,无不让人想起时代之痛,民族之伤。而他谏钟三(钟敬文)、念高旅、赠梁羽生、戏赠史复(罗孚)、调吴祖光、寄尊棋(刘尊棋)山中、遇有光(周有光)西安、题小丁(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可见他与朋友交游之乐。
据罗孚说,聂绀弩的同一首诗,有时赠给这位,有时寄给那位。这一点上,聂绀弩正有古人之风,唐诗宋词中,本就有无数朋友间吟和赠寄之作,并非为诗而诗的。
百年以来,聂绀弩之前,鲁迅、郁达夫的旧体诗作不多,也足以成家。聂绀弩之后,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各有特色,却自认为“打油”,那是文脉不断的明证。自从胡适不遗余力地尝试与倡导“新诗”以来,旧体诗成了非主流。
新诗的尝试是否成功,见仁见智,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的一段话为一家之言:“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
和老人们聊到聂绀弩,好几个人提到这种现象:当年写新诗的一些猛将,晚年都爱写旧体诗。这种现象倒真是值得诗歌研究者深挖的课题。好像是鲁迅在一封信里说过:好诗到唐,已经作尽,不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即不必动手云云。
可是鲁迅的一些旧体诗是好的。而到了聂绀弩手里,更别有一番新气象。我们的时代曾有聂绀弩这样的大诗人,他却常常为后辈淡忘!随着以他为师为友的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这一代人的老去,感慨之余,只能期待江山代有诗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