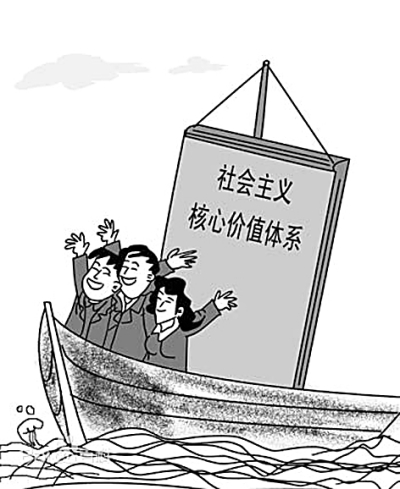读书节目文化 中外电视读书节目如何与大众文化共舞
2012年4月,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在“世界读书日”推出了特刊,首次对全国的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开辟读书版、读书周刊、读书栏目(节目)的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仅存六档电视读书节目。

即,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读书》(原《子午书简》)、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书香北京》、河北卫视《读书》、上海星尚频道《今晚我们读书》、上海第一财经频道《速读时代》以及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相较于广为人知的国外电视读书节目,如美国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Oprah’s Book Club)、英国的《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Richard & Judy Book Club)以及法国的《猛浪谭》(Apostrophes),国内外电视读书节目有何共通之处,文化环境和节目形态上又表现出哪些差异,本文试作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类节目的未来。

一、共性化的困境与问题
1.并不乐观的阅读环境
2012年6月,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2011年人均阅读图书、报纸和期刊分别为4.35本、100.70期(份)、6.67期(份),年人均阅读电子书1.42本。[1]
2004年,美国发布了一份题为《岌岌可危的阅读习惯:美国文学阅读调查》的报告显示,“阅读文学作品的成年人比例与以往数十年的比例相比出现了大幅下滑,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当属18—24岁年龄段的青少年。[2]以探讨“数字时代如何麻痹青年一代并危及他们的未来”为主题的《愚蠢的一代》作者马克?鲍尔莱恩,在书中颇有感慨地说道,“这种对书本和阅读公然漠视态度是全新的。

虽然,历代青少年对于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都愤恨不已,而且也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刻苦钻研成为各个时代的知识弄潮儿,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四处宣扬‘非阅读’(具有阅读能力,但是选择不阅读)是一种正当行为。”[3]

中外电视读书节目所赖以生存、具有共同性的社会阅读环境如此不甚乐观,依存于电视这种电子媒介上的读书行为以及读书节目的生存状况就更令人担忧了。
2.如何与大众文化共舞
1993年,上海《文汇报》率先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随即形成热潮。“正是在‘人文精神复兴’的呼声中,读书节目作为一种全新的电视节目形态应运而生” 。[4]由此可见,在中国电视读书节目诞生之初,就已秉承了精英主义的理念,如央视《读书时间》栏目所言“力图使栏目成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高雅文化的窗口”。
因此,我们看到以《读书时间》为代表的电视读书节目,从节目的选题、书籍的选择到话题的设置都走的是精英路线。电视读书节目在节目形态上表现的曲高和寡,与大众文化的类型化、日常化、娱乐化、商业化等特点相去甚远,在2004年《读书时间》停播之后,国内十余档读书节目也相继退出了电视屏幕。
电视读书节目如果对大众文化采取不理不睬、自说自话的态度,其结果必然被大众文化所拒绝与摒弃。国外的电视读书节目亦然。2009年,在法国电视2台播出还不到1年的读书节目《文学咖啡馆》因收视率过低而让位于一档情感节目。
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电视读书节目如何与大众文化共舞?中外电视读书节目的解读方式存在着差异。
2011年6月,央视《子午书简》更名为《读书》,其主持人李潘在采访中提到,《子午书简》时期,有趣,也就是话题性、故事性,排第一位,然后才是有用和主流价值;而在《读书》中,三条整个反了过来,她特别强调“有用”的涵义:“除了物质上的有用,我们更追求精神上的有用。
”其想争取的是在“更多中小城市里,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渴望精英文化,可生活环境里又得不到这些信息的那群人”。[5]可见,其呈现出来的面孔不是对大众文化的妥协,而仍是同以往一样对精英文化的坚守。
美国《奥普拉读书俱乐部》这一堪称经典的美国电视读书节目则是在褒贬不一的争议中走过了17年。1996年9月,奥普拉借助于已经开播了10年的《奥普拉脱口秀》(The Opera Winfrey Show)的影响力,创办了以“让美国重新开始读书”为初衷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
该节目的受众群体主要是18—54岁的女性,这一部分人也是美国公众阅读的最大一部分群体。[6]在节目中,奥普拉根据女性观众的特点,将对书籍的介绍嵌入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她们拿起书本,开始阅读也许是生平中的第一本书籍。
《与日常生活的辩证关系:在〈奥普拉?温弗瑞读书俱乐部〉中的传播及文化政治》一文分析道:《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制作者考虑的是如何将读书和阅读嵌入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为女性增加负担,让他们来改变日程进行阅读。[7]因此,《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择为女性所更为青睐的流行大众文化读本,比如言情小说。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成功和流行,在与大众文化水乳交融的同时,也伴随着争议。一些文学学者坚决抵制印有“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印章的作品版本。2001年9月,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代表性的事件是,《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作品《修正》(Corrections),然而该书作者乔纳森?弗瑞森(Jonathan Frazen)公开拒绝这项“荣誉”,其所担心的是,“如果他与一位学识根基并不深厚的主持人讨论书,那些所谓的严肃读者就有可能不再去看他的书”。
[8]可见,电视读书节目如果与大众文化相得益彰,就会有来自精英分子批判与抵制的声音。当然,大多数获得推荐的作者,还是会乐此不疲地接受《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奖章;美国图书馆学会也将象征着最高荣誉的终生“荣誉会员”授予了奥普拉。
二、差异化的文化背景与节目形态
1.阅读传统的差异:分享与自悟
在学者们分析《奥普拉读书俱乐部》为什么成功时,泰德(Ted Striphas)提出:研究《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重要性时,“不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俱乐部,从定义上来看,意味着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团体,或者更为乐观地说,是指有意愿就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那一部分读者群体”。[9]另外,《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猛浪谭》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依托俱乐部这样的群体组织。
图书俱乐部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人重要的阅读方式之一。图书俱乐部的成员通过俱乐部的推荐去选择阅读书目,然后可以就同一本书进行交流与探讨。图书俱乐部所营造的是一个将图书由“被看”走向“被讨论”、众人能够参与并分享读书体验、分享快乐的公共话语空间。
在此话语空间中,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谈论自己对于书籍独特的感受,同时与他人进行对话。可以说,俱乐部在营造公众话语空间的属性上与电视媒介有着某种共通性。如果将一台摄像机直接去原生态记录一次俱乐部活动,也具有可以在电视上展现的条件,因为这里有交流的平台、有对话、有分享,有着满足电视视觉化表现的元素。
然而,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读书的看法更为强调的是在适宜环境中带有自悟性的个人阅读,“妙处可悟不可传”,最精彩之处不是与他人进行交流、分享,而是在“拈花一笑”间了悟于心,就如南宋美学家严羽所提出的“大抵禅道惟有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的“妙悟”之说。
然而,这“悟”字是最难在电视空间上用影像来传达的。因此,中国电视读书节目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如何让大众改变千百年来读书是个人阅读式的传统,让读书从自悟、围炉夜话,进入到公众话语空间。
2.节目形态的差异:脱口秀与谈话节目
从节目形态来看,国内仅存的六档读书节目中有四档是谈话类节目,另两档则偏向于资讯类。而国外几档经典读书节目都属于脱口秀。
脱口秀是人际交流中较为原生态的展示(show),更为强调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主持人能够说“真话”、“刺话”。法国《猛浪谭》的中文译名,就取其主持风格具有猛浪之意,毕佛曾表示,“向一位作者说他的近作令人失望,无论就读书的乐趣或礼貌而言,都无伤大雅”,其直言不讳的性格非常鲜明。[10]
中国电视读书节目从传播模式来看,更偏向于传递模式(见表1),虽然节目主持人与嘉宾是在对话交流中构建话语场,然而,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传递读书的意义与价值。在谈话节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观点的冲突、现场观众的互动,而是强调观众对书籍本身、对作者写作背景与经历的认知过程。
相对来说,国外电视读书节目更偏向于展现模式,其强调的是分享、参与、情谊等。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指出,“仪式观点并不直接关注空间中的信息扩展,而是社会在时间上的维持;它并不以信息的行为为目的,而是共同信仰的表现”。[11](见表1)
表1 大众传播的两种模式
三、电视读书节目有没有未来?
电视与读书,作为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从开始的相遇就展现了诸多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电视媒介的碎片化与印刷媒介的有序性。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接受在一档电视读书节目中插播几条广告,却绝对不能容忍在书籍中间插入几十页与主题完全不相关的内容。
电视引导人们来看,而书籍更多的是引导人们去思考,然而电视却最不适宜展现思考,因为,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以去看。原《子午书简》的主持人李潘曾谈到,她一直面临着这样的质疑:“作为‘快消品’、大众化的电视,和代表高雅文化、面向小众的读书,本质上天然矛盾,因此做电视读书节目,从根本上就不可行”。[12]
那么,电视读书节目是否最终会从电视上消失?在我看来,一档节目是否会继续存在,最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
著名喜剧演员迈克尔?佩林在评价《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时说道:图书世界相当小众,局限于几家大报的少数书评家之手,这是个耻辱。我们不能再把读书看成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活动。理查德和朱迪鼓励人们在阅读和选书时找到更多的自信,因而扩展了欣赏与兴趣的范围。他们带来的冲击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1997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在授予奥普拉终生“荣誉会员”的颁奖词中写道:奥普拉?温弗瑞,通过她的读书俱乐部,复兴并促进了阅读在美国公众中的重要性,她对此所作出的努力超过了当今时代的其他公众人物。
创办于2000年的河北卫视的《读书》节目,在2009年初跻身广电总局确立的全国二十个示范栏目之列。时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胡占凡批示是:“在惟收视率的不良环境下,《读书》能坚守品味和格调,营造文化氛围,实属不易,谢谢大家的执著精神。”
以上三段对于中外电视读书节目的评价,说明电视读书节目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虽然,注意力的获取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得益则另一方必然受损;虽然,读书这种行为在电视上有着诸多先天的不适;虽然,电视读书节目的命运起伏波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节目形态不会消失。因为,总是会有像奥普拉这样的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书籍的力量,而去争取更多的媒介关注与空间。
注释:
[1]去年我国人均阅读图书4本 半数国民自认阅读量少.证券时报网,2012—04—23.
[2][3][美]马克?鲍尔莱恩.最愚蠢的一代.杨蕾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07:48.
[4]金山.新版《子午书简》的定位及启示.电视研究,2010—04:48.
[5][12]王砚文.《读书》变大众化是痴心妄想.新商报,2011—08—25.
[10]读书节目的经典《猛浪谭》.看!媒体.2007—10.
[11][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0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