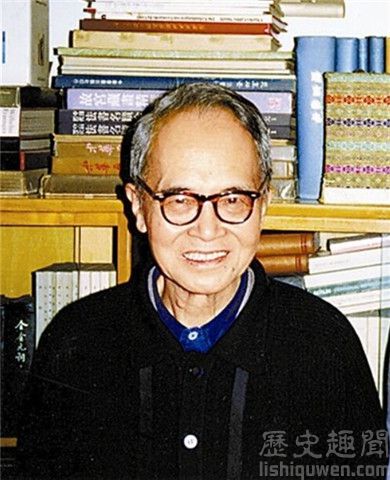寒山寺敲钟 在寒山寺敲钟
在寒山寺敲钟,说起来是很富诗意的雅事。但因为近代中国的衰落和饱受欺凌,寒山寺钟也命运多舛。此钟因此也像是警钟,提醒我们“‘历史记忆’是抹不去的,除非我们自己忘却。”
敲三下五元。这是寒山寺钟楼前的明码标价。心里虽然觉得怪怪的,但是到了寒山寺,谁不想亲眼目睹催生了《枫桥夜泊》的这口闻名海内外的大钟呢?何况还能亲手敲钟。

有此机会,缘起于日本人。1979年,日本池田市日中友协副会长藤尾昭先访问苏州时,提出想在除夕夜(公历)组织日本游客来寒山寺听钟。获得认同后,遂于同年除夕正式率团举办了首届听钟节。如今,一年一度的听钟节已成惯例,近年许多中国人也纷纷加入其中,据说拿到敲头钟门票的价钱不菲,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犹如抢到了烧头香的福分。

日本人对许多中国东西颇为关注,对寒山寺和听钟的痴迷就是一例。自从寒山寺、《枫桥夜泊》和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元素被遣唐使带回日本以后,影响力经久不衰。
“大唐雄风”式微,寒山寺大钟也遭遇了厄运。据说,钟是在明末被倭寇劫掠而去的。还有几种版本,其一,太平天国时寒山寺毁于战火,无耻之徒趁乱将钟盗卖与上海古董商人,最后流入日本。其二,劫掠者的幕后黑手是大隈重信,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

日本僧人山田寒山得知寒山寺钟在日本,因搜索无果,遂于1905年新铸二钟,其中一口准备赠送寒山寺,并请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撰写铭文:
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乃将新铸一钟,赍往悬之,来请余铭。寒山有诗,次韵以代铭: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勿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大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
这口钟直到1914年才送到寒山寺。现在钟楼悬挂的铁铸大钟,落款“大清光绪岁次丙午三十二仲冬月谷旦”,即1906年,由当时的江苏巡抚陈夔龙督造。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位巡抚大人知晓了这口日本钟上有伊藤博文的铭文而采用的婉拒之术?要知道,正是这个伊藤博文在任首相期间发动了甲午战争,而铭文中的落款“明治三十八年四月”,10年前这个月的17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
我们当然无须以恶意去猜测许多日本人捐款铸钟的善举,但伊藤博文铭文的用心却深可玩味。
何谓“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难道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先声?我们不怀疑他怀有对寒山寺和《枫桥夜泊》的崇敬,那是对大唐而非大清。在那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伊藤博文撰铭时的心境,是强者对弱者的自赏,怜悯,蔑视,讥讽,甚至是惧怕大唐之风雄起的自我警示,抑或五味杂陈?
1996年,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做交流教师时,曾经听该校的老师说起过,甲午战争以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文化圈民族都笃信风水一说,深谙此道的日本侵略者于是在朝鲜历代王朝的勃兴之地深深地打入巨大的铁钉,企图镇住朝鲜复兴的“龙脉”。那么劫掠寒山寺大钟以及后来种种劫掠中国历史文物的行为,难道就没有切断中国人“历史记忆”的算计?
越来越多的类似寒山寺大钟命运的悲剧,也激发了中国人去了解这个中国曾经的学生的真实面貌。“人家越是要用炮火欺压过来,我越是想转过人家后边看看。”(《雕虫纪历·自序》)这是诗人卞之琳在“九一八”后不久决定东渡日本的原因。由此也诞生了《尺八》这首充满忧患和反省意识的名篇: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从夕阳里,从海西头。/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听了雁声,动了乡愁,/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尺八(一种竹笛)原本是来自大唐的“异方的种子”,被一批批像“候鸟”一样的遣唐使们带回日本以后,“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诗人在一篇同题材的散文里写道:尺八虽来源于中国唐宋的笛,但是它保留了笛的高亢,而尺八在中国的母本则演变为发凄婉之音的箫了。
诗人告诉我们: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失去的已经不仅仅是在本土早已失传的尺八之声,而是汉唐雄风。而一声声“归去也”的呼唤,分明是诗人企盼国人能幡然觉悟、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肺腑之声!
2003年我在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做交流教师时,曾打听过尺八的模样而未有确切的回答。有一次在看日本传统能剧时,却看到台上伴奏的一支短笛,在用薄木片拨出的短促、沉稳的琵琶(据说也是在唐时传入)和声里,发出尖锐、高亢的声响。我想,这是否就是卞之琳做“孤馆寄居的番客”时所听见的尺八的声音?怪不得他有此感慨。
在日本时,我也有自己的感慨和反省。我在一所华人开的中文学院教过两个日本学生。其一是中年男子,中文其实不错,他来上课就是故意问一些挑衅性问题,因此我向院方提出中止讲课约定。另一个是中年牙科女医生。她没有去过中国,但是我感觉她对中国怀有好感。
有一次,教材里正好出现伊藤博文的名字。我看到她的表情有点兴奋。我说:“他发动甲午战争!”“嗯。”她点点头,接着说:“还有明治维新。”她的回答显然是常识,但是它和我想发挥的内容不对路。
片刻冷场之后,我们换了话题。课后我还在回味我们俩这无意间的对话。反映在伊藤博文身上的这两种经历,难道没有关联吗?而我们往往有意无意间“选择性地”强化或者忽略了某些东西。又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南京大屠杀。
她听得很认真,说:“有机会我想去南京。”接着她问我:“你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吗?”我一愣,有点结巴地说:“我,我还没有去过。”我用了一个“还”字,潜意识里有着解释的意思。但是我自觉言语里缺少底气。这是否也是另一种慵懒与麻木呢?我们不缺愤恨,却缺少愤恨之后的思考与行动。
前不久在参与重编《新诗鉴赏辞典》时,重读了诗人叶延滨的《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又勾起了我对寒山寺大钟、《尺八》以及在日本的这段往事的记忆:
唐朝来的秋蝉/不太讲究平仄,它毕竟不是/李白,李白只有一个而唐朝的秋蝉/很多,很多的秋蝉/就让天地间高唱前朝盛世调/冰河铁骑兮大河孤烟/四方来朝兮长安梦华/啊,风光过的蝉是在用歌唱/为那个盛夏而唱/气韵还好,气长气短仍然高声唱/只是毕竟秋了/秋蝉的歌,高亢而渐凉
宋朝的蟋蟀无颜/北宋无院/南宋无庭/无院无庭的蟋蟀躲在墙根下/也要哼哼,也要叽叽/丢掉江山的宋朝也哼哼叽叽/忙着为歌女们填词/难怪躲进墙根的蟋蟀也要唱/小声小气/长一句再短一句/虽是声轻气弱/却让闺中人和守空房的美人/失眠,然后在蟋蟀的抚慰里/养出美女作家,凄凄切切烈烈!
唐去也,唐蝉也远了/宋去也,蟋蟀也远了/无蝉也无蟋蟀的现代都市/只有不知从哪儿来的风/吹弹着水泥楼间电话线的弦/请拨唐的电话,请拨宋的电话——/忙音!忙音!忙音!……
“历史记忆”是抹不去的,除非我们自己忘却。这次在寒山寺所敲之钟声,虽然已非唐音,但是它的余音将久久种植在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