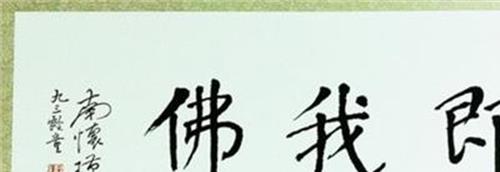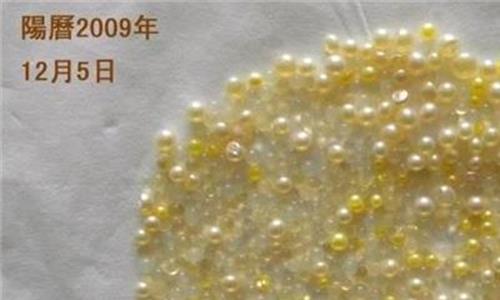牟宗三与南怀瑾 南怀瑾先生侧记:唯识·熊十力·牟宗三
南老师讲《论语》,讲《孟子》,讲《易经》,讲《金刚经》,讲《楞严经》,等等,都是讲解或讲述,但是每当讲到唯识,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讲解。
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曾向南老师请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没有细说。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

中国的唯识学,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却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以及寺院的学者中。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

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不多,近代有位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识,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识论》,对唯识论有所批评。如果不是重视唯识,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
熊十力先生是廿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
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台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个性爽朗直接,作风坦率而有原则。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卅元,资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绝了,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
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不像有些做门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这是题外闲话。
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因每天下班懒于举炊,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记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马白水、赵春翔三人则有家眷,都住在一楼,各有一大间。赵春翔是我的姐夫,张平堂又是远亲,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都爱下象棋,还时常连下通宵,黎明棋局结束,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
我常在访张平堂时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授,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涉猎颇多。
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我一定不会错过。
言归正传,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新唯识论》,分成两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论”,另有一部是“量论”。但“量论”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熊、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不肯轻率下笔。
以熊氏学养之深厚,曾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也许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终未写“量论”。
学养了不起如熊氏,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轻易从事,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过,牟宗三虽未写“量论”,但在他后来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一般认为,有所论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发现,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了唯识论。
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则只是名词的依文解义而已。
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轻率讲述,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