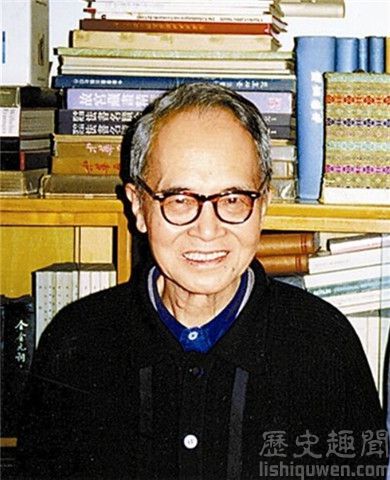钟期光夫人凌奔 与钟期光、凌奔夫妇相处的日子
1961年,左起:史凌(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夫人)、于玲、王于耕、凌奔。
我没有在钟期光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也从未和凌奔同志一起共过事,但我们家与钟政委一家在几十年风雨晴和的岁月中,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浓厚情谊。他们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已深深锲入我的脑海,使我时时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我爱人乔信明,1934年随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不幸被捕入狱。三年多的铁窗生活,使他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被组织营救出狱后,他加入新四军“江抗”东进敌后的队伍,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战斗中,担任主力团团长之职。频繁激烈的战斗,寒冷潮湿的环境使他那带过脚镣的双腿终于发了病。此后他只能拖着残体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1941年,陈毅军长决定送信明同志到华中局党校学习兼休养,恰巧我也奉谭震林同志之命到党校学习。战争年代,夫妻相聚十分难得。一见面,信明就兴冲冲地告诉我,临行前政治部钟期光主任专门去看望他,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反复叮嘱他务必养好身体,及早重返前线。钟主任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信明同志,党校刚成立,生活十分艰苦,你是学习、养病一肩挑,缺一都不能算圆满。”随即送给信明同志一笔营养费,硬要他收下。说到这里,信明同志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钟主任的名字,他那深入细致的作风和对信明一腔赤诚的情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钦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1941年底,我和信明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师工作。恰逢敌人大扫荡。我和信明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粟裕司令员的关心下随部队行动。由于敌人到处设立密探,我们每到一处,刚把饭烧好,敌人就来了,我们常常只能饿着肚子转移。我的奶水越来越少。夜行军中,大家坐在田埂上休息,我就让帮我带孩子的阿姨到附近河沟里舀碗冷水,勉强连冰带水的喝下去,以期增加一点奶汁。离我最近的钟期光同志则在黑暗中从口袋里抓出他最后的一把炒米塞给我,让我和着冰水吞下去。他的口袋里经常备着点炒黄豆或炒米这些艰苦年代略显贵重的小食品,在和人谈话时递上一把,于他已习以为常,于受益者则感激不尽。
1944年,信明在军部养病。一天,院落里的竹椅上,他正靠着翻阅缴获的敌伪报纸,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亲切的问候声,“信明同志,你好啊!”信明扭头一看,钟主任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正背着手立在身后笑眯眯地望着他。老首长的突然到来,让信明既兴奋又手足无措,使足劲儿想站起身来行礼让座。“不要起身,不要起身。”钟主任边说边按住信明,旋即坐在院中石碾上,和信明叙谈起来,谈到兴头上,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小院。事后,我才知道钟主任是到淮南龙岗检查抗大九分校工作的。为探望信明同志,不顾一路劳顿,竟绕了几十里路赶到军部,临走又给信明留下一笔营养费。在当时条件下,部队经费的困难难以言表,钟主任两次送来营养费,让我们既感激又不安。这为数不多的营养费中蕴涵着党的温暖、组织的关怀,以及一位政治工作领导者的情怀,给人以慰藉和鼓舞,由此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945年,鉴于军部情况吃紧,信明同志行动困难,组织上决定把他转移到苏中休养。我们一到苏中,钟主任就把我们安排在他住的石轮庄。两间用毛竹和芦席临时搭起的新屋,墙壁刷上了雪白的石灰,装上了玻璃窗,既明亮又卫生。屋外三面是水,水旁柳树成阴。信明来到门口,欲进又止,心想这样的条件是否过于奢侈了。立在门边的管理干部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笑着说:“庄子上房子太紧,实在腾不出来。钟主任亲自交待我们选点造屋,还指示我们要搞两条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顺着管理员的手指,我们才发现湖边歪脖柳树下系着两条小船,静静地漂在那里。呵!又是心细如发的钟主任,为别人,他总是想得那样细致周到。此后,住在同庄的钟主任常常来看望信明,有了重要的学习材料和文件,亲自拿来给信明看,体现了他对同志政治上的进步非常关心。
1946年,华中军区在淮安成立,司政后机关都转移到淮安,信明也被安排到淮安住下来。这时我和凌奔同志都由于孩子的拖累,尚未分配工作。在淮安这段时间,凌奔同志几乎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彼此的了解和感情逐渐加深。
全国解放后,钟期光同志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政委期间,我们又同住在南京。两家的来往更加频繁,曾同上黄山,共游闽南。家中有什么事总能得到钟政委和凌奔同志的关照。他们还经常把我们的孩子接到他们家中去照顾,相处得亲密无间。
乔信明与钟期光同志(右)在南京宁海路5号钟期光家门前合影。
1963年9月,信明同志突然病逝,这时钟政委已调北京工作。闻此噩耗,钟政委和凌奔同志立即打电话来慰问,听到他们的亲切话语,我顿时泣不成声。钟政委又亲自写信痛悼信明的去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部属的关念之情,给我们一家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当时我的大女儿阿光正在莫斯科大学留学,钟政委即和外交部联系要大使馆找到阿光,让他们转交告知她父亲去世的信件,并安慰她以优异成绩来纪念父亲。
1964年,信明病逝不到一年,我的大儿子晓阳又被国家选送出国留学,在北京有两个月培训时间,为此我送儿子去北京。钟政委和凌奔同志非要我住在他们家不可。钟政委知道我刚失去信明,实在舍不得孩子出门远行,就不断安慰我,要把眼光看得远一些,并送我儿一个笔记本,亲笔题写:送晓阳出国,好好学习,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凌奔同志更是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拉着手问长问短,还拿了一件自己穿的羊毛背心给晓阳出国用。当时我儿培训,除星期日外不能外出,钟政委、凌奔同志知道我想儿子,一到星期六下午,就派车把我儿接来,让我们母子团聚。
“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内控”对象,不准离开南京,我就让在北京的儿子常去看望钟政委一家。“四人帮”垮台后,钟政委和凌奔同志于1977年终获自由,到上海治病时,我也因乳腺癌来这里动手术,就这样久别重逢了。
钟政委和凌奔同志因“文革”中遭受迫害,身体很差,但他们仍然时时为我的病情担忧。在我动手术之前,钟政委担心我精神上承受不住,专门和我谈心。当他看到我神情正常,心理准备充分时,就高兴地表扬我的乐观主义精神,那情形犹如战争年代的战前动员似的,无形中使我力量倍增。
凌奔同志反复交代我女儿春雷,一定要让我配合医生的治疗,万万不可大意。手术的第二天,我在昏睡中听见有人唤我,睁眼一看,竟是凌奔同志带着她的儿子大宝来到床头,她示意我不要讲话,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我,钟政委和她的情意与关怀都在那微笑的眼神之中了,一切话语都成多余。
他们听说甲鱼对癌症患者的身体有好处,就让孩子四处奔波买了几只送来给我补养。其时,钟政委和凌奔同志也在重病之中,他们就是这样,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钟期光同志是我们的老首长,凌奔同志待我亲如姐妹,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时时处处都能体验到革命同志之间的情怀和亲如家人般的温暖。他们的胸怀,他们的风采决非言词笔墨能够表达出来的。我这篇短文仅仅透过片片断断的回忆,从我们一家与钟政委一家相处的日子里摘取几件小事,但愿能点滴反映出钟政委、凌奔同志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以此告慰老首长和凌奔同志的英灵,表达我们全家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