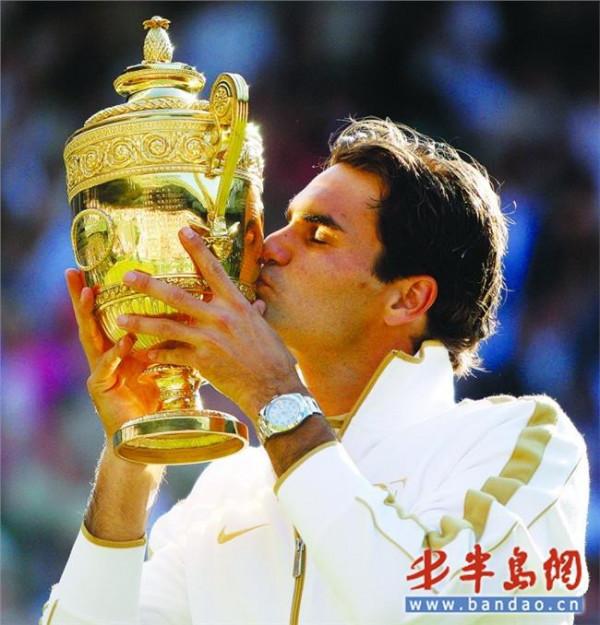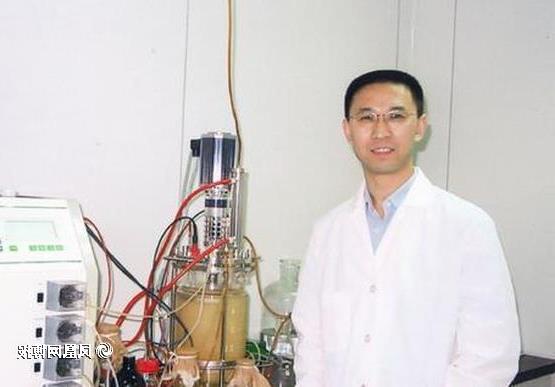罗家伦革命文献 绍籍大学者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著名绍兴籍大学者字志希,笔名毅,柯桥江头村人。
罗家伦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其父罗传珍曾任江西省进贤县知县,工绘画,尤善画梅;其母周霞尚读过不少书,笔下颇具文采;罗家伦因此从小就接受了较好的教育。

1914年,罗家伦考入上海复旦公学高中部,与孙越崎、朱仲华等绍兴同乡住同一寝室,彼此朝夕相聚。
1917年夏,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外文。期间,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杂志《新潮》;还结识了一大批对他后来的事业与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师长与学友,包括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蒋梦麟、朱家骅、顾孟余、沈尹默以及傅斯年、段锡朋、冯友兰、何思源、顾颉刚、毛子水、周炳琳、狄膺、汪敬熙等人。

1920年,经校长蔡元培推荐,罗家伦等五位同学被选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1921年秋转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教授门下就学。1923年秋,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6年,罗家伦回国,在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任教。1927年,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并加入国民党,参与创办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并渐为蒋介石所赏识。此后,先后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执掌中央大学十年,成就卓越。

1941年罗调离中大,曾出任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
1949年罗到台湾,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并发症在台北逝世、终年72岁。
罗家伦著作等身,除译作外,著有《新人生观》、《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证》、《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疾风》、《耕之集》、《心影邀游踪集》、《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革命文献》、《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等。
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见》,这是大陆在1949年后首次出版的罗家伦的文化散文集。然而,就罗家伦先生之功绩,还是以首任国立清华大学和执掌中央大学为最。
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9月,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作为国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的名声。为改变这种过分依赖外国的状况,该校从1916年起,经过十年酝酿,到1925年才成立大学部。即便如此,由於体制上的原因,要正式改为大学也不容易。
1928年,罗家伦走马上任,当时国民政府给他的任命是“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不满意,认为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的嫌疑。经过多方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的体系。
冯友兰说,当年校牌上“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为谭延闓先生所写,这是我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誉为中国教育中上的一座丰碑。
二是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会虽有美国公使参加,却由中国外交部控制,于是这几百万美金就成了少数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的本钱。
清华的日常开支是由美国使馆按月交给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只要把这笔美金兑换成国币,就有上万元赚头。至于拿清华基金去炒股买彩票,赢了归己赔了归公者,也大有人在。罗家伦上任时举过一个例子,有人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该银行就倒闭了。
他气愤地说:就这样,四百多万元的基金,已经剩下二百来万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以辞职相抗争,并通过报纸把黑幕公之於众。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会还推举冯友兰为代表去南京交涉。结果这笔钱转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基金已经积累到一亿三千万左右,这显然是罗家伦打下的基础。
三是为清华大学增添了一批基础设施。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所以他上任伊始就明确指出:“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设备。清华现在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
”为此,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至少要拿出每年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来购置图书仪器。清华人比较爱吃,也比较洋气,针对这种现象,罗家伦一再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要讲究、舒适,宿舍则一定要朴素,这样才能把学生吸引过来。曹禺直到晚年还对清华图书馆怀念不已,是因为他的《雷雨》就诞生在那里。可见人们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水木清华的“三宝”,是很有道理的。
四是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多年前,冯友兰和陈岱孙分别对这个问题作过介绍。冯对罗评价较高,但是对制度的确立言之不详。陈的评价稍差,说罗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会。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指出,这一制度的依据是1929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
1929年正是罗家伦在位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重要文件是蔡元培让罗家伦拟定并由校务会议通过的。教授治校在当时曾引起较大争议,连蒋梦麟都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
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举行的清华同学会上说过,事后证明这个规程是很适用的。几十年后,冯、陈二人重提往事,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制度的赞赏和留恋。这也说明,在清华大学民主体制的建立上,罗家伦确实是功不可没。
除以上四方面之外,罗家伦在清华园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不收女生,如果要把这个问题提交有关部门,很可能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他一上任就分别给教职员颁发了聘书和委任状,在强调聘书比委任状重要的同时,还为教员增加了工资,并降低了高级职员的薪水。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
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日战争爆发不到十年,就培养出钱钟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一切,难道与罗家伦的开创性贡献没有关系?
执掌中央大学校政十年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作为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其在全国各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当可想见,因而管理也实属不易。
从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间,该校校长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独罗家伦先生,执掌十年校政。在当时国难当头、战祸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罗家伦凭着执着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使得中大获得较大发展。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
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
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八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六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户外,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
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主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
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四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
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首先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力挽留原有优秀教师,另一方面及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知名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罗家伦曾经对友人有过这样一段告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一次,蒋介石问王世杰:“志希(即罗家伦)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王世杰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内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
”这在当时,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定期发薪,绝不拖欠,有时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
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学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学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的有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物理学博士施士元,地理学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原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前南高师高材生张其昀等。
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千,著名诗人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生物学家童第周,化学家高济宇,政治学家张奚若,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
一时间,中央大学少长咸集,群英荟萃,盛极一时,令兄弟院校称羡不已。
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中大应该拥有更为广袤的办学空间。因为:⑴“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⑵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⑶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等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⑷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极不经济;⑸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
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所能容纳5000—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大胆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首肯(据说,蒋介石曾向为数不多的军、政要人发过晋见他的令牌,有此令牌者可随时随地去见蒋介石,侍卫不得阻拦,罗家伦便有此令牌)。
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在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
罗家伦最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山林起伏,布置起来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又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教学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方山,登高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
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是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块大洋,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动工。
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建,预计次年秋季便 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城的建设嘎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呈眼前。
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势下,罗家伦即刻召开了教授会,议决兵分三路,分赴重庆、两湖和成都,另觅新校址,最后考虑重庆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的中心,而且地势复杂险要,宜于防空和固守,在那里建校可以获得相对持久的稳定,所以,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四迁重庆。
其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果断决策是合乎时宜的。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予中大西迁。
可以想见,整所大学的千里大迁徙,其工作是极为艰巨繁杂的。当时南北各大学在迁移过程中,都备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一举西迁重庆,1937年11月初,就在重庆开学复课,八年抗战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为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部: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二百亩,为了能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42天时间,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
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二个月,建起了44幢校舍。
1941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大时告别演说中,曾不无幽默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西迁后的中大,时常受到敌机的袭扰,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8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就在如此简陋困顿的教学条件下,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校长罗家伦继续执着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将原教育学院调整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又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分设9个研究部。
在罗家伦最后离开中大时,中大在学科建设上,共拥有7个学院,一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学生人数,1938年在南京注册时为1072人,到1941年6月增为3153人;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共开524种,1941年的下学期则为829种,成为当时全国高校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以致在抗战初几年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大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三分之二。
罗家伦认为:大学应当承担起三种任务:
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教育本来是要把以往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熔铸后教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的。这种青年,不但要知识人好,而且要体魄好,人格好,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二是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我们不但要为自已的民族开发知识的宝藏,而且要为人类的社会,增加学术的遗产。
三是要能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我们既不能脱离时代而生存,我们的教育工作也不能脱离时代而独立。何况我们当前的时代,真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大时代……这就要靠我们认识这时代的精神,把他的需要和我们的工作结合起来。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罗家伦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本刊节选其中部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