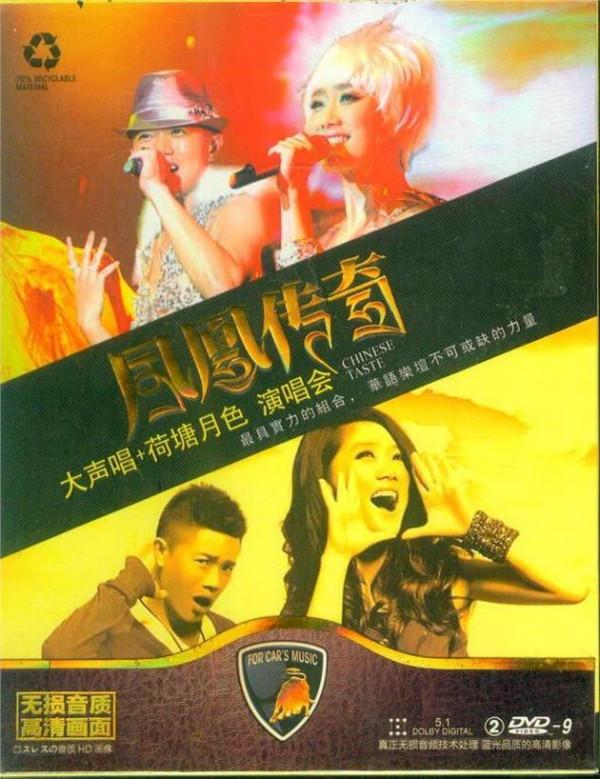戴玉强演唱会 《假面舞会》公认最难唱 戴玉强吃睡均抱着谱子
长达三小时、满是咏叹调和多重唱的《假面舞会》,无疑是最难的歌剧剧目之一。国家大剧院这次对《假面舞会》的选择,或许是在证明了舞台布景的顶级技术之外追求剧目艺术内涵的又一次尝试
本刊记者/万佳欢

国王爱上了臣下的妻子,原本忠心耿耿的大臣知情后展开复仇,最终在盛大的舞会与欢宴上展开一场暗杀。权力、政治与丑闻,占卜未来的神秘水晶球,爱情和死亡——歌剧《假面舞会》拥有最莎士比亚式的戏剧性元素,也同时拥有最真实的故事背景。

这部威尔第的中期作品根据历史上第一起国王遇害案、18世纪末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暗杀事件而创作,被认为无论形式还是戏剧内容都达到了“真正的雄伟壮丽的境界”,在西方久演不衰。
而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假面舞会》相对生僻,其知名度显然不如《图兰朵》或《卡门》。5月24日起,由意大利当红导演乌戈·德·安纳执导的国家大剧院版《假面舞会》上演,一些外行观众一边感叹国家大剧院一贯恢弘华美的舞台布景,一边被第一幕纷繁复杂的人物弄晕。这部三个小时的歌剧除了需要足够的歌唱技巧和体力,每个角色都有大量内心纠结的戏码。

同以往一样,《假面舞会》的演员分为外国组和中国组,后者包括人们熟知的歌唱家戴玉强、廖昌永,还有14年未在国内演绎整部歌剧、但却几乎征服了世界上所有顶级歌剧院的女高音和慧。
竞争、专业和“柔和的家庭气氛”
为了迎接2013年瓦格纳和威尔第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对相关剧目的筹备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曾制作过威尔第《弄臣》《茶花女》的大剧院最终选择了这出难度极高的《假面舞会》。
2011年,大剧院开始与国外联系,为《假面舞会》寻找合适的演出团队,而最后他们惊喜地得到了意大利导演乌戈·德·安纳的肯定回复。乌戈曾从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获得过意大利歌剧最高奖项“阿比亚蒂大奖”,用《假面舞会》项目人朱鹤的话说,他能来是“天上掉了馅饼”。乌戈的到来吸引了不少人的加盟,其中包括正在国际舞台当红的和慧。
“和慧很难请,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很有要求,”朱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四年前曾经约和慧来唱大剧院版《图兰朵》,却被婉言谢绝,理由是担心演唱《图兰朵》后所有人都会只约她唱这出剧,会把自己的艺术道路走窄。而这次,和慧简单地询问了导演和指挥的情况,然后答复“我来”。而男一号的演出者、男高音戴玉强却为是否接演这出剧犹豫了很长时间。
《假面舞会》被公认为最难唱的几部歌剧之一。“词多、快,在语言上就是一种挑战。重唱部分特别多而且难,这种‘大抒情’男高音需要耐力和持久力,”戴玉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就是个吃功夫的事,掺不得半点假。但我觉得这个戏我再不唱,以后就没体力唱了。”戴玉强为此投入了整整两个月,吃饭睡觉都抱着谱子,甚至还戒了烟。
4月25日,《假面舞会》开始正式彩排。在谈及与国内外演员合作的区别时,和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我们中国这组的演员也都很棒,但有些时候语言上是不是还可以更好。我很幸运,我意大利语没有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与和慧一样同样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歌唱家张秋林在剧中饰演女巫乌丽卡。这也是张秋林第一次出演《假面舞会》,但对她这样的女低音来说,这个角色是必修课,剧中的咏叹调她几年前就已经练习过上千遍。张秋林每年都在巴黎歌剧院演出。在她看来,那里集合着全世界最优秀的演员,竞争激烈、氛围专业,大家只谈语言、音准、表现力;相比之下,在中国排练、演出十分放松,是一种“柔和的家庭气氛”。
在巴黎,排练时会有专人在台下就演员的吐字和音节标准度做记录。副指挥则会在练习结束后来敲张秋林的门,对她说:“你这句稍微唱长一点;那里重音应该再强调一下,还有个地方不能换气。”
“国外指挥的要求非常高,你每一个字、每一个辅音,指挥都要知道你是怎么吐的。每一个乐句都要研究很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这里在音乐上还没有达到这么精致的境界。”
“欧洲歌剧界与中国歌剧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假面舞会》最初的故事取材于18世纪末瑞典所发生的古斯塔夫三世暗杀事件。1858年,《假面舞会》在为圣·卡洛尔剧院做首演排练,恰巧发生了一名意大利人企图暗杀拿破仑三世的事件。由于文化审查,威尔第不得不在《假面舞会》首演时把故事背景从瑞典改成北美波士顿。直到1935年,该剧才在瑞典头一次照原作内容上演。
而对导演乌戈而言,“历史实情”是重新创作《假面舞会》的要素之一。他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很明显是在表现18世纪的宫廷情景,因而大剧院版本采用的就是瑞典背景。
乌戈来北京后,挤出时间去游览了故宫、天坛、地坛、雍和宫和孔庙,项目人朱鹤认为这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文化的重视,“跟你在一起时,他从不讲别的,只讲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传承下来的艺术都承载了很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再创新也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根。”5月10日,乌戈在与中国舞美家协会的座谈会上说。
乌戈是电影导演专业出身,他对舞台的写实性要求已经到了相当电影化的程度。为了吸引中国观众,他的舞台设计运用了很独特的色彩表现,但这些色彩与传统东方电影、戏剧中的风格大相径庭:它们不是浓烈的红、橙、金,而是素雅的黑白对比。
在座谈会上,他请大家理解一个西方人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观众群体创作的困难性,“我可以想象观众的想法,但是偏差难以避免。”
无论观众或者演员,文化差异都是无法避免的。参与演出的演员们说,歌剧对中国人来说最难的不是声音,而是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程度和对语言的把握。“我们的声乐教育跟国际是接轨的,”歌唱家廖昌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歌剧制作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服装、礼节方面多下工夫。”
十年前,廖昌永便在多明戈的引荐下,于底特律歌剧院演唱过雷纳托一角。但这次导演要求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那个时代相符合,“排练过程中,导演一直在跟我们讲历史和故事背景。”他说。
乌戈对演员表演的要求十分严格,演员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体力,他们被要求跑着唱、跪着唱、坐着唱、站在特别不平坦的山坡上唱。“原来的威尔第歌剧,你站在那里看着指挥唱,别的导演也允许。”戴玉强说。
《假面舞会》开始排练后的一段时间,乌戈每晚都在看中国电视剧,“通过观察中国平民生活,有助于我了解演员身上的性格,”他说。乌戈认为,欧洲歌剧界与中国歌剧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需要相互学习。
“我们不能连游戏规则都不懂”
国家大剧院对与国外歌剧创作、制作团队合作中的“偷师”行为并不避讳。“这种合作慢慢把来自西方歌剧几百年的创作和演出经验拿过来、并且保留下来,”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在2011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国家大剧院开始从购买国外经典剧目发展到尝试联合制作歌剧。而相继成立合唱团和和管弦乐团后,又开始尝试采用国外的主创团队加国内演出班底的模式打造自己版本的西方经典歌剧剧目。
中方的参与程度正在逐年加深。以2009年首演、随后两年复演两轮的《弄臣》为例,最初中方只负责舞美、道具等硬件制作,第二轮演出将乐团替换为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最后又进展一步,除外方演员,其他演出人员和制作事务全由大剧院负责。
目前,以这种独立方式制作的西方经典剧目包括《卡门》《茶花女》《爱之甘醇》《托斯卡》等。这些剧目与《假面舞会》一样,除了外国组主演,合唱演员和乐团全部来自国家大剧院。
而另一方面,国家大剧院也于2009年开始启动了包括《西施》《山村女教师》和《赵氏孤儿》在内的完全中国原创歌剧的制作。但相比之下,引进著名歌剧显然比原创风险更小,更具票房吸引力。
廖昌永认为,在国内观众对歌剧了解有限的前提下,还是应该多唱西方传统歌剧、而非原创歌剧。他举例说,这就像写书法——什么都不懂就直接开始写草书,结果只能是比丑。
“我们得明白歌剧的制作流程,不能连游戏规则都不懂。”廖昌永说,“多唱传统歌剧,除了让更多中国观众去了解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还会让演员、包括作曲、编剧在内的制作团队都了解歌剧制作的规律。这之后再做原创,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迄今为止,国家大剧院的经典歌剧重排项目走出国门进行演出的仅有与普契尼节日基金会合作的《图兰朵》。而在国内,经过几年市场培养,观众已经习惯并接纳了这种外国组加中国组演员的演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