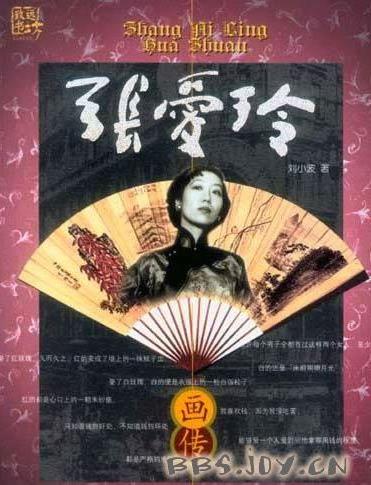故乡的云华晨宇 故乡的云的优美散文
这是七百年前一个风平浪静日子,屋舍的顶上冒过两餐的炊烟,棚里的头谷已也喂过两次,仲秋的风很乐意在接近肌肤的瞬间让人一激灵,天越来越凉了。乡民之间唯一的谈资已经发酵,所有人和头谷都期待着马上到来的秋收;如果那家收成好,说不定就能给儿子添一房媳妇,这是大家默认的。

只见太阳余晖的颜色渐渐变深,火热的红渐渐泛黄,黑色的影子也随着气温降低而覆盖田间,一波一波乡民在恋恋不舍中结束侃山,他们陆续回到屋子,将要同这片天地一同进入睡眠。我相信,倘若没有这天的大事发生,次日醒来的他们一定又滔滔不绝。

正当大部分村民刚刚进入睡眠,却突然声如巨雷,地动山摇,一场旷世骇浪掀起了。真是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这次明天还没来,迎接他们的不是秋收的喜悦,不是中秋团聚的欣喜。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日戌时,山移十里,地裂成渠,这是中国史载的第一个大地震,上纪落不偏不倚地占据震中。

迨于大德七年坤舆大震,观洞屋庐摧圮为之一空。
——上纪落村碑刻(公元1335年)记载
公廨倒塌殆尽,房屋倒塌二万四千六百间。
——平遥县,《元史·五行志》记载
大德癸卯,坤道失宁,上下两刹,多致圮坏
——太原·王居实《奉圣寺记》碑记

地裂成渠,泉涌黑沙,寺庙村舍遍地瓦砾,片刻的时间便颠倒了一个世界,对于幸存者而言他们是旧世界的遗弃者,他们是新世界的新生儿,一种无以言表的重压砸在他们的头顶。混沌世界,尸殍残骸,他们背负着死去的亡魂,肩负着重建的重任,还有不得不活下去的求生本能,继续上路了。
与此同时,活着的乡亲继续靠着汾河的水勤恳劳作,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慢慢浮现。丘陵为池,城郭为陂;地震将乡亲们的田地大规模迁徙,汾河东岸将生出大片田野,村庄里也凭空生出许多沟崖,从此一个崭新时代就此开始——泉水叮咚,风景秀丽。
叁佰玖拾贰年后正值康熙盛世,民丰物皋,这些淳朴憨厚的乡亲早已忘记当年的伤痛,上天却又耍了他的孩子脾气,几乎又在原地发生一次大震。当时,烈火烧天,黑水涌地,整个平阳府顿时浸没在滚滚烟尘之中。
这是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戌时,我们的乡民依旧像当年的先祖一样,继续被动接受这场无能为力的浩劫。汾河两岸的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四周田地一片汪洋,他们只能继续顶着所有的压力继续开始新的生活。
震后几百年来,上纪落的地势总比四周的村子要高上很多,它是临汾盆地里一个凸起的黄土崖捱。依崖而凿的窑洞,沟中诞出来的多处泉水,他们九曲回环地排布在村中平地的四面八方。平地上建起来的土房子并不整齐地排列,但在屈活和东头垂直相交的位置还是开出来一条载入史册的官道,每到一四七十便逢的集市也在此热闹,这一切都构成了上纪落村数百年来继续鲜活的动力。
历史的尘烟飘荡七百年后,我站在故乡的崖捱上,也忍不住落泪。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为智慧的祖先和浩瀚的岁月默默低头。我知道,像汤汤沟、师家沟、水翁沟、石坡沟、煞天沟、屈活、补子上、石板上、桥子上、猴娃垄等,这些自然村的名字定是我们的乡民在两次地震后,凭借自己的智慧,结合那沟崖的外表,跳脱而出的生动词汇。
这些词汇比他们幸运,比他们坚强,但又比他们更寂寞,目送着一辈又一辈的乡亲出生在这片黄土之上,又眼看着一拨又一拨步履蹒跚的人渐渐回归这片土地。又是深秋,一阵风吹过苍古而幽凉的土地,我,忍不住浑身一抖,天越来越凉了。
庄稼要丰收了,家人一定会团聚吗?不,我不知道……
二、沟里缘,我的前半生
对我而言,师家沟是血脉深处的记忆,至少从曾祖父年轻时,他的家就住在这里。这沟里有枣树、槐树、皂角树,还有一口公社时期留下来的老井。这沟里还有《雪花神剑》《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还有更早的一部是《神雕侠侣》,那是自打有记忆时便在祖母家经常看到的年画,上面有杨过和姑姑、大雕。
说起这师家沟的来源,它同所有中国农村的组成一样,最先住进来的是一户姓师的人家,亲戚套亲戚。到后来,这沟里住的大多还是一大家子,除了师姓,便是秦姓了。我还从父辈的话里听说过这样两件事情,一是祖母在三十左右的时候从老窑顶的崖上滚了下去,二是祖父在为叔叔娶小妈的时候出了他这辈子唯一一趟远门。
到我这一辈出生时,父亲、叔叔与他的父母都已从沟里搬了上来,一槿大院子鼎立在横贯南北的官道东侧,房屋坐北朝南,只朝南开了一处大门。我刚出生那会,全家住在一起,哦,这时候姑姑还没出嫁,她留着酷酷的学生头,跟着曾祖父、祖母与祖父在学校里,开个铺子。
这位木兰花毕竟也有着美丽的底子,毕竟也是个爱美的青年女性,后来的一天下午,她穿着灯芯绒的蓝色外套、黑色踩脚裤,踩着大红的高跟,左手插兜,右手抓着学校大门外的栏杆,留了影。
自打我上学后,每天清晨都有一个女孩准时到我家门口喊我上学,而我每次几乎都是从母亲的怀里被摇醒,然后半眨巴眨巴惺忪睡眼,迷瞪着穿上衣服上学去了。天还未大亮,蟋蟀和公鸡此起彼伏的叫起来了,她牵起我的小手,飞快地跑着。她,是我的小姑姑,比我大一岁,当然这不是那位帅帅的亲姑姑,她的亲祖父是我亲曾祖父的同胞兄弟。
不上学的日子里,我也是跟着她混的。整日的跟着她在沟里,跟一群别的孩子,有大有小,而她却永远是那个最有主意的,最有勇气的。遇见更大的男孩子挑衅,她会妙语连珠地怼回去;遇见秋天果子成熟的时候,她会教我们爬树,带我们去一些更繁茂的沟崖享受美食。
然而,也有一些她不在的时候。我便跟地主他们去玩,尤其喜欢在他家大门外的崖下。抬头望上去,这是一块较两边凹进去的地势,距离崖顶也不过六七米的高度,75度左右斜坡,孩子们攀出了台阶和“岩点”。
崖下有一根柱子栓着牛,往外走几步就是那口古水井和具有灵性的大槐树。忘了说,地主姓师,他的祖辈是这沟里的先人,他的母亲和我祖父是堂兄,照此计算,他比我又大了一辈。我们同年生的,一直到我上高中前关系都非常好。
模糊记得这古井最先是露天的,井口只围了一层青砖,到后来村里给井盖了个砖房,青灰色的墙面,顶子上铺了层层灰瓦,就连地上也铺满了整齐的青砖,在当时这样的工程应该会花不少钱吧。井房的门是朝西开着的,房子里东、北两面都是密不透风的石墙,唯南边的墙上留了一口小窗,窗外是一片空地,从窗口到地下有两米左右高度。
与其说是窗子,倒不如说是在墙上开了个洞,通风照明。挨着窗子的西边就是那棵老槐树,井房的顶子上是它茂密枝叶投下的斑驳树影。这条狭长的沟里南北极长东西极窄,除了顶头的坡有半截是从南北向转回东西向的,剩下部分的坡虽有蜿蜒,但却不改南北走向,居民则靠崖凿洞的从门窗里对视着中间的土路。
这条路南接下纪落顶头,北则伸到官道上去。大家都叫它小坡,它是除了那被列入古迹的石头坡外的另一条从南边进村的路,与官道的使用率相比这里更受周边村民和孩子热爱。叔叔婚后几年,家里的大院子便迎来了一场风雨,后遗症深远持久,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异常感觉。
先是围了一圈的土墙和朝南的木门被迅速拆掉,靠近官道西边的起来一排崭新的橡胶顶(砖房),接着是祖母从院子里最中间的那间砖房搬回沟里。后来没过多久,这槿院子的正中间竖起一道红(砖)墙,一户变两家,但是两兄弟间还是血水交融,他们坚持在新起的两处大门两边的三间房子里都留着一道后门。
这堵院墙隔断最初的作用是用来隔断母亲、小妈、祖母间的矛盾,可是治标不治本,到头来无辜连累了院子中间的几颗大梧桐,连累了那些令我十分开心的黑兔子和白兔子,他们都因为动工的缘故,伐掉的伐掉,卖了的卖了。
再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跑到沟里,跑到祖母的怀里哭诉。闲着的时候,就跑到祖母的窑里瞎翻,翻完里边翻外边。祖母看着委屈的孩子总是先长叹一声,祖母看着可爱健康的孙儿总是自她那年轻白皙的脸庞上畅出令人着迷的笑,那笑是温柔的,知书达理的,不似那些开怀大笑的婆姨和村妇。
有时候跟地主一起去捡西瓜靡儿给猪吃,有时候我自己去喂被祖父拴在半坡那棵枣树上的牛;有时候还去场(chuo)里的粪堆旁捡虫子给鸡吃,有时候还能去亲手为刚出生的小猪剪短脐带。现在想来,那都是在体验生命最神奇的轮回法则。
熊孩子总是不会那么让人省心的。有一次我从祖母家窑外墙上的储物台翻出一枚手榴弹,学着电视里的人物模样,想尽办法想要引爆,还好经年失效,已成了一枚哑弹,才没引出更多祸端。我知道,那枚手榴弹绝对跟参过军的曾祖父相关。
又一天,吃过早饭,匆匆跑到地主家,他家不仅有着沟里或者所有亲戚里唯一一台的彩电,而且他家里的桌子上总是摆着水果,那时他父亲在村大队任职。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伙伴,大家就从他家屋子里出来,开始商议爬崖比赛。数一二三就开始爬,谁都急急争着前几的名次。
争先恐后,你推我嚷,大家各显神通。到了三分之二的地段,我排在第三位,上面第二的是地主,只见我奋力向上,脚上一蹬,伸出右手抓住地主半袖的下摆,这一刻那颗原本就扑通扑通跳着的心脏更加勤快起来,我的嘴里刚哼出“游啊游(东游记的歌词)……”便突然脚下腾空,上身后仰,从坡上滚了下来。
就是这么巧,落地滚了几圈停了下来,从头到脚还坐北朝南的趴着。地主他们赶紧从这陡峭的坡上下来,他们看见我右腿的膝盖外侧淌出一片鲜红,磕磕巴巴都急得不会了言语。地主最先醒过神来,赶去我家找我父母,经过紧邻坡顶下的祖母家时他看见了我哥哥,到了坡顶左转撞进了我家的大铁门。
聋哑的哥哥急急奔来,看见已经坐在路石上一动不动的我,哭了,稀里哗啦,然后,我心一紧,才跟着哭了。他示意我上他的背,他们搀着我,一起使劲,我双手搂住哥哥的脖颈,笑了,像一朵饱满开放的向日葵,吸了足够的光。
到了坡底,母亲接上了我。好在诊所离家不远,开在供销社的斜对面,我被引到诊所里,才知道了那口子有七八厘米长,血肉都翻了出来,最后只是消了消毒,涂了一下碘酒,连纱布也没裹,回家了。扎进我腿里的是一只破碗,是不懂医务常识的一个玩伴拔了出来,他心急,他太关心自己的伙伴。
我努力回忆那颜色,幻想着那像极了玫瑰的妩媚。
我翻开库管我抚摸着那一道长长的伤疤,它突出来肌肤上,像一条蜈蚣趴着。
三、豫让桥南通秦蜀、北达幽并
据《赵城县志》记载:在县南十八里下纪落村有一座桥叫豫让桥,明朝正统年间(1436-1450),赵城知县何子聪将豫让桥建成石桥,改名为国士桥,后来坍塌。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写了五大刺客,依时间顺序排行,即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
豫让酬恩岁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
谁有当时国士心?
一条自北而来的溪水(石坡沟泉水)流至此处。两岸人家,有一条小石桥东西而立,桥再往南,溪水到此处恰好汇聚了一个洗衣的小池子,不远处是连绵的荷塘;春秋冬夏,这里都热闹非凡。而在此不远处有一桥是明朝古建,屹立百年。
奔跑的孩子和着平仄交错的杵衣声,老远就开始清脆入耳;桥下的河流顺着河滩的方向流去,一直向西通往汾河。水流声汩汩而过,草柳的长势如逢甘露,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春天扑面而来。
仰头望去,青苔在斑驳的墙体里桥嫁接南北;年代久远,气势雄浑(我自岿然)。记忆中,我们经常翻过桥两边的护墙,墙两边都有高低不均的土台堆积裹挟,这应该是数百年来岁月给予的恩赐。
土台之上有小道通往桥下,不知是人为开辟还是淘气的我们踩踏久了,便有了路。顺着内墙往下爬,有男有女,是大孩子的顽皮。
偶尔跌倒亲吻春泥的孩子,一不小心又跌进窄处的河道哇哇大哭,泥土的沁香和童稚的欢快都是children最好的礼物。开心的我们一般有两种组团方式,跟随父母的或是独立组队的,无论那种,都有各自的的取乐方式。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南宋)《小池》
他们的嬉笑声如同绕枝的藤蔓,在苍翠的季节琴声袅袅,温暖四溢;这一片古老而满怀生机的土地上光影渐变,一不小心,就穿越了时空。648年前,似乎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年份,历史的沉淀透露出对生命本源的思考。
尘封的记忆,被遗忘的繁华,大夏政权覆灭许久,但“蜀人楚籍”的呼喊却于此时定格。环顾四周,明初的许多移民移徙,大多都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加以表达,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也大多止步于此。而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也正源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