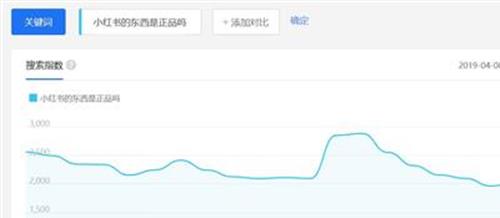余英时的书 余英时:究天人之际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文集》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
《论天人之际—— 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余英时 著 中华书局 2014年7月出版
杨河源
日前,12卷本《余英时文集》(精装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余英时文集》继2006年后再次进行增补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由中华书局出版。两书的出版在书界又形成了余英时热。

《余英时文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沈志佳博士编选,系统、全面地收录了余英时迄今为止在各领域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著作。余先生于84岁高龄撰文说,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
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本版刊登杨河源先生的文章,及《论天人之际》的书介绍,希望读者从中可“自得之”。
《国学与中国人文》收集了余英时先生西元两千年后的十多篇文稿,可以视为余先生在话题指涉领域的定论之作。虽然话题纷纭,形式不一,仍然可以归为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挑战-回应,这一几乎所有文化转型都可以用得上的基本模式,对于历史悠久而唯一未曾彻底断裂的中华文化而言,近代一百多年以来,可谓跌宕起伏、血泪斑斑。从乾隆朝的礼仪之争到道光朝的华夷之辨,从咸丰朝的“以夷制夷”到光绪朝的“中体西用”,从晚清民初的全盘西化到“走俄国人的路”,似乎都彼路不通,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大热。
这看似凭空出世的热潮,背后有长期价值真空的饥渴铺垫。对于国学,无论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教研专业,还是虽居异国但不放弃中国文化认同的“理解的同情”,余先生大概都会乐观其成的。
但余先生在梳理了“国学”走过的百年道路之后,不免担心:“以国学而言,由于老辈凋谢,继起的人很少,已无法维持‘国故’第二期(1917至1949年)的研究水平了。过去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现在或不免已解人难索了。
”诚哉斯言!这些年,媒体上有论坛、大学里有系科、企业有培训班,而只要还有点规模的城市,各种自发的“读经班”更是数不胜数,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不断扩充地盘的“国学热”,风头一时无两。但成色究竟如何?还真让人不敢乐观,且不提读经的头号“经典”《弟子规》不过当年的童蒙读物,即使“庙堂之高”的百家讲坛,于丹教授将《论语》勾兑成“快乐”的心灵鸡汤,与“道不行”、陈蔡绝粮、“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孔子,相去何止道里计!
国学也好,士人传统也好,士才商魂也好,儒家价值观也好,在高的层面,都会遭遇太史公的愿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集中,余先生用力最多、篇幅最大也最能启人慧思的,应该就是他论述中国哲学“轴心突破”的《天人之际》了。
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征的原生传统”,之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其他几个高级文明的“人”、“天”两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外向超越”而走上以“心”证“道”“内向超越”的心学传统,之所以有突破地面向而保留着连续的痕迹,其实在纪元之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决定了的:中国的“‘轴心突破’或可理解为与‘巫’传统的破裂。
有孟子、庄子的例子,我们可进一步看出,心对于‘气’的操纵与运用取代了以前巫与鬼神沟通的法力。于是,透过陶养心中敏感的气,所有的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巫师。”
天-气-道-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的这几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核心概念,经过余先生精彩的梳理,清晰起来。中文的“天”(道)究竟意指自然还是统摄自然的神,这一学者们普遍的疑问,余先生给出了答案:“‘心’是现实世界(人伦日用)与超越世界(道)的唯一交合之点。”“道”作为“存有与价值之源”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余先生留下的这块空白,刘明武先生的研究,也许能激发更多的话题。
经典中道的表述很多。“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系辞》中的这个说法,可能最为精准。“得道”者如何呢?“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按照刘先生的说法,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空的“道”,一个字表述是道,两个字是阴阳,三个字是造物主,四个字是自然法则。
这“恍兮惚兮”缥缈难明的“道”,体现在无所不在的“阴阳”上。阴阳在苗族古历界定为可以重复可以测量可以实证的两点上:“冬至阳旦,夏至阴旦”。
彝族天文历法的“阴阳”同样以太阳的运动为旨归,冬至大年,是年首、岁首、节首(二十四节)、气首(冬至一阳生,阳气之首)。“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素问》这句基本为中国哲学研究者忽略的中医经典的话,或者能为“道不远人”的“天人合一”研究开辟新路呢。
从“轴心突破” 开始的历程
《论天人之际》是探讨中国思想起源问题的一部专题研究著作。余英时先生借用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突破”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通过比较文化史的路径,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轴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大跃动,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余英时先生将“轴心突破”说用在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上,试将中国轴心突破的展开历程,置放于比较文化史的脉络之中,加以系统的叙述。
《论天人之际》的一大纲领在于断定三代的礼乐传统(也可简称“礼”)为中国轴心突破提供了直接的历史文化背景。先秦思想家如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状态则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展现,也是中国哲学性思维的全面而有系统的发展。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经历了轴心突破的古文明最后出现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诸子的系统性思维取代了巫的地位,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主流,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然而这一取代的历史过程是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论天人之际》的系统阐述让这一脉络清晰生动。
……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 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