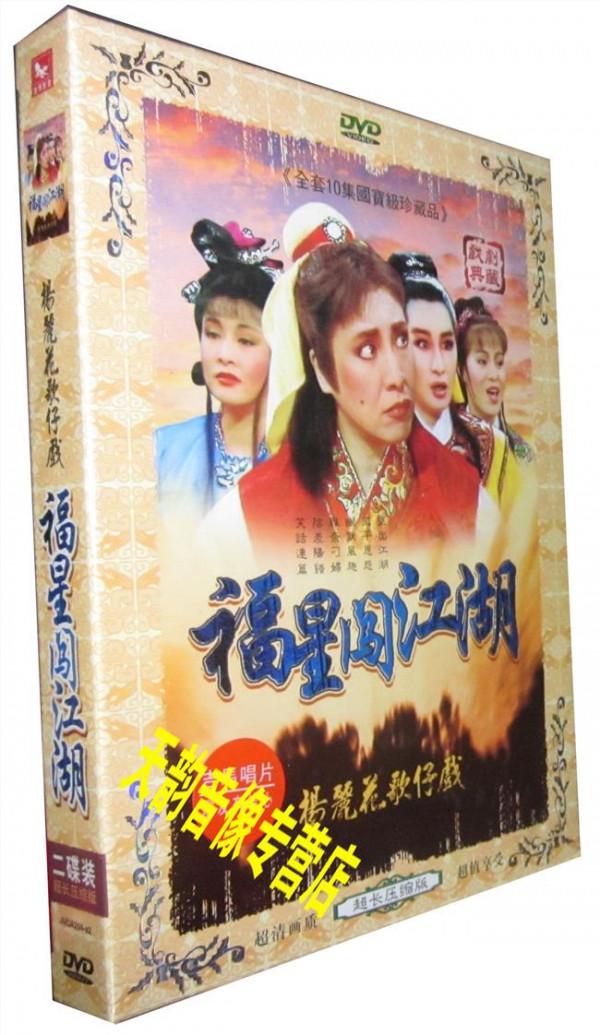杨丽花的现状 杨丽花|《玉合记》:性灵所钟 情自真淳
《玉合记》是梅鼎祚一部规模宏大、情辞兼美的传奇,也是昆山派扛鼎之作。甫一问世,在群星璀璨、佳作如林的明代中后期剧坛引起极大反响,称赏者甚众。戏剧家汤显祖、思想家李贽分别撰写题词和序言,剧评家祁彪佳、王骥德等盛赞,一时“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曲论》)。梅氏晚年在《长命缕记序》中亦不无自豪地宣称:“凡天下吃井水处,无不唱章台传奇者。”

梅鼎祚《玉合记》取材于《柳氏传》,除了在情节线索上更加迂回曲折、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更加细腻丰富外,在主题思想意义的进一步深化上也有着更出色的表现。《柳氏传》多少带有一些香艳气味,是对才子佳人遇合的欣赏,多奇异艳称;而梅氏“借脂粉以抒翰墨,托声歌以发性灵”,有意过滤了原作中的香艳成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青年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深藏于人性深处自然而然、蓬勃生长的美好情感,处处闪耀着性灵的光芒。

△《玉合记》书影资料图片
梅氏对“情”的颂扬和肯定,主要体现于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寻更为积极主动,对爱情的关注更加纯粹集中,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捍卫“情”的纯洁无瑕。《柳氏传》之韩翃贫窘,羁滞长安,与李生友善。李生幸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自门窥之,倾慕不已。

李生成人之美,将柳氏赠予韩翃。天宝乱离,士女奔骇,柳氏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后为蕃将沙吒利劫夺,与韩翃偶遇道中,“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无限深情,摇曳生姿。

而《玉合记》中的韩翃,一改原作中惊慌失措、懦弱被动的形象,衍变为积极主动,在章台偶遇柳氏,一见钟情,热烈追求,以爱情信物玉合相赠;遭逢乱离,生死未卜,千方百计找寻柳氏,感情真挚,哀婉感人。柳氏原本为李生的“幸姬”,梅氏改编为“待年之姬”,强化了爱情的专一性。
柳氏邂逅韩翃,芳心暗许,“假饶他碧玉多情,也须要明珠为聘”。在情爱的激荡下,柳氏甚至在李王孙面前也丝毫不掩饰对韩翃的好感,当李王孙主动提出将她许配与韩翃时,大胆允诺:“妾方待岁,不止周星。
弄管持觞,既免蒸黎之过;称诗守礼,何来唾井之嫌。”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情”的强大内张力,使向来含蓄内敛的传统闺阁女性,爆发出饱满昂扬的生命姿态。而“情”的最高潮表达,则是柳氏被劫,面对沙吒利的凌逼,坚决抵抗,以死来维系爱情的忠贞。
△韩翃资料图片
梅鼎祚写“情”的自觉意味,还表现在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敏锐捕捉和细腻刻画方面。如第三出“怀春”,描写柳氏情窦初开的爱情心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与柳氏独守空闺的落寞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唱词《棉搭絮》着力深化了此种心境。
第十七出韩翃中举后奉诏从军,柳氏渭水送别,她唱一曲《榴花泣》:“阳关一曲,幽恨写琵琶。(悲介)和泪雨注流霞,魂随芳草绕天涯,似东西沟水争差。”渲染出眷恋不舍、感伤悲凉心绪。第二十三出兵变爆发后,柳氏只身携带定情信物玉合,剪发毁形寄居佛寺,“一种妖娆,万般憔悴。
纵使人见,安得似前”,朴实无华的语句道出她内心的孤独凄凉和黯然神伤。第二十九出韩翃寄诗给柳氏后,她唱一曲《忆秦娥》更是沉痛:“空拖逗,爱离两字难参透。
难参透,夜灯风外,晓钟霜候。”黑夜、孤灯、秋风、晓钟等萧瑟意象交相错杂,充分抒写出她与韩翃分别后凄婉欲绝的心境。梅氏正是通过这些处理手法,对人物情绪表现得越细腻、越深入,充溢着强烈的画面感和代入感,作品对“情”的颂扬也就越有力度,更具有持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
梅鼎祚热烈张扬性灵思想,自觉表彰两性之情,乃由其自身经历、思想与时代所激荡。从作家经历来看,张扬性灵的文学思想,实乃梅氏屡遭仕途坎坷、理想破灭之后的自觉选择。梅氏出生于宣城仕宦之家,少年时才名即显,与文坛名公巨子多有交游,满怀“丈夫当经纶雷雨、参成天下”之志。
可惜,多次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阻断了他入仕的道路,幻灭了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被迫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现实处境,使其滋生挫败、焦虑和孤独的心境。同时,又不断受到宗族内部纠纷的牵缠,且接连遭遇多位至亲的相继辞世,体认到生命的不自由和精神的极端苦闷。
这样的悲剧性体验,使得梅氏不得不开始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寻找新的生命支撑点,遂转而追求独立的自我,关注一己之心灵,弘扬自我之性情。这种人生转向投射到文学创作中,便是认同和坚持“曲本诸情”的文艺观,对人性、个性和情性进行酣畅淋漓的抒写,借以凸现性灵的觉醒。
从时代思潮来看,万历年间,以王畿、王艮为代表的王学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迅速风靡开来,对禁锢、约束人心的传统权威秩序提出激烈挑战,肯定日常生活、内心情感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追求心灵的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况且,梅氏十多岁时就与王学思想家罗汝芳、王畿等名士结识,听其讲学,接受熏陶,渗透于文学创作中,自然形成梅氏重情的创作观念。
另外,同汤显祖的交往对梅鼎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万历四年(1576),梅氏与汤显祖相识于宣城,诗酒流连,惺惺相惜,结下此后长达四十年情深意笃的友谊。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杰出天才,汤显祖尊情、重情的艺术思想,深深影响了梅氏戏曲创作的主旨,“情”成为梅氏戏曲创作的灵魂和动力。
△汤显祖 资料图片
显然,《玉合记》对情之张扬和人的性灵觉醒,与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思想一脉相承。屠隆《玉合记叙》称赞备至:“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
二百年来,此技盖吾得之宣城梅生云。”并且说《玉合记》传奇“洄洑顿挫,凄沈淹抑,叩宫宫应,叩羽羽应,每至情语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则至矣,无遗憾矣。
”梅氏将一篇千余字的小说,改编为长达四十出的戏剧,文本的蕴含量明显增强。与之相适应,突出主题,采用更加婉曲周详的叙事、更加多元立体的情节来扩充作品的容量,同时使得传奇这一体裁的本质特征——故事的传奇性大为加强。
因此,《玉合记》在基本依照唐传奇叙事的同时,浓墨重彩书写了“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大量穿插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宸游、李王孙与轻蛾入道成仙、侯希逸与许俊练兵、沙吒利归顺等次要人物和情节,造成故事的多线索发展。美中不足的是,梅氏对详略的剪裁略有偏颇,一定程度上造成全剧关目冗杂散漫,如李贽所言:“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紧要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谓之不知趣矣。”
作为一个一生徘徊于主流体制边缘、以布衣终老的朴实学者,梅鼎祚改编、重塑“章台柳”故事,在作品中表现性灵思想,更见这一思潮波及之广泛,彰显晚明“人之觉醒”的社会真相,恰恰印证了“文学就其深刻意义而言,乃是精神史的载体”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