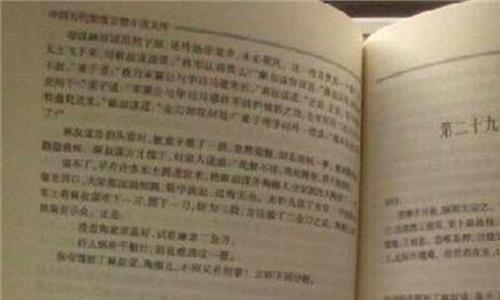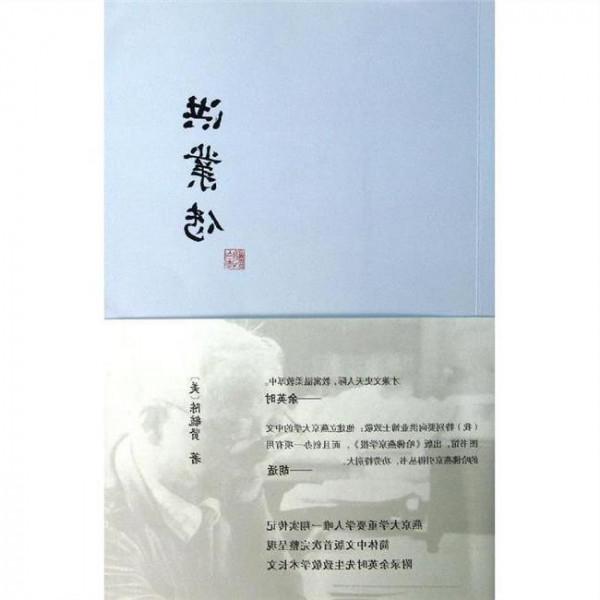余英时钱穆 余英时评价钱穆先生:一生为国故招魂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我的老师钱宾四先生逝世使我这两天来的精神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已写了一篇《犹记风吹水上鳞》,记述我和他在香港时期的师生情谊,那完全是个人观点的杂忆。现在再写这一篇《一生为故国招魂》,是想扼要说明钱先生的学术精神。

但这也只能代表我个人对这一精神的初步了解,远不足以概括钱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和意义。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

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我现在所以敢匆促间尝试写这篇文字,是由于我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钱生的学术著作我确实读得很仔细,有些更反覆体味过许多次。
第二,我曾有幸列于他的门墙,四十年来,不但听过他的正式讲授,也和他先后有过无数次的讨论。但是必须声明,所有钱先生的弟子大概都具有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在他的弟子之中,追随他比我更久更密切也大有人在。
因此我在下面所介绍的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但如此,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这正如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现在所强调的仅仅是他"为故国招魂"的一面。本文开头所引的是我刚刚写成的一副挽联,我想用它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而且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钱先生的斋名之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素书楼"则指无锡七房桥的旧址,不是台北外双溪的那所楼宇,因为后者不过是前秆的投影,而且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十六岁萌发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深入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
这篇文字主要是以"沧江"和"明水"两人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的。"明水"提出种种论证指出中国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而"沧江"则逐条反驳,说中国绝无可亡之理。
两人的问答一层转进一层,最后说到了中外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直到"明水"完全为"沧江"所说服才告结束。后来我们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沧江"是梁启超,"明水是汤觉顿。
这篇文字的题目也不是"中国不亡论",而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的《国风报》上。一九一〇年,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
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后来我读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时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学夜读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至于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
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钱先生又屡次说过,他非常欣赏梁启超所用"国风"这一源于《诗经》的名称。不用说,他早年也受到了《国粹学报》(一九〇五~一九一一)的影响,对于"国魂"、"国粹"(借自日文)、"黄帝魂"等流行观念是同样能够欣然接受的。
当时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有"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不过"五四"以后,这些观念在知识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来钱先生改用"中国历史精神"这个观念,意思还是一脉相通的。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
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
"中国不会亡"的历史根据何在?此一念当时便引申出了无数的历史问题。《国粹学报》中人如刘师培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指出中国史上的治乱循环是因为进化的阶段尚浅,西方则治了便不再乱。梁启超写《新史学》曾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
(按:以一史归一姓,可见任公当时情感之激动。稍一寻思,岂非笑话。)这一观念旋即为《国粹学报》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扬.流风至今犹在。至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专制,更是上帝在"最后审判"中所下的判决词,毫无上诉的余地。
从此以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
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因此国粹学派本身即包含了一个无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国粹"、"国魂",有人以为此"魂"寄托于历史,有人以为哲学(儒家和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为文学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则视为天经地义。
所以刘师培力证中国古代,也有石器、铜器、铁器三级,邓实则深信耕稼为君主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分别即在处于此二不同的阶段。他更明白宣称:"此黄人进化之阶级。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然而同一个邓实却又痛斥当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