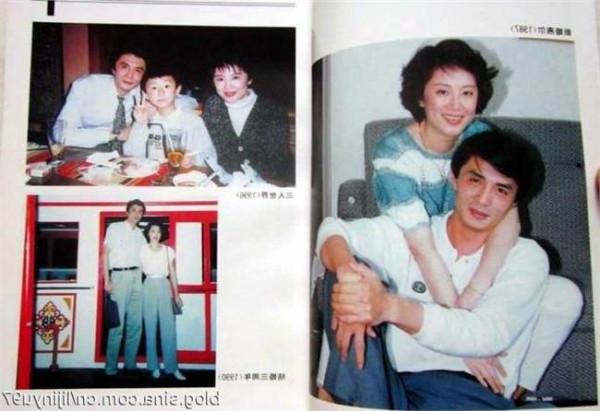汪曾祺故居 高邮汪曾祺故居行
原来汪老的文字早已在此迎接我们了。
这样相遇虽非第一次,却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最动人心魄的一次。我扭头看同伴,相顾大笑——“咱们到了。”
可还得走。
渐渐从小巷上了大街,看着不对,得找人问路,这次找了一位年轻人,年轻人听得懂普通话,会说普通话,年轻人也性急,方听说我们在寻找“某某的故居”,便朝反方向一指:“你们走错了,看秦观在那边!”“小伙子,别走!我们看的是汪曾祺。”

想想好笑,二老都成仙了,上哪儿看去?
果然走错了,回头继续穿巷子。高邮的巷子,我觉得亲切,窄而洁净的巷道,青砖和灰色的矮房子,甚至满天蛛网般的电线,露天开口的茅厕,都让我想起十岁前住过的老院子。这地方和我有缘,甚至有神秘的玄机。那么多的似曾相识,譬如大淖,像极我梦里垂钓的乐园,譬如街衢和里巷,毫无陌生感,以致边走边念叨“我来了,我来过?”而前面路过的小街,总共五六间店子,有两家的招牌里竟嵌着我和同行者的名字,真是有趣。

高邮给我的感觉像家,一个现实中已不存在,只在梦中还常常回去的家。
汪老的故居是“突然”出现的。明知走在竺家巷上,明知“9号”马上出现了,可真站在门口了,还是需要适应,因为它太普通,除了钉着几个“标明身份”的牌子,便和其他民宅没有不同了。它低矮的青砖门脸是民用的,它的保险门窗是民用的,它门上的对联是民用的,它的里面——一定还是民用的!

然而轻轻叩门,久无应答,我说走吧,或许已做展馆了,而我们来得不巧,不是开馆的时间。或许命里注定,此行要“留一大白”。如汪老笔下耐人寻味的伏笔。
可同伴很执着——“可能还有人住!”,乓乓乓,持续而坚定的敲门,过了一会,防盗门竟“嘎吱”开了。

门里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花白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笑容可掬,并不以为遇到了土匪,一边把我们往屋里让,一边说到:“卜豪意思哦,偶们栽里便,偶们莫听见!”
就这样,一步跨进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故居的客厅。进屋先看见汪老的照片。这是一张抓拍照,汪老左手支肘夹烟,视线看向上方,像是一个谈话的瞬间,嘴微微张着,像是刚吸进去一口烟,又像是将吐出一句话来。据说这张《纽约时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最得他的中意。
为我们开门的是汪老妹夫金家渝先生,他和我们寒暄,朝里屋喊了一声“丽纹,有客人喏!”可屋子实在是小,说话间,客人已不知不觉穿过客厅,迈进了起居室,就这样仓促的与一位气质相貌绝佳的女士相遇。
汪丽纹女士是汪曾祺先生同父异母的妹妹,七十岁年纪,比1920年生人的汪先生小了不少。宾主落座,久仰之类的话不说了,跋涉千多里,由浙入苏,摸寻而至,正是一种情愫无言的表达。还不止这些呢,一想到身处大淖旁,汪老故居中,访客的心情不由激动了;墙上挂着汪老画的马铃薯花,周围包裹着熟悉的文字,对面说话的是汪老家人,这一切,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听,门外是什么声音?感觉到这会儿只要站起来,推门出去,就能看见“岁寒三友”聊着天走来,看见十一子和巧云拉着手儿去大淖,看见小英子和明子有说有笑的上街耍子,看见“故里三陈”正操持各自的营生,看见戴车匠、王医生.
.....
火眼金睛要耐得住三味真火,练成了不看则已,一看必穿人肠肚。汪老的文字亦然,不写则已,写就了字字直入人心。他是怎么做到的?“空灵天生,心手不歇,简出于繁,举重若轻。”这是我的看法,可惜斯人已逝,不能当面请教,不然呈以拙文,敬以醇酒,岂不快哉。
我常自得,与汪老相似处有三:写作,下厨,爱喝酒。其实还有一个相似处我不好意思讲——汪老固然是真人的,我也是一个直人。虽然少了不止一点,真和直多少还能互通。常想起汪老酒后的痛陈:我们啊,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善良!为了这个善良,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也想起汪老的释怀: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活得快活!
我们谈汪家的前世今生,谈汪老作品的深重影响,谈汪老文字里丰富温暖、深远炽烈的人性光芒,不知不觉日已偏西。告别的时候,我像在述说一个箴言般的,庄严地对汪丽纹女士说:“您看着吧,汪曾祺先生的雕像有一天将竖立在高邮的街头,北京的街头,乃至每一个有文字存在的地方!”汪女士点点头,说了声谢谢。
忽然觉得自己口气好玩,忽然想起江苏之行的诸般好玩,遂以汪老的名言为人生中已结束和即将开始的旅程做个陈词——“生活,是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