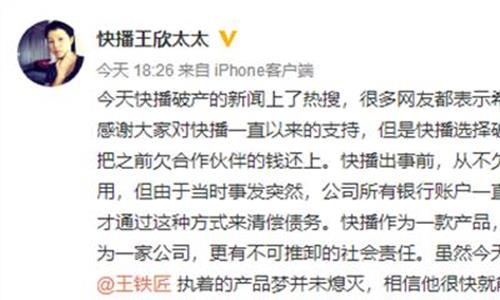彭修文与彭家鹏 彭家鹏 一个浑身都是音乐的人
观赏过彭家鹏的排练和演出,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浑身都是音乐”的人。他的音乐意图非常明确,乐团的乐手能够迅速领会;他的肢体语言极富表现力,又能准确地控制速度和力度,瞬间将全场观众的视线牢牢锁定。

6月4日,彭家鹏与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合作演出的“龙舞狂想·跃东方”民族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四年前,他就曾与天津歌舞剧院合作,执棒歌剧《原野》成功参演“首届中国歌剧节”,该剧荣膺七项大奖,他本人也获得了“优秀指挥奖”。

演出结束后,彭家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提到自己不久前指导过天津某学生乐团的排练,“我站在指挥台上,就立刻忘记他们是学生乐团了,我并没有把他们当小孩,完全按照职业乐团的标准要求他们。音乐就是这么神奇,他们再小,却能理解你说的话,按照你的要求,马上就做到。排练时间不长,那个乐团的整个演奏状态和音乐思路已经开始跟我配合了。指挥这个工作很神奇,有些东西说不清楚,不同的指挥都有不同的气场。”

曾有音乐评论家评论彭家鹏的指挥风格:他把朝气蓬勃、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生活气息糅进了他的指挥艺术。在他的指挥艺术中,不仅有西洋指挥圆润、流畅、宽广的线条特征,还具有中国音乐讲究气韵与顿挫的民族特征。

“浑然天成”背后,总有一段艰辛岁月。与彭家鹏交谈,很多故事他都喜欢用“辛苦”二字来起头,而我发现他恰恰是“苦中作乐”的好手:被迫转战民族管弦乐领域时,他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研究,买了很多的磁带、唱片,更积极地推进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交响化的探索;首登维也纳金色大厅时,他曾向欧洲音乐泰斗布拉威挑战,只为扭转西方人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吵闹、猎奇”的既定印象,演出结束后,布拉威称赞彭家鹏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最好的指挥和最好的乐队”,维也纳音乐界评价彭家鹏的指挥风格是“小泽征尔和穆蒂的完美结合”;在欧洲观摩学习交响乐歌剧,他曾经拿着一个汉堡,在剧院一坐就是一天,只为欣赏大师的非公开排练,为舞台上的纵情挥洒和精准表达积累更多能量。
兜兜转转,彭家鹏终于成长为一名指挥交响乐和民乐“两栖”指挥家。
在彭家鹏眼中,指挥这个职业反差太大,在指挥台上风光而鲜亮;走下指挥台,有时会觉得冷清而孤独。夜深人静时,他常有很多困惑,比如民乐什么时候才会获得与交响乐同等的支持和资源?明明自己交响乐指挥得也很好,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他只会指挥民乐?会不会有更多的交响乐指挥走向民乐,这条路实在太疲惫……然而太阳照常升起,一切的感慨都催促他加快前进的脚步。
分享过去在巴黎听歌剧见闻时,彭家鹏说,在巴黎最大的好处,是你完全没有时间去做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以外的任何事情。而彭家鹏的人生也没有时间处理民乐、交响乐和歌剧等音乐之外的事情,“如果有来生,可能不会再做指挥这个职业。我在排练时经常说这句话,这是我的感慨。这辈子已经没办法了,没有音乐,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民乐一听就上瘾
记者:您为什么放弃在西乐上的发展,投入到中国民乐事业中来?
彭家鹏:在欧洲的大师班学习后回国,正好原来的交响乐团重组,我被调到创研所工作。当时原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指挥彭修文去世,民族乐团缺指挥。广播艺术团的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民乐团兼任指挥。我刚从欧洲回来,受西方教育熏陶,又是学习西乐出身,尽管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全国顶尖的民族乐团,但心理上我仍很难接受这样的安排。
可是,我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香港的第一次合作,改变了我对民族管弦乐的印象,我发现有些民族音乐很好听,也的确能看出广播民族乐团良好的素质。我并不是为了振兴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不敢这么说,我就是热爱我的事业,只是换一种方式坚持而已。现在看来,我还是跟民族管弦乐缘分更深一些吧。
记者:1998年年初您接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和艺术总监,为了民族管弦乐团更快进步,您注入了哪些自己的想法?
彭家鹏:广播民族乐团是一个非常棒的乐团,不可能随便找人当总监。乐团的前任总监彭修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班也不好接。从指挥技术角度来讲,在担任首席指挥之前,我跟他们有过多次合作演出,保留曲目已全部吃透,得心应手,但担任艺术总监就有些难度。
民族管乐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西洋管乐那么“合群”,个性比较突出。这就要求在训练乐队时会更辛苦一点。演奏民族乐器的这些艺术家个性都太强,让他配合旁边的人,一般很难做到,他觉得就应该他展现,可如果每个人都展现,乐团就乱了。
我从指挥的整个状态、动作和指挥技法上做了很大改变,比如某个团员一直弱不下来,指挥就一定逼他弱,指挥的动作就小到让他不能动为止,看他还大不大,再大你就不动了,这还真管用。所有的东西也是在实践中去摸索。
记者:您也担任了澳门中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您是如何与澳门中乐团结缘的?
彭家鹏:很偶然,本来我去澳门中乐团观摩,没有表演任务,正好他们的指挥马上离任。他们说,反正彭家鹏也来了,干脆让他指挥半场。临时指挥了半场以后,他们觉得我好像跟其他指挥不太一样。当时他们选了7个候选指挥,每个指挥去工作两个月,然后由团员打分,领导再选。我在7个候选人之外,但也客座指挥了两个月,结果他们选了我。
我刚刚到澳门的时候,澳门中乐团是一个有点半职业性质的乐团,乐手们白天去上班,晚上来演出。他们请我去也是想改革,转变成职业乐团。他们开始看简谱,我让他们看五线谱,有些人没学过,就自己学,在五线谱下面标上简谱。
一点点“招兵买马”,排练时,因为水平参差不齐,就要花很多心思,也占据了我很多时间。这是我做得最辛苦的指挥,但也是成就最大的。毕竟澳门中乐团现在已经属于一流乐团了。我们几年前来天津演出过,当时反响还不错。
记者:多年从事民乐指挥工作,您对于民乐指挥这个身份有哪些新的认识?
彭家鹏:现在看来,中国的民族管乐想要发展,还需要真正学西洋音乐、指挥交响乐队的人。因为西方的指挥法和指挥艺术是非常科学的,对交响乐队非常好。民乐本身是不可能产生指挥的,很多都是业余的,有些打打拍子就算是指挥,这样民乐团不可能发展。但是,民乐团的指挥必须是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如果让外国人来指挥,那也肯定不行。
指挥家不是表演者
记者:很多人心中有个误区,认为民乐简单,西洋乐难度更大。
彭家鹏:其实中华民族有着悠远深邃的历史文化,是民族音乐发展的根。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作为指挥,一旦踏入这个圈,就会期待它能够变得更好,愿意为它付出一切。
刚开始指挥民乐的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尝试,然后开始巩固,积累经验。这条路我走得很累,很辛苦,得到的却不一定都是称赞,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很多人讨论你这条路走得对不对,民族管弦乐能不能交响化?不同的声音太多,常常让我觉得更累。但是,在民乐团做了这么多年,很有感情。通过这几次巡演,我发现我们已经有了听众基础,也就要求我们将来要推出中国的好民乐。
记者:除了民乐指挥外,您也在指挥交响乐团和歌剧,您对这三个不同的音乐方向作何理解?
彭家鹏:要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指挥民乐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它一点不影响我指挥交响乐甚至歌剧。我指挥过很多戏曲,京剧、越剧、豫剧、沪剧都指挥过,再指挥西方歌剧觉得好像没什么好学的,水到渠成。其实从荷兰大师班结束之后,我就不需要在指挥技术这个问题上再去下功夫了,因为技术已经伴随我很多年了,已经很成熟了。
最主要的是怎么才能通过技术,把音乐体现出来,让乐队队员明白指挥的意图,把握好作品的风格、速度、力度和声音、音色。
记者:从2000年至今,您连续多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指挥了“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中国新春交响音乐会”,并先后率领中国东方交响乐团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赴瑞士、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演出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常年在西方演出您有哪些收获?
彭家鹏:在国外演出学习期间,我会大量观看各种演出和排练,更多地去观察大师对于音乐的处理,而不是他们的姿势、动作。就像优秀的钢琴家,他的钢琴弹到一定程度时,所学的就是音乐的分割和表现。有些人成才,除了机遇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音乐独到的理解。
比如说很多人质疑郎朗,说他家教很严,是被逼出来的。郎朗的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演奏方面确实有独特的东西。这个世界需要郎朗,也需要李云迪。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比较,一定要问到底是郎朗好,还是李云迪好,到底是彭家鹏指挥得好,还是李心草指挥得好。
推广中国原创歌剧
记者:您曾与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成功合作歌剧《原野》,并在首届中国歌剧节中摘得七项大奖,请您谈谈那次合作演出的经历。
彭家鹏:当时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要参加首届中国歌剧节,选择了歌剧《原野》。我指挥过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原野》,当时请歌剧《原野》的作者金湘先生去看,看完后他觉得《原野》已经演了好多年,中国很多比我有名的指挥家都指挥过,但我们演绎的《原野》又有了新的味道和意境,他特别喜欢我对音乐的解释和处理。
他把我推荐给天津歌舞剧院的高久林院长,当时我跟高院长并不认识,但高院长知道我,他说彭家鹏来了我们求之不得。这就是缘分,一拍即合。
记得排练第一天,挺吓人的,我说能换指挥吗?我不想指挥了。为什么?我以为刚刚排演过,一了解才知道,他们是四年前演过。后来的过程很艰难,但是也跟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白天排练,晚上聊天。后来我们到福州比赛,给我们安排的场地在长乐机场附近的歌剧院,没能在福州最好的大剧院。在演出场地不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拿了七项大奖,说明大家的确都用心了。
记者:您之前曾说过,可能未来工作重心会偏向交响乐和民乐,您多年来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广歌剧,怎么看目前中国歌剧的现状?
彭家鹏:推广歌剧我觉得要两手进行,一方面是西方的经典歌剧,另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推广原创歌剧。因为中国人习惯听西方歌剧的还仅限于圈内人,老百姓(603883,股吧)不会去听的,首先是语言障碍,其次是文化障碍,能去听交响乐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打造一个更适合中国人听的歌剧,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剧本,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交响乐版歌剧,一个是民乐版歌剧。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指挥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彭家鹏:其实指挥并不是一个多么潇洒的职业,而是特别辛苦的。如果只为了自己的动作好看,去设计,再去排练,这就本末倒置了。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指挥像一个很冷静的导演或将军一样,要在乐队面前把音乐拆解得很清楚,告诉乐手应该怎样去完成每个环节,然后把整个音乐“组装”起来。
这个时候,指挥要考虑如何跟乐队在一起,参与到乐队的演奏中,这才是一个职业指挥家应该做的事情。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某一位指挥大师的动作,模仿他对音乐的处理方式,就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
反过来说,我们去模仿小泽征尔也好,模仿卡拉扬也好,模仿得跟他们一模一样了,指挥出来的也依然不会是卡拉扬的东西,这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去做一个模仿者,也不一定非要做创新者,而是要做一个发自内心的音乐表演者,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速度、自己的力度、自己的音乐语言。
然后就是积累,这不是天天在家看谱子就能练成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地和不同的乐团、不同的音乐家交朋友,跟他们谈艺术,聊音乐,去看很多大师的排练现场,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彭家鹏口述 每个学音乐的人都有指挥梦
我父母都是在歌舞团搞戏曲,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他们演出的地方,后来父母告诉我,只要舞台上音乐一响,我就会跟着打拍子,大家评价说,“这小孩乐感很好,律动和音乐都是一样的。”
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我学的是作曲、理论和钢琴。有一次同学一起拍照,我做了几个指挥动作,刚好就被指挥系的老师发现了。他说,“哎呀,你应该学指挥,感觉多好,比我们指挥系毕业生都好。”过了两天,那个老师又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兴趣考指挥系。
我觉得所有学音乐的人都把指挥看作最高境界,内心想学但苦于没机会。可是,当时距离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他说,“没关系,我教你一部作品,你先学会,可以作曲、指挥一起考。”我报考了作曲和指挥两个专业,都考上了,最后选了指挥系。
硕士毕业后,1996年和1997年,我先后两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大师班的学习。第一个大师班在荷兰,是以俄罗斯指挥家康德拉申命名的,他一直在欧洲生活,是他把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爱乐管乐团推向了世界顶尖乐团的位置,在荷兰影响力非常大。大家为了纪念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那个大师班非常难考,必须在康德拉申指挥比赛中获得前三名才有资格报名。最后整个亚洲就录取我一个,全世界选了12个人。
在中国,指挥技术的学习大部分以模仿为主。到了荷兰,我开始独立思考。乐团老师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还会教一些乐队心理学知识,例如在乐队面前该如何做一个领导者。那段时间的学习彻底改变了我对指挥的认识。虽然全世界只精挑细选去了12个人,但最后拿到证书的只有8个人,给我们发证书的是康德拉申的太太。
1997年,我又一次被破格录取到乌克兰的大师班。在那里我师从爱迪·罗丹和梅耶尔等世界著名指挥大师,他们培养的学生目前都活跃在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我在这个大师班学习了弦乐的弓法、管乐的呼吸、各声部的平衡,细到对每一个音符的处理。我以大师班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学习,并成功指挥了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的两场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