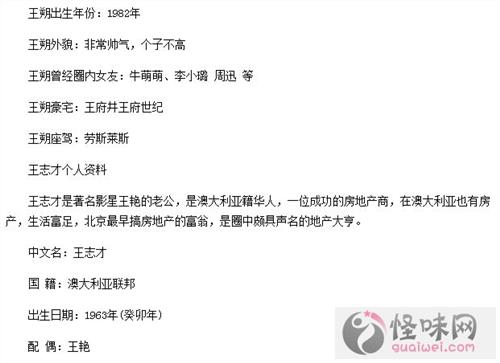动物凶猛王朔 凶猛动物——王朔的火焰与海水
4月11早上,接到新经典总编杨老师的电话,说是看了我的文章《我们在池塘湖底——致王小波》,惜才,邀请我参加12号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办的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活动。我诚惶诚恐,概因一眼瞥见同时出席的名单:蔡骏、韩松落、绿妖、徐则臣和张天翼诸位老师。我高中时代看过他们的书,所以当晚演说时不免紧张。但能如此近距离地听作家们说起另一个作家,这种感受确实很奇特。

徐则臣老师在说到王小波的时候,提及了王朔。他说这两人是给汉语写作松绑的作家:
“在王朔之前,口语似乎从没有如此大规模地进入汉语小说,他给小说的‘说’正了名,即使之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方言写作,依然没有把汉语小说从端庄的书面化中解放出来。或者说,他把小说之‘说’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重要,让小说里自始至终飘荡了一个真正日常的口语。不管这种口语化于小说的这一艺术文体而言是否科学,大概也没法否认,王朔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当代汉语小说叙述的生态。然后是王小波,毋庸置疑。”

这是徐老师演讲的文字版本,但当晚他脱稿而谈,说得不尽相同。大概是说中国至明清以来涌现许多小说,有很多篇幅很长富有世俗气息的对话,但只是寻常的市井闲聊,直到王朔这儿,这些“说”,才成了日常,成了小说的核心。一堆人在那叽叽喳喳的说话,而且说个不停,满篇的人物都在胡侃。他说至此,我没忍住扑哧笑了。这“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确实是我在读王朔的书时最直接的感受了。

王小波也谈过王朔,但三言两语带过了:“与王朔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些作品里带点伍迪·艾伦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这就没法喜欢。总的来说,他是有艺术成就的,而且还不小;当然,和伍迪·艾伦的成就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伍迪·艾伦的电影我看过不少,觉得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絮絮叨叨。而八十年代就说出“流氓都去当作家了”的王朔,向来爱拆的,就是精英们的台子和西洋镜,他还不无讥讽地调侃他们只是“知道分子”。王朔喜欢以“流氓”自我标榜,他也同样絮絮叨叨,不过不是精英式的,而是小市民式。
他爱在公众面前把自我的姿态放得够低,内心留着傲慢。我总觉得他的骨子里是悲悯的。没有悲悯,就遑论艺术创作的深度了。他很狡猾,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但这种悲悯,让我觉得他深沉,就像梁左。
毫不夸张地说,王朔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我全看过,大部分都喜欢,最偏爱的是他的两个长篇《我是你爸爸》和《看上去很美》,中篇的小说则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顽主》。
虽然识其文风许久,可真正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朔,还是大学时看《锵锵三人行》。他样子不蛮横,没有老气,甚至有着几分清秀,可以想象年轻时一定嫩得可以,可能还带着稍许害羞和机灵。其实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中出境过,确实眉清目秀,而他的角色身份却是“胆大手黑,威震北京的小坏蛋”,这当然是姜文或他自个儿要求的揶揄。
我算明白了梁左的那句玩笑话,他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
窦文涛和梁文道本是非常能说的主,可是碰到“侃爷”王朔,根本插不上话。王朔的语速很快,让人诧异他的脑容量之庞大。我能想象他写《顽主》等完全用对白组成的小说时,一定也是边写边狡黠地嗤笑,词语想必一个接一个蹦出来,他只要一铲接一铲地往纸上搬运就行了。文思如尿崩,写到绝妙处,难免不击案自觉牛逼。
他在节目上谈到自己在北京大院长大,小时候看的都是第一手的政治资料,还都是军队内部文件。这种军事情结,一直就延续到他的阅读喜好上,如偏爱《张国焘回忆录》和《丘吉尔回忆录》等。大院的孩子都有这种情结,甚至连一帮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用的都是军事扑克。相较于大院里人高马大的孩子,他已经算文气和安分了,可仍然能轻松翻过两米高的墙,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憋一天不出来。
他公开说自己有着“反社会”和“攻击性”人格。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坏,有的人喜欢把对外界的姿态,或社会人格的部分,自我贬低,免得苦心去经营形象。他身上的那股无赖劲,无非是后天形成的伪装和保护,这是对他童年期父母“缺席”的后天的自我补偿。他内心何尝不孤僻敏锐,一个不脆弱与敏感的天才,是难以驾驭如此纷繁复杂的创作的。
阿城在《脱腔》中有说,王朔是“一个共和国的善良的人,现在这样的人罕见了;一个心理上,我的观察是在童年受过伤害的人,容易害羞,但从动物行为学讲,害羞不是软弱,而是抑制机制,抑制的是攻击性,进取性。我从来不理文如其人那一套,所以也无所谓反差”。
阿城眼光真准,评价得在理。我从王朔的作品中看到的就是此种感受,他夸张了自己的攻击性,却讳言了自己的善良与温情。
马未都曾说:
“王朔有个能力,就是凡是他经历过的生活,哪怕一个生活场景,哪怕我们大家在一块聊天,他都能够逼真地高于它再现,这是他的能力。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小说,一定是有事的,一定是有过这段经历,绝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这是他创作的一个秘密。我认为他的文学能力强在这,就是他观察事物的那种仔细。”
所以从王朔的写作中去寻觅他的自小的经历,是可靠的。王朔爱看侦探小说,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如《人莫予毒》和《枉然不供》等,但不为人知。我自知自己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无疑也是当着文字荒原里的侦探,一点点建立对他的认知和判断。
《看上去很美》这部小说是他对自己“人之初,刚落草”时的模糊又真切的经验记录。他和那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在群宿环境中长大,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
不必像福楼拜那么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也能知道,方枪枪就是王朔。他坦言自己“小时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像自己”。
在张元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中,幼儿园也是一种监狱,是集体主义对于个人主义的压制,体制对个体的规训与惩罚。其中有一幕,当老师们抓到和陈南燕睡在一起的方枪枪,开始围着他哄笑,在这萦绕着的笑声中心的方枪枪,一脸无辜与茫然,他也跟着笑,开始还笑得童稚纯真,后来,这笑容渐渐变得无所适从,无奈到让人怜惜,甚至一度要成为哭泣。
在小说中,王朔描写了方枪枪,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他自己,对于黑暗侵蚀而来的感受:
“夜晚不是光线的消失,而是大量有质量的黑颜色的入侵,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些黑颜色有穿墙的本领,尤其能够轻易穿透薄薄的玻璃。完整平均的黑暗使我瘫软,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明知同室还睡着那么多人也不能给我丝毫安慰,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磨牙声、梦话声更突出了我的孤立。本该大家一起害怕的东西全要我一个人面对。”
这种黑暗的经验,如梦魇般,不仅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他认为老师是妖怪,要吃掉他和他的朋友们。他拉着陈南燕的手,试图逃出这监禁,可是外面是个医院,他无处可遁形。老师教训他,唬他最终也要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他害怕。成人世界的运转逻辑始终包围着他,到最后他被集体孤立。谁说孩子就没有孤独?这大概就是王朔压抑的童年期的真实写照。
想到王朔的时候,我不会想到他的嬉笑怒骂,他的争议和孤傲,他喋喋不休的胡侃,反而一张深沉且悒郁的面孔会浮现出来。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他在《致女儿书》中,对于自己的家庭的记录,总是诸多和父母的争吵,大吼。有些话看了让人唏嘘: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我是你爸爸》中的很多桥段,似乎都来自他自己的感受,这在《致女儿书》中证实了。王朔抱怨父亲脾气差,对于孩子交友的干扰太多,对他的朋友很不客气,还会教训他们,这让他觉得父亲很失态。他怕他的父亲,这个父权的形象让他望而生畏。而母亲并未填补这种失落,她专制,在家独大,不知尊重与理解孩子。
中国式家庭的感情,大抵就是这样隐晦与深沉,每个人都如同难以摆脱身上毕露的刺的豪猪。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开诚布公地相互坦露过自己的真实内心,可能没有,所以在《我是你爸爸》,王朔用文字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的最后父亲和儿子最终互相谅解,而现实中,王朔的父亲早早离世,他在父亲去世后曾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不要再和母亲吵架。但很遗憾,他没有做到。
在博客年代,洪晃谈到王朔和徐静蕾的关系时说:“小时候多少是被自己的母亲惯坏了,为所欲为,所以需要一个女人为了他赴汤蹈火,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呵护。”这话说的十分刻薄,可是有一点她说的对,王朔是没有长大的。
他内心始终还是那个叫方枪枪的小男孩。他自小缺失的部分,在往后被他用暴戾补上了。
王朔的青春时期,被他花了不少笔墨记录在《动物凶猛》中。北京复兴路,方圆十数公里被他视为出身故乡,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这一带被他称之为“大院文化割据地区”,他“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的习气莫不源于此”。到现在“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
这些东西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种属于年轻人不计后果的莽撞与直率。
姜文把《动物凶猛》改编成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除却时代的印记,每一代人的青春几乎都是这么相似。我还喜欢叶京根据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改编成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青春在王朔的笔下大抵就是挥霍不完的热情,被压抑的欲望,无处发泄的能量,晒得黝黑的面孔,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落下,炽热焦灼,又无处安放。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太酷了。电影《顽主》,三个主角选得特好。张国立、葛优、梁天,他们仨穿着衣冠不整的衬衫,就这么双手一插兜,百无聊赖地往那路口一站,那种八九十年代的味道就出现了。他们奚落着正经,嘲弄着一切他们视为权威的东西,满嘴跑火车,揪不出半句真话,逢人就开涮逗乐。王朔唯一一部导演的电影《我是你爸爸》中,胡同街口站着的,也尽是这些叼着烟流里流气打台球的青年。
王朔的小说给了我关于八九十年代的青春的想象,他笔下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然卓尔不群,俾睨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这些人邪里邪气,不苶不傻,油腔滑调,蔑视着伪善,这是一个对经历过的假正经假大空时代的矫枉和反讽。譬如,他在《一点儿正经没有》中对于作家这个行当极尽冷嘲热讽: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家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痿。’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在我印象中,王朔最凶猛的时候是在2007年。那会儿我还在读初中,老是能从报刊上看到他在骂人,把诸多地域的人贴标签式的骂了一通。当时心想,这孙子真是乖戾,所以到了很晚才看他的书。可是我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他,却有一种不自觉的同情。冯小刚和他闹掰,父亲死了,哥哥死了,梁左死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在那时深深攫住了他。
他的这些暴戾,或许也是源于内心的坠落,对人间事的意兴阑珊,失望沦为虚妄,兴致寡淡,索性就自我放任。他的好朋友马未都曾说过一个细节:
“他们家住的门口有一修自行车的。他看着他就烦。然后他突然走到那人跟前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不能离开这?别让我看见你。’那人说行。王朔就回屋,拿出了三万块钱,就给了这修自行车的。那人就绝尘而去。这时候王朔家里,我估计就三万零一百块钱,他为什么说出三万,因为他知道他就这点钱。他当时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后来写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人很难理解呢,就是这个缘故。”
那段时期,他开始读佛教,开始了解物理学和宇宙学。《我的千岁寒》即取材自《六祖坛经》,这毋宁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想从痛苦中挣脱。他在《回忆梁左》的文章里如是写道:“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忘了这一世的事。”
我们熟悉他被媒体所塑造出痞子形象,口无遮拦地骂人,成了他的符号。可是我们知道,真实生活中的他并不如是,至少某一段时间里不是。王朔是有过不少欢欣的日子的,我们在他小说中看到的那诸多叽叽喳喳的热闹,大多是他早年生活的印记。
他说《浮出海面》这篇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吃力也是最满意的,通篇写的是感情生活。他说得如此真诚,让我们愿意相信和前妻一同完成这部作品的日子在他生命中所占有的分量:“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
可他终究还是个很矛盾的人,在女儿六岁的时候,他离了婚。女儿结婚的现场,他也没有到场,陈丹青说:“他扛不住,没有勇气站在这儿。”他的敏感与软弱,和他的锋芒与机敏,并存着。再凶猛的动物,也都有他柔软和温情的一面。
这种对照,让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题目,前半部分的人生是“火焰”,后半部是“海水”。绚丽的时候绚烂之极,可平淡的时候,也终究落得平淡无奇。我有时候会想到《红楼梦》,前面是热热闹闹的喜宴,大伙儿欢聚在一起,那时候的他,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被无数拥趸簇拥着,欢呼着,春风得意的坏蛋。可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筵席终散,后面只剩下了白茫茫一片。
据说王朔在写上古史,无论他再出什么作品,不管怎么样的改变,只要能让他摆脱抑郁与困顿,我觉得都是好的。不必苛责一个人非得在另一个人生阶段去完成与他年轻时候类似的创作,好的写作永远是最私人的,最个体的,是自我解脱与救赎的。
以《我的千岁寒》中的一句话作结:“我再见你,记住,不是青苔,也不是蘑菇,是一片橘子色。”这一片橘子色,我姑且理解成是识得乾坤大后的人,犹怜草木青的那一点温存与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