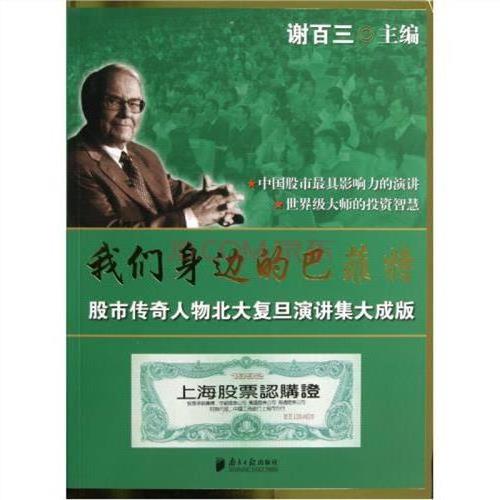樊建川老婆 【知青故事】知青传奇人物:樊建川
樊建川,中国知青中的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
人们这样介绍他:曾下乡、当兵、任教、做官。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从事收藏数十年,其藏品种类繁多,重点为抗战文物和“文革”文物。此两项收藏在国内位居前列,如137件文物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5,他在中国四川安仁镇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其收藏事迹为媒体广泛报道,他的收藏目的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抗战);为了未来,收藏教训(“文革”);为了民族,收藏传统(民俗)。
他的收藏品目前已达数万件,他的收藏事业,名震四方,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目前,他是是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
可见,樊建川先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知青。
中国知青樊建川先生

在他的博物馆幕墙前
在由樊建川口述,作家李晋西记录的自传体作品《大馆奴》一书中,有关于建川先生插队在农村的章节,内容生动、真实,完全没有许多知青题材作品中那种叫苦、叫累、叫屈的东西,娓娓道来,只讲故事。特录部分转发,希望朋友们喜欢。

1975年7月,从山东回宜宾几天后就下乡了。下乡地是宜宾县日成公社五一大队嘴上生产队。生产队距县城有几十里,当时没有公路,我是走路去的。到第二年年底,我当兵离开,我在农村差不多待了一年半。
我一直住在农民李国成家。他有五个孩子,加上他妻子,他父亲,共八口人。当时插队知青都愿单住知青房,自己开伙。为什么我要住在他家里呢?不想做饭,做饭太麻烦了。刚开始做了儿天,还是感觉太恼火。我住的房子是他们家搭的偏棚,我住的这头,最低的一边有一米二,放床那一边高一点,房里还放了一口棺材,是为李国成父亲预备的。
另外一头喂猪,中问虽有竹片糊上黄泥的墙,但猪的气味一直有。我刚到的那天做什么活呢?到田里找黄泥巴补墙,因为偏棚的墙,泥巴都掉了,完全透风。
李国成的父亲李幺老爷,是远近百里的传奇人物,在当地很有名气,很受尊重。传说他会念咒语,比如谁长了一个疮,他指着疮念咒语,会把疮念下去。周围几十里的人如果在钓鱼,看见他就不钓了,因为他会念放生咒。他会画符,在盘里画了后,把水喝了。
李么老爷告诉我,高处来的蛇有来历,神物。低处的呢,无所谓,俗物。有次吃饭,梁上现蛇,他立即闭眼念念有词,依稀听得有“列祖列宗”字音。李幺老爷会补锅,把铁化成铁水补。补锅是他的职业,几十里地都叫他幺补锅。我住在他家里,农民就说,哦,那个知青就住在幺补锅家里。
李幺老爷真正厉害的是武艺高强,名气很大,是武术世家。他还会民间杂技耍狮子、上刀山(刀捆成梯子)等。到了春节他就会表演,光着脚走在刀上。他还有很多徒弟,一起表演,三张桌子架得很高,上边还架个板凳,在板凳上倒立,翻跟头。所以,他就是乡间的一个舞狮者,一个补祸的手艺人,一个巫师,一个兽医----他会骟猪,骟鸡。
我在他们家搭伙,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他们对我特别好,在粮食紧张的时候,自己吃稀饭,让我吃干饭。吃肉的时候,会把肉悄悄藏在我的碗底下,因为家里孩子多,怕我吃不到。我刚下乡干活时,锄头把脚铲了,他们用药给我包扎;割水稻时,我不注意把手指甲割掉了三分之一,也是他们治的;挑担子久了后,肩膀磨破化脓了,也是他们把脓挤出来,给我包扎的。我在他们家得到很多照顾。
知青要经常聚在一起,当时一个生产队有一两个知青,但是一个公社还是有一百多个。聚会时,有宜宾市的同学,有柏溪镇的同学。聚会采取什么办法呢,当时粮食是有限的,就轮转转会,今天到他那儿,明天到你那儿。其他知青都自己煮饭,特别是女知青,觉得农民家脏,吃不好。
轮到我这儿比较恼火,存在吃饭的问题。来七八个人要吃好几斤米,我没法跟房东开口。后来回去跟父亲讲,父亲给了我点钱,转到我这儿时跟房东说好,有八九个朋友要来吃顿饭,除了自己的伙食费,还会多给几块钱。
他们还是做得很好,地里的萝卜、红薯尖没有问题,如果有腊肉,还会切几片腊肉。但他们家还是穷,一般早上晚上吃稀饭加红薯,只有中午一顿是干饭。这还是好的时候,有时连干饭都没有。
菜基本上没有,就自己种的一点西红柿、丝瓜、南瓜之类,绝对不会去买菜来吃,地里种什菜,吃什么菜。一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没有菜的,桌子上就是豆瓣酱----用生产队分的胡豆自己做的豆瓣酱。如果有客人来,比如我的知青朋友来,房东就会下挂面,面里放一点泡菜坛子里的泡菜水,有点花椒生姜味,盐放重一点,拿面来当菜。
当时这都是很待客的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会推豆花。吃豆花算打牙祭了。当时生活状况很差。当知青时,最便宜的纸烟是经济牌,八分钱一包。我基本上抽这种,再后,就是和农民一起裹叶子烟。
回房东家,从左依次是:
李幺老爷、樊建川、建川的妻子
下乡后,我基本不回家,干活再苦也咬着牙干,干得很好。送公粮等体力活,没说的。一般的农活,种红薯、玉米、水稻都会。犁田、耙田、栽秧子、打谷子,包括踩草上树,也没问题。踩草上树需要手艺,中间是个木桩,草围着堆得很高,没有手艺的话就会倒。
还有用耙子挖泥巴糊田埂,要糊得很严实,避免田漏水。这些比较难的农家活都会做。自己的自留地当年产了七十多斤麦子,我做了四五十斤挂面挑回家去,家里非常高兴,算是我对家里最大的贡献,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我还在生产队的面坊做活,做了很长一段时间。麦子出了,做挂面,挑到城里卖给老百姓,给生产队挣点现金,这算生产队的副业。当时没有电,用手在面板上把面和好,一个人踩轮子推动转轮,把面压薄,再把压薄的面切成面条晾起来。我们的工分值很低,好像是一毛二分,干一天活就一毛多钱。还有更低的,几分钱一天的。
当知青有很多艰辛,最恼火的是饥饿。第一年还好,政府按月供应口粮。第二年就惨了,靠挣工分在生产队分配吃伙食,一年能分二百斤谷子,打成米就一百多斤,摊到每个月就十来斤。当然,还能分点麦子、红苕之类的杂粮。当时一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二来劳动强度大,三来缺乏油气,人长年处于饥饿状况,只想吃。
有次栽秧子,眼一黑就昏倒在田头了。社员用板板车(四轮人拉车)把我拉到公社卫生院,医生一看就说,啥子哟,没得病,饿的。开了个证明,让我到隔壁供销社买了二两红糖化水喝,就可以走路了。
有次,队里通知到保管室分油,我拿个瓶子直奔而去,到了才知道是空欢喜,原来是按人头一人分一小匙。农民家里一般有五六口人,还可以凑成一点规模,我的那一匙油倒进瓶里,可能会流不到瓶底而黏附在瓶壁。想明白了这一点,我接过匙子,放进嘴里,使劲吸人,全咽下了。
生产队保管室里会放一年的种子,像胡豆花生呀,会派人睡在里边守,害怕被盗。当时让谁守都不放心,怕会在里边吃,虽然把粪便撒在花生胡豆上,但剥了皮还是可以吃的,吃了把花生胡豆壳埋起来,也不易发现。生产队就叫我去。我在保管室守了大概一个月吧,没有吃过。
攀建川插队时与同学合影
后排最高者是攀建川
比较特殊的活就是到城里买化肥。这算比较轻松的活了,大家结伴到县城代销社去挑,当时很少尿素,更多是黑黑的磷肥,一个人挑大概一百斤。第二个活也比较轻松:卖东西。比如卖面,生产队规定好价格,卖了后把钱交回生产队,再给你算工分。
卖红薯会遇到麻烦,虽然生产队规定好了交多少钱回去,比如八分钱一斤,一百斤交八块钱,但没有人一下把一百斤全买完。买的人会选,把皮弄破,就没有人买了,另外红薯上的泥也会被弄掉,斤数就不够。
刚开始做的时候会亏本,会倒贴几毛钱,后来也懂得怎么卖了。先要卖一毛钱一斤,到后面不好的就降价卖六分钱,反正要不停地算账,要把八块钱卖够。当然多卖了,可以算自己的收人。我最希望的是来一个人全部把红娜买光。
有一次运气特别好,是一个铁路员工,问了多少钱一斤,然后叫我挑着走,记得走了很远。当时从生产队过江到合江门码头,再到菜市场去卖,这次他让我挑了个通城,挑到宜宾城的另一边,最后还上几层楼。但是还是觉得特别好,省了去算账啊,虽然走了很远,挑了一个小时,但都卖了,比较爽,还有时间在城里转转,看看老同学再回生产队。但只有这一次,其他很糟糕,很费劲,也有赚的,就赚几毛钱。
到县城里卖东西,有农民要你帮着代卖一点他自己的,有一次,就被农民算计了。他家的鸡害了鸡瘟,我不知道,问了要卖多少钱,把鸡放在红薯上面挑着往城里走,鸡在路上就死了,变硬了。当时很吓,得赔人家鸡呀。卖红薯都是五六个人一路,他们都给我主持公道,说,都是瘟鸡了,还叫你给他卖,别管他,回去交给他,我们帮你证明,我们还得骂他。
没办法啊,我赔不起啊。后来把鸡给他挑了回去。村民都说,你也不能坑人家樊哥哥嘛,樊哥哥这么老实的。那个农民还狡辩说,我的鸡怎么会是瘟鸡啊,我也不知道啊。最后他拿回去吃了。当时穷,会吃瘟鸡。
生产队特别需要肥料,但化肥特别紧,我们就去挑大便。当时都是早厕,我在县里边有关系,就去给他们联系。一般的厕所是不让淘的,有的要给钱,会有人守着,比如一毛钱一挑,像交通局、林业局的厕所。当然会尽:淘干的,淘稀的就不划算,几十里路,挑干的可以和草灰或掺其他绿肥,就是比较好的肥了。
交通局、林业局的厕所挑过后,他们就求我说,樊哥哥,你去找好的。所谓好的,首选县革委招待所,次选县革委党校。党校不是随时都有,培育干部时才有,粪便特别好,里面不是书记就是大队干部,每天都要吃点肉。
县革委的有油气,焦黄。食肉动物的粪便比食草动物的粪便好。臭,就是标准。队上农民形容粪便好的言语,一是油气好重哟,二是紧凑。他们认为黄色的特别臭的就是最好的,宜宾话叫“黄金杠色!
”就是黄金一样的颜色且是干的。当时生产队对粪便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你挑的粪不好,就会说,你挑的粪不臭。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王云清,是一个大汉,他对粪便特别有研究,是鉴识粪便的专家,也是谈价格的高手,走进别人厕所,瞅一眼,立刻能判断。
王队长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看重我,他们过去挑不到好粪,通过我可以挑到。生产队的人都对我特别好,因为我可以给他们找到好的粪便。有一次挑粪回生产队,我说,哎呀,王队长,这挑我就挑到我的地里去了。他也没说什么,嗯了一下。当时的政策,知青可以在队上的养猪场挑粪。实际上生产队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