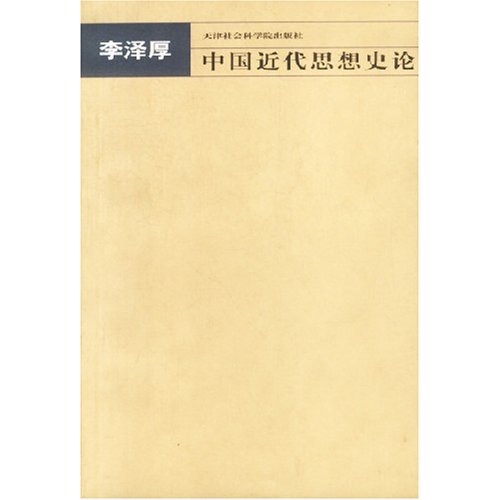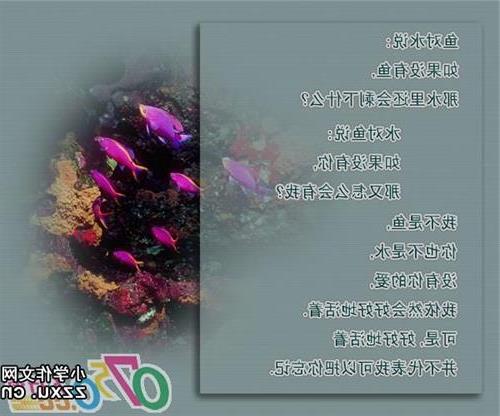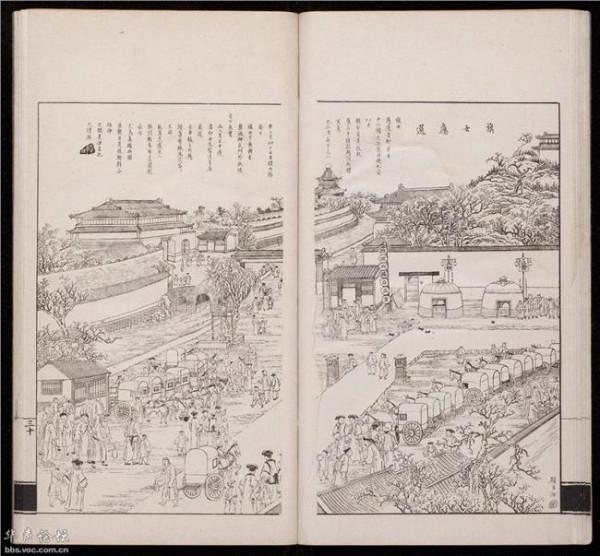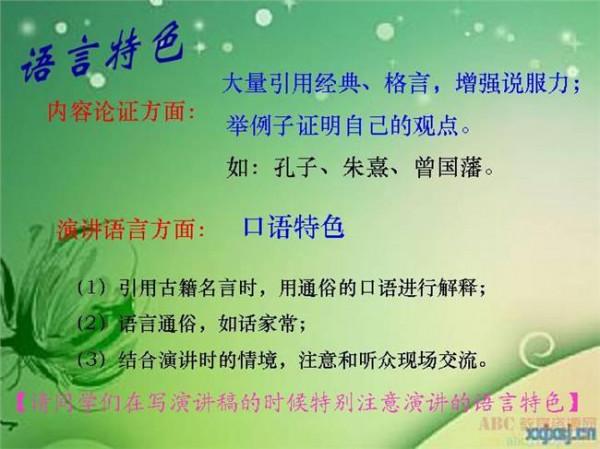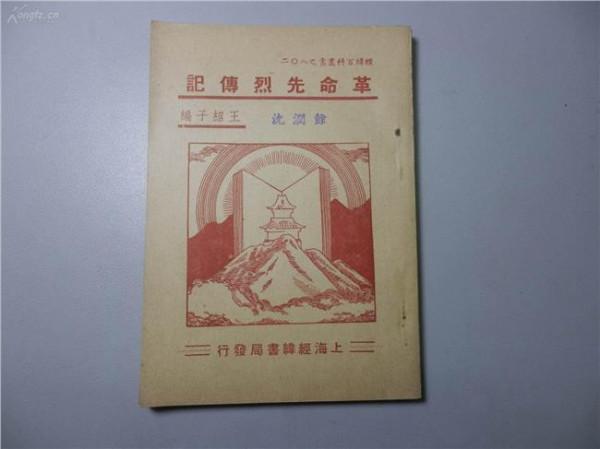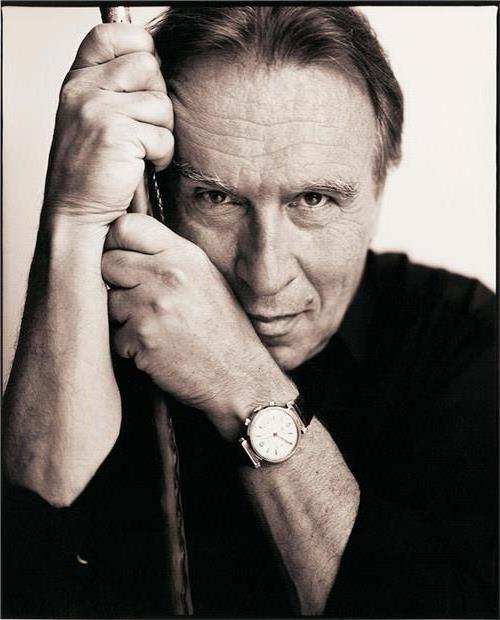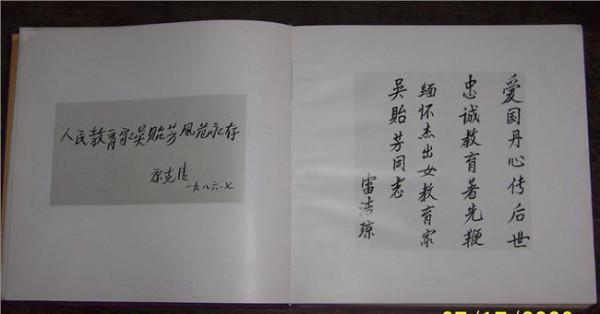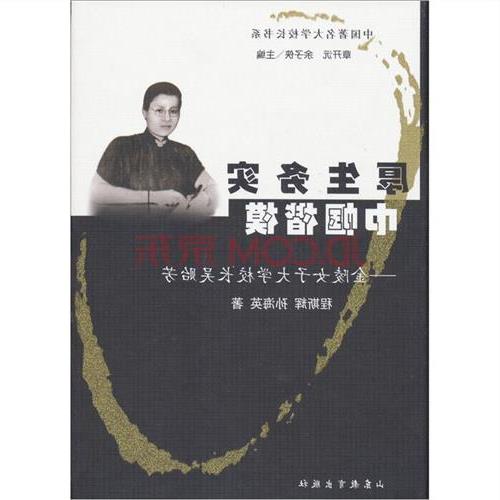李泽厚美学 李泽厚的美学特点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一文里,批评了《新美学》的论点,同时也申述了他的美学特点,即所谓自然美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或依存于)自然的社会性。他在这里是把自然美和社会现象的美并举的,也就是把自然美和社会事物的美区别开来谈的。

因此所谓自然,显然不是如从来一般哲学家和美学家那样把它包括社会和自然界,而是指和社会区别开来的自然界,也就是指自然发生而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事物。然而李泽厚却说:自然物有它的社会性,而自然美即在于它的社会性。那么,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自然物却又有它的社会性,这在我们看来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自然物的社会性,李泽厚说:“自然在人类社会中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着的。自然这时是存在在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它与人类生活已休戚攸关地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所以这时它本身就已大大不同于人类社会产生以前的自然。而已是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它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它已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了。”[1]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自然物本身就已大大不同于人类社会产生以前的自然物了。怎样的大大不同于以前的自然物呢?因为这时自然物是存在于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已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它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已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了。

这种理论实在是非常高妙,我们一时也无法理解,只有先看李泽厚所举的实际例子吧。好在接着上面引文之后李泽厚就说:“这种自然的社会性”,“就正如作为货币的金银,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它们可见可触的物理自然性能以外,而且还具有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确然存在的客观社会性能一样。”
这里他举出“作为货币的金银”和“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的例子,应该是要说明自然物的社会性了。然而实际上不是如此。因为第一,“作为货币的金银”就是金银“作为货币”了。它本质上已是社会物的货币而不是自然物的金银了。
至于“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不是自然物该是更易明白的,世界上难道有什么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机器吗?机器是社会事物原是不成问题吧。第二,它们既是社会事物,虽有自然属性乃至自然形态,但它们的所以为社会事物的本质就是它们的社会性。换句话说,社会性就是它们的本质,就是它们的所以成为社会事物的决定性质。
这样说来,李泽厚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只说明了社会事物的社会性,不能说明自然物的社会性;不仅不能说明自然物的社会性,倒还说明了物的社会性就决定该物本质上成为社会的物而不是自然物了。譬如“作为货币的金银”原是自然物,原具有自然属性,而作为货币或商品就具有了社会性;既具有了社会性,它就在这种社会性的规定之下已是社会物而不是一般自然物了。
即算“作为货币的金银”这时依然是自然形态的金银,但本质上已不是自然物了。于是社会物虽然具有自然属性,但是自然物,就它作为自然物来说,就不能又说它具有社会性。因此李泽厚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不仅不能证明他所谓自然物的社会性的理论,倒是他的理论的否定。
关于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李泽厚又举出了两三个说明的例子。他说:“我们承认自然美的社会性,并不是否认物体的某些自然属性是构成美的必要条件,如高山大海的巨大体积,月亮星星的暗淡光亮,就是构成壮美或优美的必要自然条件,物体的‘均衡对称’也是如此。
但是这些条件本身并不是美,它只有处在一定的人类社会中才能作为美的条件。这就正如作为货币的金银必需有重量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但重量这个自然属性本身并不能构成货币,它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成为货币的条件一样。”
这里他首先举出了“高山大海”和“月亮星星”两个例子,然后又举出了“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例子。所举的例子本应该要能说明自然美如何在于它的社会性,然而又完全不是如此。关于高山大海和月亮星星这种自然物,它们本身究竟怎样存在于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而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又怎样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化”了,也没有一点说明。
试想一想,假如高山大海的巨大体积或月亮星星的暗淡光亮,果然如李泽厚的理论所说,它们本身存在于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具有了社会性质,它们本身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化”了;那么,巨大体积的高山大海,将遨游于这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不免有饮食男女吵架斗殴的事,它们就会是从来神话中的巨人了。
而李先生的理论也就该是一种非常壮美的神话吧。或者美国的月亮的暗淡光亮“人化”了,具有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性质,而中国的月亮的暗淡光高“人化”之后具有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于是这两种社会性质不同的月亮的暗淡光亮就不免矛盾、斗争,就如从来的童话中的精灵一样。
而李先生的理论大概也就只是一种非常优美的童话吧。然而若是作为美学理论,就未免有点近似于“荒唐”了。至于所举“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例子,如上所述,它本质上是社会的物而不是自然物,李泽厚再次举出来也还是不能说明自然物的社会性,事实上也并没有说明金银的自然美如何在于它的社会性。
然而更说明自然物的美,金银倒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因为自然物的金银的美是大家所承认的。金银虽然可以“作为货币”而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说金银的自然美,则不是因为“作为货币”具有了社会性质然后才是美的。
事实上很显然,金银由于它本身的美才成为装饰品的原料以至成为价值体现者的货币,却不是由于它成了装饰品原料乃至货币然后才是美的。这就是说,作为自然物的金银本身是美的,它的美就是它作为装饰品原料乃至货币的先行条件之一,是它具有一种社会性质成为社会事物的先行条件之一,而不是相反的,不是它成为社会事物、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然后作为自然物才是美的。
也就是说,金银的自然美并不在于它的所谓社会性,而是在于它本身,在于它的自然属性。当然,我们说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自然属性,并不就是说自然美等于它的某种自然属性。
这样说来,李泽厚在谈自然美时,只能反复举出“作为货币的金银”来谈它的社会性,却不能举出作为自然物的金银来谈它的美。就是因为金银的自然美显然不在于它的社会性,而在于它的自然属性。这就是说,金银这个例子,不仅不是他的理论的证明,倒又正是他的理论的否定。
李泽厚最后还曾“举一个通俗的国旗的例子把整个问题说明一下”,当然,特别要说明的就是他的美学特点,即所谓自然美的社会性问题。他说:
国旗本身又美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这块贴着黄角星的红布显现了什么“普遍种类属性”、“均衡对称”之类的法则呢?当然不是。一块红布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它的美是在于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这种代表是客观现实。这也就是说,国旗一一这块红布黄星,本身已成了人化的对象,它本身已具有了客观的社会性质、社会意义,它已是中国人民本质力量的现实,正因为这样,它才美。
很显然的,他在这里正是要说明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他提出的所谓“普遍种类属性”、“均衡对称”之类,本意就是为了反对自然美在于自然物本身。我们现在也就他所举的这个“通俗的国旗的例子把整个问题说明一下”吧。
第一,国旗难道是自然物吗?显然不是的。李泽厚自己也说,它是代表了中国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的,因此它本身是具有社会性质和社会意义的。就说那么一块红布、五个黄星,也不是天生自在的而是人造的。李泽厚把这样的国旗的社会性来说明白然物的社会性,这不是把国旗也当成了自然物吗?如果国旗也是自然物,那么李泽厚又认为什么是社会物呢?
其实国旗的具有社会性质,就是它本质上已是社会物而不是自然物了。把本质上是社会的物作为自然物,又反过来把它的社会性质作为自然物的社会性质,由此来论证自然物的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这难道果然是什么科学的论证而不是一种耍魔术的手法吗?
第二,国旗的美难道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不在于它那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吗?恐怕未必是的。因为国旗固然是代表我们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的,也就是这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是代表我们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的,如果代表国家的这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本身不美,那么国旗的美又在哪里呢?
且不说这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正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国旗这一点,即看它还不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时候,它那样的五个黄星的一块红布,难道果然如李泽厚所说,“本身并没有什么美”吗?用不着谈多少高深的理由,只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征集的国旗图样很多(一说达两千余件之多);政协的国旗国徽组从这许多图样中选出它这一幅图样来,固然是由于它那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可以作为国旗代表我们国家,同时也由于它本身就是美的,或者比别的图样是更美的。
这就是说,它在当选之前还不是国旗,如果李泽厚问它要国旗的美,它是没有的;虽然如此,它这样的颜色、形状的一块红布、五个黄星本身就是美的。而它本身的美就是它被选来作为国旗代表我们国家的先行条件之一。如果愿意实事求是的话,这点事实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国旗的美之一助吧。
自然,国旗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本质上是社会的物,国旗的美和它的这样性质有关系;然而如果说它的美不在于这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那么所谓国旗的美不就完全是空洞抽象的吗?
以上两点说明什么呢?这又说明李泽厚所举的国旗的例子,不仅没有证明他所谓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而且相反的,那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在定为国旗之前本身就是美的;定为国旗之后,作为国旗的美也还是和它这样一块红布、五个黄星的颜色、形状自然条件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这个例子又不是他的理论的证明,倒是他的理论的否定。
二 招牌不等于货色
李泽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诩的。甚至把他的论点不说是他的论点,而直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如此的,或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此的。
然而有些事实叫我想到,招牌不等于货色,只看招牌取货不免上当。因此对于李泽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美学,我还是想看看它究竟是什么货色。
李泽厚所宣传的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点,所谓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我们在上面就曾说明,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因为他既把自然和社会区别开来谈,那么自然物和社会事物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物是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
虽然自然物和社会事物并非截然不同或完全无关,甚至一个自然物同时也可以是社会事物,如一块石头是自然物同时也可以是建筑用材。但是既把自然物和社会事物区别开来谈,就不能抹煞这两者的本质的区别。
如果抹煞了这种区别,不仅造成理论的混乱,而且容易颠倒两者的关系,为唯心主义的论点敞开大 李泽厚认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自然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它是存在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这首先就是说,自然物是依存于人的,依存于人的社会关系的。
这不仅是抹煞了自然物和社会事物的区别,而且正是把自然物归人于社会事物,以至于根本否定了自然界的独立存在,否定了自然界。这种理论难道还有什么唯物主义的气息吗?
所谓自然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按李泽厚的进一步说明,是自然物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化”了。自然的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首先就是说,它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存在(也作为实践的对象而存在),于是所谓自然物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化”了,也就是说,自然物本身是人的认识的“异化”,是人的意识的化身,是人的感觉、观念或感情、意志的表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难道不正是唯心主义的滥调吗?
然而李泽厚说,他的这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由于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两句话,以为就可以挂上那块金字招牌,叫人看来“眼花缭乱口难言”了。
李泽厚在论自然物的社会性时,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引来两句话说:“对象的存在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然而马克思这两句话的本来面目和意义究竟是怎样的呢?好在马克思的书已有何思敬同志的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这两句话就在译本的八十八页上。如果一翻该书,首先就可以看到译文的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意义的完全不同。我在这里不想引用何译书上的译文来争文字上的是非,只想说明,由马克思原来的文义,决不可能得出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的论点:所谓自然本身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和以前已大大不同了。它这时已具有了社会性质而“人化”了云云。
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如本节标题所指出,是“私有制和共产主义”。李泽厚所引那两句话的前后文的主要意思是:私有制束缚人的感觉和属性,而共产主义则是人的感觉和属性的解放。马克思说:“私有制把我们弄得那样愚蠢和那样片面,甚至当一个对象被我们持有着,从而作为资本对我们现存着,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着、吃着、饮着,在身上穿戴着、被我们居住着等等,一句话被我们使用着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对象。
”于是对象对于我们就只是“持有的意义”,自然就是单单的有用性.
而人的欲望和享受就只表现其利己的本性。然而,“私有制的扬弃是一切人的感觉和属性的完全的解放;但私有制的扬弃恰恰是因为这些感觉和属性无论在主观上或在客观上都成为人的之故才是解放。如同眼睛的对象成了一个社会的、人的、从人类并为人类发生的对象一样,眼睛就成了人的眼睛。”“欲望或享受就失去其利己的本性,而自然就失去其单单的有用性。”
以上所述马克思文中的主要意思,是要说明他在这里所说的,决不是什么人类社会产生以前或以后的问题,也决不是什么和社会事物区别开来的“自然本身”的问题。他说的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私有制和共产主义”两个大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里所谓人的,就是社会的,也就是人类的,是就共产主义社会“失去其利己的本性”的人而说的。所谓自然则是人的生活活动的一般对象,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主要是社会事物,无论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对象或享受对象,即“从人类并为人类发生的对象”。
特别是在李泽厚所引的话中,原有“在社会中”的字眼,说明所谓对象原是在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显然不是说的自然物本身。然而李泽厚在这里的引文中就把“在社会中”的字眼擅自抹煞,把所谓“对象”说成是社会事物以外的自然物本身。
不难看出,李泽厚在这里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就是把马克思的所谓“自然”和“人的”或“社会的”,都作为他自己的用语那样解释。在马克思,不是把自然和社会区别开来谈的,而是把社会事物包括在自然之中,而且明白地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在李泽厚,原来是把自然和社会区别开来谈的,结果是把自然归人到社会之中,而且明白地说:“自然这时是存在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也就是说自然是社会的一部分了。于是按这种逻辑就必然达到自然界是依存于人的,而没有人就没有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结论。
这样以他的用语的意义去解释马克思的用语,进而以他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的论点,结果就是以他的唯心主义去歪曲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去宣传他的唯心主义。
李泽厚的所以那样引用马克思的那两句话,原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论点,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他所引的那两句话,实际上和美的问题并无什么密切关系。但是就在那两句话的下一段文章里,就有马克思理论事物的美的话,他却偏偏没有引用。
譬如马克思说:“非常操心的穷困的人对最美好的戏剧没有感觉;矿物贩卖者只看到(矿物的)商业的价值,但不看矿物的美丽和特有的本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说这些话的意思,主要是在于说明私有制怎样使人物质生活贫困,同时也使人精神生活贫乏,也就是束缚了人的感觉和属性,所以穷困的人不能感觉戏剧的美,而矿物商人也看不见矿物的美和特性。
马克思在这里的关于矿物的美的话,就和自然美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我们且以矿物这个例子来看自然美是不是如李泽厚所说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吧。这里所说的矿物,是在矿物商人手里的。应该说它已是商品,也就是本质上是社会的物而不是自然物、了。
所以这种矿物已具有了商业价值,已具有了社会性质了。如果按李泽厚的理论,这时矿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商业价值,而商人看到了它的商业价值正能看到它的美。而且只有如商人那样看到了它的商业价值,才能看到它的美。
然而马克思却说,商人虽看到了矿物的商业价值,也就是看到了矿物的社会性,却看不到矿物的美。这就是说,矿物的美和矿物的社会性究竟是两回事,即算这时的矿物已是社会的物,具有了社会性;但是矿物的美并不在于它的社会性。
由此可见,李泽厚的理论是和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完全相反的,李泽厚的引用前一段文中和美的问题并无密切关系的话,而不愿引用后一段文中这种和自然美有关的话,显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按马克思这种话的意思就否定了李泽厚的理论。李泽厚的自诩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如此的论点,原来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的假货色罢了。
三 事实终胜于巧辩
以上两节和另一节《歪曲决不是批评》,都是去年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发表之后写的,也只是针对着《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中他的理论特点的意见。最近看到《新建设》上李泽厚的《论美是生活及其他——兼答蔡仪先生》之后,还想再说几句话。因为李泽厚这次说的大致是老话,我要补在这尾巴上来说的也不免是老话,所以不必多说。
一、在《歪曲决不是批评》里我特意说明:《新美学》认为美有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后两者决定于社会关系或阶级的一般性,自然美则在于自然物本身。而李泽厚原来是、这次依然是笼统地说:“蔡仪的美学观”“漠视和否认了美的社会性质,认为美可以脱离人类社会生活而存在”。这是不是歪曲?是不是依然歪曲?如果李泽厚愿意想一想部分不等于全体,当然能够得到解答。
二、在《歪曲决不是批评》里我特意说明:《新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所谓典型性或美的本质,说的是“事物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的一种统一关系”。这就是说,事物的个别性或一般性都只是它这种统一关系的因素,只是规定它的美的因素,决不是说一般性或个别性就是事物的美。
因此自然事物的个别性或一般性也只是规定它的美的因素,决不是说自然物的个别的或一般的自然属性就是美。而李泽厚原来是、这次依然是说我“把美归结为简单的低级的机械、物理、生理的自然属性或条件,认为客观物体的这种自然属性、条件就是美”。
这是不是歪曲?是不是依然歪曲?如果李泽厚愿意想一想关系的因素并不等于关系,当然能够得到解答。
三、和上述那点相关的还有一点,就是《新美学》认为事物的一般性(如以生物来说,它的生长生殖等生命活动)是规定事物的美的因素或主要条件,事物形体的一般性(如以生物的形体来说是均衡,其中以动物形体来说则是对称)是规定事物形体美的条件。
但这决不是说这种一般性就是美的法则,也决不是说这种一般性是可以离开具体的个别事物或事物的个别性而存在的。然而李泽厚原来是、这次依然是说我“把物体的某些自然属性如体积、形态、生长等等从各种具体的物体中抽象出来,僵化起来。说这就是美的法则”。这是不是歪曲?是不是依然歪曲?如果李泽厚愿意想一想规定条件或主要条件不就是法则,当然能够得到解答。
四、在《歪曲决不是批评》里,我还着重说明:《新美学》的基本论点和黑格尔的美学观点本质上的不同,在于黑格尔认为美是根源于客观现实以外的观念,《新美学》认为美在于客观现实本身;黑格尔认为现实美不是真正的美,《新美学》认为现实美就是真正的美。
而李泽厚原来是、这次依然是说《新美学》的论点相当接近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这是不是歪曲?是不是依然歪曲?如果李泽厚愿意想一想形式不就是实质,当然能够得到解答。
然而李泽厚就是不愿意这么想一想,硬要把部分和全体、关
系的因素和关系、条件和法则等等的区别当作没有这回事,于是
在这次文章中多方巧辩,、想要掩饰他的歪曲,不过事实总是事
实,巧辩也是抹煞不了的。
还应该说明,《新美学》认为社会美在于社会事物本身,同样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本身,而李泽厚主张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新美学》认为美的本质是事物的典型性,自然美是自然事物的个别性显著地表现一般性,而李泽厚主张自然美是自然物本身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或“人化”。
如果李泽厚能实事求是地针对《新美学》的论点进行批评,也能实事求是地针对自己的论点加以论证,我是非常欢迎的。然而李泽厚似乎并不愿意明白《新美学》的论点,只是从《新美学》里断章取义地摘引词句,并加以不适当的引伸,就据以判定是机械唯物主义或相当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而且也似乎不愿意明白自己的论点,只想为那种论点掩饰,就不惜从马克思的书里断章取义地摘引词句,并加以不适当的引伸,就据以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
这就不只是有无“科学的态度”的问题,也不只是是否“大意的误解”的问题,而是更坏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歪曲了(新美学》的论点当然是小事,而且还以他的唯心主义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宣传了他的唯心主义,这是我认为必须指出加以批判的。
1958年6月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1958年,后曾收入文集:《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探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美学论著初编》(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