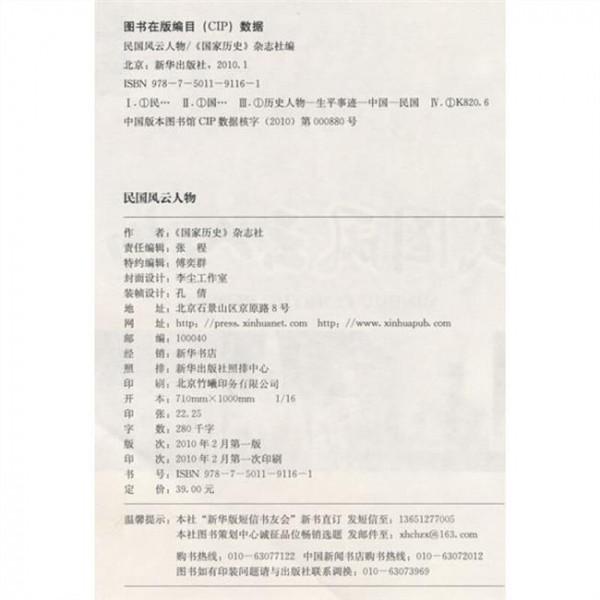叶廷芳先生虽从事 忆朱光潜先生叶廷芳 忆朱光潜先生二三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也就是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月,“兴无灭资”运动普遍展开,经常在某个文化学术领域物色“资产阶级观点”的典型代表,然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他进行批判。记得在美学领域较早被选中的“靶子”是朱光潜先生。
那时总以为朱先生必以一篇系统的检查和认错告终。但不,只见他检讨后依然精神抖擞,顽强应战。他在接受对方某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切实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真与别人论辩。他自知不懂马克思主义,却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决心学习这门新的学问,且为此学习俄语。朱先生的这一特点,当时给予我这个大学生深刻印象,觉得他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想不到这位心仪中的大学者后来竟有机会让我认识,甚至还在同一个单位共事!那是1960年的下学期开头,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根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于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着手扩充该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队伍。
为此他把全系一些较有外国文学专长的老教授都集中在文学教研室,同时从四年级爱好文学的学生中抽调了好几位,包括笔者,作为“新生力量”。朱光潜先生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代表”,但大家都公认他是确有学问的学者。
所以西语系和哲学系(他也兼哲学系教授)就共同委任他一个任务:给两个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一门西方美学史培训课,课堂就设在西语系所在的“民主楼”(这座中式大屋顶的二层楼是原燕京大学的遗产)。
说心里话,这门课我是很感兴趣的,谁料第一课我就出了洋相!原来朱先生正在讲课的时候,窗外的树上传来嘁嘁喳喳的鸟叫声,我朝窗外一看,只见一群欢蹦乱跳的鸟儿玩得正欢,似乎在互相热烈交谈什么。我正津津有味试图辨别出它们交谈的内容,忽听得一声“叶廷芳!
”的叫唤。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只见朱先生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请你站起来!”“你把我刚才讲的复述一遍!”。这下我懵了,什么也答不出来!全班二十几人的目光一起投射过来,我一下成了众目睽睽的聚焦点。我满脸通红,等着朱先生的训斥。但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盯了我一会以后,用手势示意我坐下,继续讲他的课。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学校之所以用拔苗助长的办法让我们提前毕业,“赶鸭子上架”当教师,就是希望我们快快“成长”起来,以便早日把“资产阶级专家”的老教师们替换下来。这一意图当时系里掌实权的领导曾经明确地向我们透露过,老教师们心里也是明白的,故他们对青年教师一般都客客气气。
然而朱光潜先生通过给我这个“下马威”,分明表示他不买这个账!我把朱先生这种表里如一的严格态度跟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争鸣精神联系起来,觉得他在这里表现的又是一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我又看到了他的一种骨气,因而心中更加敬佩他了!于是我决定登门拜访他一次,为道歉,也为求教。
开门的正是朱先生本人。出乎我的意料,他热情招呼我往屋里坐。在他楼上的书房坐定后我马上说:“朱先生,今天主要是来向您负荆请罪的……”“哦,没有那么严重!那天上课你走神了,我提醒你一下而已。”停了一下,他接着说:“现在你自己也是教员了,我想你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也不会当作看不见的吧?”我连忙说:“是,是,维护课堂纪律是每个教员的责任。
”也许他看见我脸红了,赶紧把话题岔开:“最近你在忙什么?”“在写讲稿,关于海涅的。
”我说。“你备课时除了德文,还看别的语种的资料吗?”“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语,大学第二外语领导要求我学俄语,可学了俄语却把英语忘了!现在这两门外语用起来都有困难。”他像在思索什么。
这时我立刻想起了朱先生掌握多种外语,正好乘此机会向他讨教一下:他有什么诀窍没有。他听了我的提问后说:“那时我们有机会去国外学习,在外语环境里效果自然不一样。再说西方一些大的语种都是拼音文字,字母大同小异,字义也有不少相近甚至相同。
从学习方法上说,外语这东西最讲坚持,切忌中断,不能抓了这个,放了那个;凡抓到的就要死死不放。”我又问:“在您学过的几门外语中,您觉得哪一门最难?”他沉吟片刻,说:“德语最笨。”见我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就没有继续回答为什么了。
然而“文革”后,恰恰是朱先生最弱的这一门外语,使他完成了一项国家的重点翻译工程,即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第一卷已于1959年出版),这也是他个人翻译事业中成就最大的组成部分(其他还包括莱辛的《拉奥孔》和歌德的《谈话录》等),一如杨绛,她也是利用几门外语中的弱项西班牙语解开了她钟情于欧洲巴洛克文学的最大心结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
二者都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年代里、通过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比较起来,朱先生还要不容易。因为“文革”初期,朱先生在学校里受红卫兵的冲击比杨先生在我们单位受到的冲击要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学》的翻译任务如同《西方美学史》的编写任务一样,都是“文革”前周扬交代的国家任务。
在“文革”的中期和后期,周扬已经作为文化界“最大的走资派”投入监牢了,你还在执行他的“黑线”,岂不是真正的“死不悔改”吗?但朱先生显然没有考虑这些。此刻我的记忆闪回到“文革”中、后期在北大两次与朱先生的偶遇,两次都是未名湖西边尽头的小径上,其间相隔两三年。
两次都见这个瘦弱的老人右手提着一个蓝色的布袋子(里面显然装了几本书),佝偻着背,眼睛只看着路,迈着沉稳的步子。我喊了一声“朱先生!
”他朝我一笑,我问:“您去哪里?”他手一指,淡淡地说:“系里!”后来知道,他在被罚扫厕所那些年,民主楼入口左侧的那一小间原来勤杂人员用来休息和放工具的地方,成了他劳动之余的去处。由于他的住宅有一部分被分给别人住了,朱先生白天只得“蜗居”在这里,忙里偷闲进行他的《美学》第二、三部的翻译!
第二次去朱先生府上拜访,已是“文革”之后了。那时他已经从燕东园搬到了燕南园。经过了沧桑,很想去看看这位身体瘦弱而精神坚韧的老人。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朱先生情绪很好,他亲自给我沏了一杯茶。寒暄以后,我说:“朱先生,我实在佩服您!
您挺过了"文革"的批斗和摧残,还完成了《美学》的翻译。”他说:“批斗嘛,嘿嘿,”他轻轻地笑了一下,好像觉得很滑稽,但突然语气一转:“但也不能说人家都错,因为我不能说我没有缺点。
但我也有一个信念:我是愿意学习的,我是尊重科学的。至于翻译,这要归结为我珍惜时间。谁都会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生命是靠时间来维持的,没有时间,你做不出成绩,也就体现不出生命的价值。说到黑格尔《美学》的翻译,我只认定两点:第一,这是一部世界经典名著;第二,这是周扬同志交代的任务,因而是国家的任务。
你说他有这个那个错误,我管不着,我只敢说,他交我这个任务是没有错的。”“我以前听您说过,您只学过一年德文,却把这部很有难度的大部头拿下来了!
这太了不起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我的英文、法文基础还比较好,也参考了俄文。在这些语言的帮助下,我把德语中有些难懂的地方弄懂了。因此可以说,我通过《美学》的翻译等于把德语重新学了一遍。”
接着这一话题,我又向朱先生讨教一个问题: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精读”和“泛读”应以哪个为主?朱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以精读为主!”他说:“与其一年读四本书,不如一年读一本书!”他认为,在你的外语阅读能力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扎扎实实读几本书,泛读起来就会囫囵吞枣,理解错了往往都不知道,知道了也不知错在哪里。朱先生还认为:“精读的最好方法是翻译。”
我又向朱先生请教一些在治学方面的经验方法。“经验、方法这类东西是不好说的,因人而异啊,”他说。但停了片刻后还是说:“就我来说,珍惜时间最要紧。在这个前提下,多读、多写、多思考。同时,只要以为对的,就坚持;发现错了,就修正;不懂的,就学。至于别人怎么看,让时间去做结论。做学问,就是不能人云亦云。”
现在,每当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0卷,未名湖畔那位踽踽独行的枯瘦老人立即映入我的脑海,而卡夫卡那句箴言也同时从我的记忆中跃出:人是不可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精神内核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