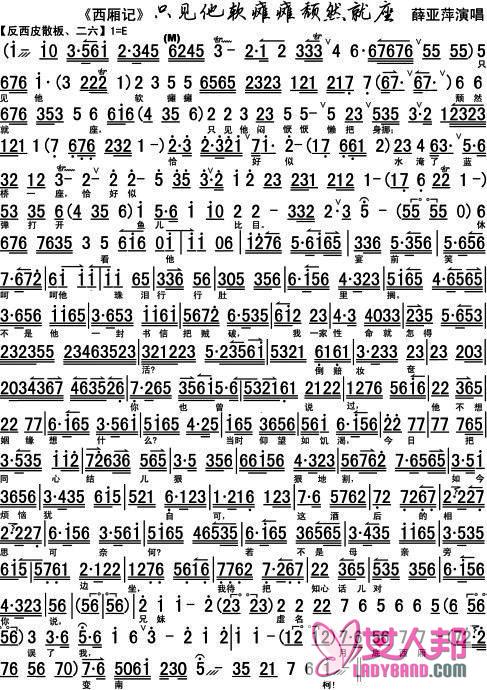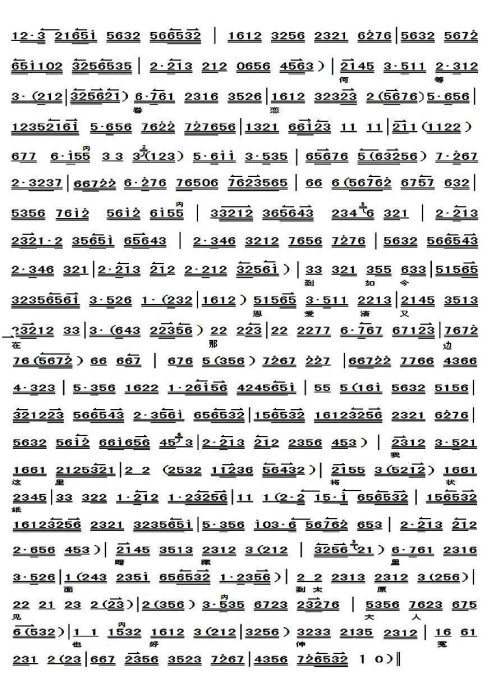统派张亚中 张亚中:“一中三宪”探索两岸统合大道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在《中国评论》月刊八月号发表专文《一中三宪:重读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者认为:“两岸目前的法理现状为‘一中两宪’,当两岸签署和平基础协定,包括双方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两岸为宪法上的平等关系时,其实就已经进入‘一中三宪’,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机制。
”而“两岸关系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大事,对此重大问题,我们有必要解放思想,开大门、找大路。”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用知识寻找共识 用情怀探索交集
今天,我想重读邓小平,重新认识一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要,也试试看能否与时俱进地为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走向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在台湾研究会许世铨副会长的促成下,两岸统合学会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及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六月中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由两岸重要学术菁英参与、极为有深度的高水准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两岸和平协议”与“两岸统合路径”。
这也是两岸学术界第一次严肃地就两岸定位与未来的和平协议进行深入学术性的讨论,除了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孙哲主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以外,其他参与者均是法学专家。为了与北京学者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两岸统合学会特别以自上年十月起在《中国评论》由张亚中、黄光国、谢大宁、杨开煌、谢明辉等教授陆续所发表的专文,以及包括沈卫平、许世铨、俞新天、李家泉、周志怀、黄嘉树、才家瑞、张茜红、陆钢、牛震在内的大陆与海外学者的重要文章作为讨论基础。
王振民院长特别将他在《环球法律评论》所撰写的《“一国两制”下国家统一观念的新变化》一文提供与会者参考。而笔者在今年三月底出席澳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学术研讨会时,也拜读了饶戈平教授所发表的《一国两制方针与宪法在港澳地区的适用问题》一文。这两位法学专家对于“一国两制”的诠释非常清晰,应该具有非常的官方代表性,也提供了我们一个讨论的基础。
与会者均瞭解到,如何面对“中华民国”的身分与地位,是两岸定位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处理,两岸几乎无解。在两岸的定位上,我长期所主张的是“整个中国内部的两个宪政秩序主体”。多年的社会运动伙伴,也是所敬仰的黄光国教授,将其简化补充为“一中两宪”,以求清晰明朗。
(请参阅《中国评论》2009年5月号《以“一中两宪”跨越和平协议的门槛》一文)。与会的台湾学者,也认为宪法层次关系是两岸关系定位的必要性质,台北方面很难在这方面让步,也同意“一个中国”(即“整个中国”)是北京不可能让步的底线,而也是两岸关系得以正常化与和平发展的基础。
与会者均同意,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有知识,也要有情怀。知识帮助我们探寻共识,情怀让我们以关怀、体谅、包容的态度去思考两岸与中华民族应有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情境下,一场严肃而有深度的会议,却是充满温馨与启发。与参加其他的国际会议不同,我们纵有看法的差异,但是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外人”,而是在讨论“自己人”的难题。
两岸问题的核心症结已逐渐浮现,“两制”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一国”。返回台北的途中,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尝试为两岸的核心争议找到共同的诠释?一个看似冰火不容的问题,是否可以经由有我们的知识与情怀,找出解答的线头?
探索:“一国两制”是否限定在中共宪法下的两制
饶戈平教授在论及港澳的基本法与中共的宪法关系时称,“把基本法称作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容易导致宪法和基本法位阶的混淆,在客观上贬低或否定宪法的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和职能,因此,‘小宪法’之说不可取”。饶教授清楚地指出,《基本法》法源的基础在于中共1982年《宪法》所增设的第31条,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按此规定,宪法允许在特别行政区实行另由法律规定的制度,即可以不必是中国大陆通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能够从宪法上找到根据来保留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饶教授也特别提到,1982年《宪法》之所以增设体现与包容“一国两制”方针的第31条,是为了处理好一般和特殊、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这种个别的例外是宪法所允许的,不构成对宪法的对立。以第31条来体现一国两制方针,恰恰是宪法本身的一种慎重安排,构成宪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饶教授很清楚地说明了,北京与港澳的关系是《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虽然《宪法》给予了《基本法》宽容的空间,但是《基本法》的源头是《宪法》。或许可以替饶教授再狗尾续貂地补充一句:即《基本法》位阶低于《宪法》,“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并没有、也不可以违反“一中一宪”原则,而“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振民教授也清楚地处理了“一国两制”的时代意义。在王教授的大作中,首先界定“一国两制”是一种新的统一观,它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摆脱掉“武力统一、一国一制”的制约,“不再由僵化的观念来决定国家统一,而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在互相尊重对方的前提之下谋求国家的统一”,“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统一的标准及实现国家统一的成本和代价”。
王振民教授提到“如果采取‘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就能保证不让台湾同胞付出任何成本和代价,台湾不受任何伤害,不仅可以余留目前已有的一切成果,包括民主成果,还可以从统一中得到更大更多的好处和便利”。不过,王教授也在结论部分说,“‘统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尽管古今中外的认识不一样,但还是有一些最重要的共同标准,例如政治主权的统一和宪法上的统一”。
值得敬佩的是,王振民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基础,即“如果统一是必然的,那么能够维持现状的统一当然就是最好的统一方式。至于是否叫做‘一国两制’并非问题的关键”。
综观这两位深具代表性的法学先进,在看待“一国两制”内涵时,共同强调“一国”内部的“主权统一”,以及“两制”必须服膺于“一宪”。至于其他的内容均可以谈。换句话说,他们的文章揭露出了根本的问题,也显现出问题可以解决的曙光。
问题在于,两岸如何看待“一个中国”?这“一个中国”到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或是两者加起来的“中国”,即本人所称的“整个中国”?“一宪”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国统一后的宪法?
饶戈平教授所引证的中共《宪法》高于港澳《基本法》,是否同样也必须引用至未来在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即中共《宪法》高于台湾的《宪法》或《基本法》?或是依据王振民教授所说的“维持现状的统一当然就是最好的统一方式”,那么这种最好的方式,是否当然可以包括维持两岸现有的宪法?亦即统一后的中国,是否应该不只是尊重双方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包括“尊重双方现有的宪政秩序”?
简单地说,落实在港澳的“两制”是中共宪法下的两制,那么,应用在两岸的“两制”是否也是中共宪法下的两制,或者是两种宪法下的两制?就本人长期在台湾的生活与观察,如果未来适用在两岸的“一国两制”,“一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制”是指中共宪法下的“两制”,那么,除非兵临城下,或台湾经济已经残破,台湾任何一个政党的菁英可能均无法接受。
近年来,“一个中国”与“一国两制”不断地在台湾被妖魔化而得以收效,其原因也在此。
两岸关系是一个有机体,有其不变的常数,也有随着时空而变动的新情况,在重新思索两岸定位与展望未来时,我觉得,有必要重读邓小平,尝试从他的思路中找寻一些启发。
思考:邓小平是从民族和平统一角度看两岸
邓小平曾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一直在想,找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好好瞭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在死胡同里找个出路”。在这样宽广的思想下,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
在港澳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结果。在回归以前,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均暂归英国与葡萄牙。两地没有本身的宪法,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中央政府,因此,“一国”的定义非常清楚,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从原来从属于殖民国政府,换成从属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本质没有改变,可是却取得了北京巨大的包容,即容许港澳有自己的制度,实行高度的自治。简单地说,港澳的地位不是没有变,而是比以往提升了。
邓小平思想的最终目标,也是他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工具也是安排,它的工具性目的为:一方面做为一种号召,在统一前减少人民对统一后制度是否会改变的疑虑;另一方面做为一项政策安排,做为在统一后减少统一代价而实践的一种制度,让人民不改变现状地继续平稳生活。
目标与原则确定后,北京对于统一后“一国两制”的应有内涵也在摸索。这个原本为台湾所设计、做为统一政治诉求的主张突然在港澳落实,北京也在适应。正如同王振民教授在研讨会时所说的,1997年收回的只是香港的土地,而不是全部的香港人民。
当时香港居民有一半以上是持英国的证件,这是国际法上难有的特例,但是北京不以为意,依然将其视为是“一国两制”可允许的独特之处,而顺利让“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这个简单的故事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只要目标与原则正确,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也好妥协,给香港方便,其实也是给北京方便。
台北毕竟不同于港澳。台北延续着在中国大陆南京时的法统,它不是殖民地政府,也从来就不是个地方政府。在面对如何适用“一国两制”时,北京的菁英或许也可以与我一样,重读邓小平,与时俱进地诠释与理解其思想精神。
如果我们同意,如何促使“和平统一”才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一国两制”只是为“和平统一”而服务的一项政策设计;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认识邓小平,不再把“一国两制”当做一个定型的方式,而是一项为减少统一代价的政策。那么,在思考两岸问题时,不要被“一国两制”现有的框架所限制住了,而应该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如此我们的思路将可更为宽广。
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是因为他看到了“两制”之间有着暂时难以跨越的鸿沟,必须用时间解决,他有耐心与自信地等待。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意涵着两岸不应该永远地分裂。从邓小平的交集中,可以看出他广阔的心胸与格局,他是从如何促使民族和平统一的角度看两岸,只是在那个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两岸争正统的年代,邓小平很自然地,也必须地将“一国”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在一个和解的年代,邓小平应该会站在民族和平统一的角度来处理两岸的争议,而不会多着墨于哪一个政权是正统。
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他看到今日两岸的发展与欧洲统合的进程,我深信邓小平会告诉世人:我主张的“一国两制”,“一国”是指中国的主权不可分割,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中国人民;“两制”是指在统一后,两岸可以各有其自己的制度,彼此尊重;“一国两制”的精神在于为“和平统一”而服务,至于方式,不必拘泥,只要是和平就好。
他会在现在的“一中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外再加一句,“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人民,为两岸全体人民所共有与共用”。这四句话不是站在狭隘的本位主义,而是宽广的民族主义立场。我们不妨就在这新四句的基础上重读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基础:“一中两宪”是两岸定位的法理现状
我完全同意王振民教授的看法,“维持现状的统一当然就是最好的统一方式”,我相信这也是他深刻认识邓小平思想所得到的心得。“认识现状”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学者必有的态度,即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去讨论问题。与自然学科不同,社会学科不可能在真空的理想下处理争议,而应该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它或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是它却真实地存在。
如何认真地面对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基于“维持现状的统一当然就是最好的统一方式”这个看法,我们就必须来看看两岸的现状是什么?
现状一:两岸各在其领域进行宪政式的治理。两岸自1949年起处于分治的状态,各依据其宪法在其领域内行使完整的管辖权。事实上,1949年以后,两岸的政府都没有在对方的领域,对对方的人民行使过管辖权。一直到今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