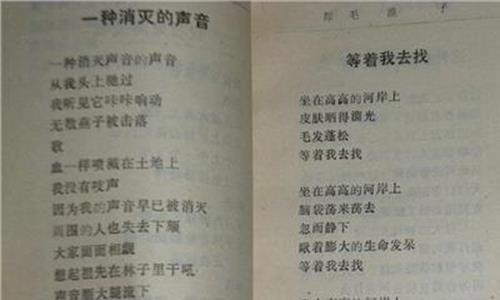刘半农子女 刘半农的摄影生涯
公众视野里的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加入过民国年间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团体———光社,主编过中国最早的摄影年鉴《光社年鉴》,甚至还写过一本摄影理论专著《半农谈影》。

本文介绍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刘半农。
刘半农的摄影情结
在北京大学员工中,刘半农摄影早已出了名。早在常州府中学求学时期,刘半农就喜爱上摄影。那是1909年前后,清朝还没有灭亡,由于江苏是洋务运动的发祥地,历史上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和火柴厂都在江苏,无论小学或中学都有自然科学教育的传统,那时刘半农买了一个小镜箱,玩弄过一两个暑假。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任革命军文书,1912年任《时事新报》、中华书局编辑,写过旧体小说,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刘半农到北大后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文章、诗歌也发表不少,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在学界表现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学府中,像他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当上大学教授很难服人。一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对刘半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留学的资格。1923年秋天,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时因为失眠严重,又买了一个小照相机随便玩,以松弛心思。
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刘半农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影友的期望中,1927年刘半农加入光社。对于摄影的情结,刘半农在文章中写道:
我学摄影,可以分作两期:第一期在十七八岁时,买了一个小镜箱,玩弄过一两个暑假。这一期的事现在已经很模糊,只两年前所做小诗中有“暗红光中的蜜吻”一句,算把当时的影子补记了一点。第二期起于1923年秋季,那时在巴黎,因为不眠症闹得很厉害,又买了一个小镜箱随便玩玩;此后每有什么摄影展览会,都随便看看;有关于摄影的书报,也随便买来翻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因为始终只是随便而没有用过苦功,所以始终还在初学期中,没有什么惬意的作品。
在留学期间,刘半农经常以他的三个孩子为主要拍摄对象,在临时布置的强烈灯光下为他们照相。照完相后,他就换上红灯泡,请孩子们和夫人帮他一起冲洗底片。在业余时间,他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进行研究,每当巴黎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他都赶去参观;看到有关摄影的书报,他也时常翻阅。
1925年9月回北京大学执教以后,对摄影的兴趣更浓了。据刘半农女儿刘小蕙回忆,她常作为父亲“拍摄室外景色的助手,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去颐和园观荷,还是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去北海赏雪,我常常为他背摄影箱和三脚架”。有一年冬天,女儿刘小蕙刚放学回家,刘半农就带着她去北海取景照相。他不辞辛苦地接连一张又一张地拍摄雪景,直到太阳下山以后,他们才踏着积雪回到暖和的家里。
刘半农之子刘育伦对父亲自己做照相机一事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教我们摄影了。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给我们做过一个照相机。那个照相机不像现在的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也不是玻璃的,而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来成像。照相机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地就睡觉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捣鼓。那种照相机当然是十分简陋的,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阮府胡同,他和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照相机去到院子里。对着静止的事物,打开快门,过个二三十分钟关上快门,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时候胶片也不像现在的胶卷,是一张一张往外抽的,我也说不大清楚。后来在照相馆里还用这种照相机。
2000年上半年,刘育伦电话告知江阴市博物馆馆长唐汉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社会名流写给父亲刘半农的书信被发现存于人民大学。据刘育伦回忆,最初这些信是由他收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育伦家从北京迁至东北,于是把书信存于岳母家中。
但是“文革”期间,其岳母遭到抄家,书信被搁置于北京市某派出所。他推测,可能是派出所交到人民大学统战部的。在刘半农子女的请求下,中国人民大学同意将这批史料交给江阴市刘氏兄弟纪念馆保管。
在徐悲鸿写给刘半农的5封信中,主要是想委托半农先生将其画拍成照片,参加德国柏林某著名杂志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这些书信有的只是一些留言纸。原因大约是刘半农在北大时,平时有课才会到学校,因而即便在同一学院教书的朋友,平时也很少见面,于是用留言互相交流。可证明刘半农当时的摄影特长在北京大学同事中已经有了名气。
艺术教育家王森然先生评价说:“先生生平勇于任事,所见皆足珍贵,其美术摄影中诗意之浓,为一般摄影家所不及”。正是出于刘半农“勇于任事”的性格,在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摄影团体———光社发展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担起了光社领军者的重担,直到光社的烛光熄灭。
编辑《光社年鉴》
加入光社后,刘半农参加了光社的第四、第五次作品展览。第七次展览他有25幅作品参展,1932年的影展有26幅作品参展。刘半农很快就成为北京摄影界的活跃分子,在摄影圈中颇负盛名。光社也因刘半农的学术地位而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刘半农加入光社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筹划以年鉴的形式编辑出版社员的摄影作品集。1927年、1928年的两集年鉴都是由刘半农亲自编辑,同时主笔撰写序言。自古以来国学著作,有通史、有通鉴,唯这“年鉴出自西方”。光社年鉴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摄影年鉴。
《光社年鉴》第一集,是光社1927年第四次公开展览的社员作品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北京光社第四次影展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收入当年的年鉴。16开本铜版精印1000册,年鉴中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撰写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三篇文章。三位文章作者分别就自己的观点陈述了办社宗旨和光社历史,内容要点有所不同。
1928年第五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光社年鉴》第二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也印行1000册。第二集比1928年出版的第一集,在内容上又有所扩展,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两篇长篇讨论摄影技艺的论文。
一篇是社员王琴希的《摄影用干片速度之变迁及其与显影液关系之研究》,另一篇是刘半农《没光棚的人像摄影(半农谈影之余)》。似乎还在体现光社“研究”的宗旨。必须附带说明,出版第二集年鉴的时候,北京已经改成了“北平特别市”,如此情况前后两集年鉴的名字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光社年鉴》选刊的作品,完全出自光社社员之手。编印也是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1912年,刘半农中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谋求职业。经过朋友介绍,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当编辑,所以编辑出版工作由他担当最为得心应手。
书的扉页上,署有刘半农的大名和头衔,以他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也给年鉴增色不少。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摄影艺术年鉴。1929年第二集出版之后,光社的活动也就逐渐减少,社员也有不少离开北平,所以《光社年鉴》前后只出版了两集。
两集《光社年鉴》的销售,颇值得一提。第一集出版后,当年就卖出800余册。严格地说,光社成员大多数是薪俸阶层,当年教授的薪水虽然比底层工薪者高出百倍,但在北京要租住公寓、养家购书、往来应酬等开销,清贫终为本色,与后来上海“华社”不能相比。上海华社成员中有一些富裕的商界大佬,如经营化学染料的商人张珍侯、《时报》发行人黄伯惠等,对华社都有资金支持。
《光社年鉴》照例刊登广告外,在发行销售上,可以看出他们经营有道,编者声明:“每集限印1000部,卖完不再添印,定价视存书之多少为标准,存书愈少,则定价愈昂。”每册均有编号,前200本非卖,供社员用。如此下来,第一集的销售,最后还小有赢利,还提高了年鉴本身的收藏价值。
其实他们是学习了书商的销售办法和现代市场原理。这两本年鉴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随着年代的推移,它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其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摄影艺术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北京有位热衷收藏古旧摄影文献的先生,叫赵俊毅,他不仅收藏有全套《光社年鉴》,并且还注重在民国旧报刊中寻找摄影史料。不久前他告诉我:在1927年11月27日《世界画报》第112期刊载了张学良预订《北平光社年鉴》的亲笔信。
信是写给北京真光摄影社的,称“内寄现洋票两圆,将光社年鉴请分神代订一本”,信是张学良从保定行辕发给北京真光摄影社老板的,也可以推断,这一举动也许是经过策划的营销手段,因为张学良不仅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些北方摄影家,如张印泉、冯武樾等人,还给《北洋画报》等一些娱乐报刊以资金支持。有多种文献材料足以证明《光社年鉴》的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光社年鉴》的社员作品均以姓氏笔画排列,不分尊卑幼长,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西方民主思想和艺术上的平等精神。《光社年鉴》的出版,为中国摄影文化保存了发展初期的历史面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写作《半农谈影》
刘半农还是一位摄影评论家与写作家,他于1927年写成一万余字的有关摄影的长篇杂文《半农谈影》。
《半农谈影》是刘半农论述摄影艺术的文章,作为作者亲身从事摄影艺术创作的体验笔记,全书14124字,用白话文写成,深入浅出,力求给摄影新人以艺术本质上的正确认知和指导。艺术教育家王森然先生评价刘半农艺术成就时指出:“先生因好美术,故极嗜摄影,曾组织光社,每年举行展览及出版摄影年鉴,内载先生之作品颇多,并根据其经验,著《半农谈影》一书,在沪开明书店出版,为我国研究美术摄影之唯一名著。”
然而,该书的出版却不逢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刘半农在出版界有个很好的朋友,叫李小峰,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参加新潮社任干事,参与过学生刊物《新潮》月刊的出版,负责校对、发行等杂事。刊物停止后,他仍继续把积压下来的旧刊物摆摊卖,后来在鲁迅支持下,与大哥李志云、夫人蔡漱六及孙伏园集资在北京创立了北新书局。
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了《语丝》周刊,经常为这本杂志供稿的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等社会文化名流,李小峰负责印刷发行。
1927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书局,李小峰逃到上海。
是年9月底,刘半农刚刚写就《半农谈影》的序言,因北新书局被北京奉系军阀政府查封,刘半农为避文祸与周作人躲进北京菜厂胡同日本友人多田少佐家中大约一周时间。事后刘半农自嘲那几天的生活是与周作人“寝、食、相对枯坐,低头共砚写文而已”。
由于李小峰的出走改变了原来的出版计划,《半农谈影》最初一版只得以一个虚构的出版人———“北京真光摄影社”名义自费印刷,于当年10月出版,在北京真光摄影社寄售。真光摄影社地址在北京西长安街路北,大抵今天靠近电报大楼的位置。
离北京大学不算太远,北大师生洗印照片经常光顾于此。刘半农无奈之下以真光摄影社的名义“出版”并代卖“谈影”。直到1928年夏,刘半农去上海后,见到了李小峰。李小峰在万云楼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沈尹默、林语堂等人共宴欢叙,之后才把书稿直接交给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
1930年4月再印刷第三版。《半农谈影》初版73年以后,中国摄影出版社于2000年10月重新排印出版了第四版,特印1000册以致纪念。
中国20世纪早期出版的摄影书寥寥无几,而且大都是介绍摄影技术一类的书籍,而像《半农谈影》这样全面而又通俗地阐述摄影艺术创作原理的书,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视野,它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摄影艺术”的评论作品,作者以他特有的诙谐语言,对轻视摄影的偏见,进行了笔墨上的回应。
文内还叙述了他对摄影的看法和一些美术摄影的基本法则,算是对刚刚入门的摄影爱好者的知识普及,他文中讲解的极其浅显摄影构图方法对后来中国的艺术摄影确实有着一定的影响。
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摄影已经进入了数字影像时代,人们回头品读,仍觉有味。的确,刘半农加入了光社后,一些摄影观念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摄影与摄影发源地法国摄影之间的差别,他以中西方不同的视角,即兴完成了这本摄影理论著作。
《半农谈影》假借批驳了钱玄同“凡爱好摄影者必是低能儿”,这种当时在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论调展开叙述,自然引人入胜。其实,刘半农与钱玄同是再好不过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同事,还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了《新青年》杂志,后来迁到北京,钱玄同、刘半农都积极参与,撰写文章。
《半农谈影》反驳了“照相总比不上图画”的观点。批评了当时的照相馆“把照相当做一件死东西,无论是谁的‘脸谱’到了他们手里,男的必定肥头胖耳,女的必定粉妆玉琢——扬州剃头匠与苏州梳头娘姨的手艺,给他们一箍脑儿包承去了。
”指出,这是为了迎合顾客的心理,是职业的需要,然后亮出刘半农自己的观点:照相可以分为写真和写意两大类,如果加上照相馆,则是三大类。他说:“我们承认写真照相有极大的用处,而且承认这是照相的正用。
但我们这些傻小子,偏要把正用的东西借作歪用———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美’来———因此不得不于正路之外,别辟一路。”是什么样的路子呢?就是“写意”照相。他说:“写意,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随时随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来,必须有所寄藉。被寄藉的东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藉上去之后,就变做了活的。”这种“写意”照相,就是艺术摄影,或称美术摄影。
为了说明问题,他列举了两个有名的例子:“譬如同是一座正阳门,若用写真的方法去写,写了一百张还是死板板的一座正阳门;若用写意的方法去写,则十人写而十人异:有的可以写得雄伟,有的可以写得清劲,有的写得热,有的写得冷———我们看到了这种的照相,往往不去管他照的是什么东西,却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去领略作者的意境。
换言之,我们所得到的,是作者给予我们的怎样的一个印象,而不是包造正阳门的工程师打给我们的一个样。”另一个例子是:“譬如‘云淡风轻近午天’是个印象;你若说:‘云作灰白色,不甚绵密;风力每秒钟二公尺,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五分’,这就是一篇死账,还有什么意趣呢?”这就是说,单纯的“写真”“复写”,是死的,而“写意”“非复写”则是活的,有情趣,才是艺术。
必须指出,刘半农所说的“意境”,多半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立意和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审美感受,而并非专指艺术作品中所包蕴的艺术境界。所以在创作中,他还强调“意境写得出写不出,以及写得好与不好”的技术技巧和艺术修养。
《半农谈影》关于摄影创造的意境议论,有具体的内涵。联系到当时摄影科技水平有限,摄影家掌控作品的表现力的能力还很低,当时人们一般还认为摄影只能复写生活的情况,刘半农提出摄影艺术要表现作者的意境,无疑是比当时国内仅仅掌握照相技术的摄影爱好者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中国,这一步使摄影从机械模写的时代进入艺术创造的时代。刘半农的观点,得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摄影家的赞同和支持,在艺术观念上起到了警示作用。后来,包括郎静山在内的很多中国摄影家都坚信不疑地放弃了“写实”,唯美与“写意”之风在中国摄影艺术界大行其道,几乎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摄影的主流趋势。
(本文摘编自《光社纪事》(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作者为中国摄影出版社编审,摄影史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