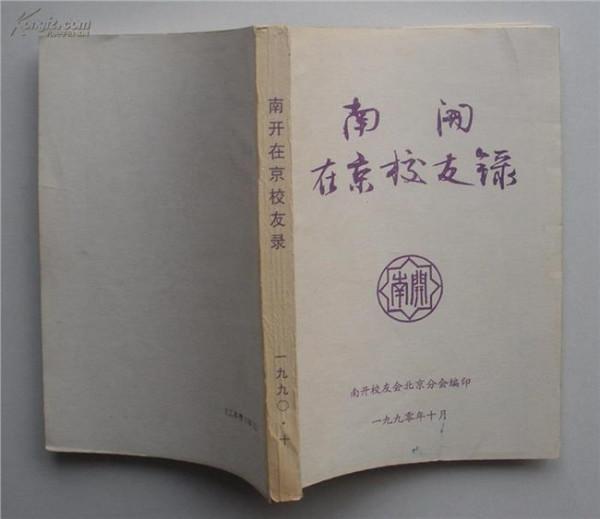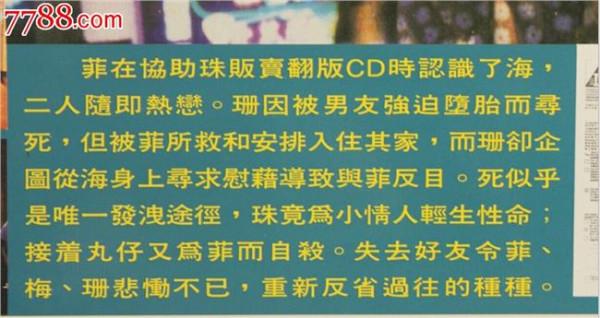钱钟书经典语录 从钱钟书评价说起
不久前杨绛女士在106岁高龄上仙逝,自然是喜丧。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能够活下来真的并不容易,媒体与自媒体的漫天盖地,也在意料之中: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缺少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了。就连那些假冒着杨绛女士名字的鸡汤格言,也不足为奇:如今时不时有人造谣,而且往往就有更多人相信。真实成为稀缺,让人往深想想竟然有些不寒而栗。

我在七十年代见过杨绛女士几次,印象不是很深,多半是由于钱钟书先生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她是一位很正常、有些锋芒的民国女知识分子。她的学问自然也是好的,但是比起钱钟书先生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事实上,杨绛女士毕生主要还是传统的女性角色,自觉自愿地辅佐支持夫君。她的当代传奇,首先还是因为她是钱钟书夫人,其次大概是由于她的长寿,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渴望长生不老,有着长寿崇拜的民族。

杨绛女士去世,由此又引发了不少有关钱钟书先生评价的文章。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或者读不懂;就连他的《围城》,更多的人只看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认识陈道明扮演的方鸿渐。杨绛女士的文字,要平易普通很多,但也绝对不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那一种。他们伉俪身后或晚年成为人所共知的明星人物,很难说和他们本身有多少关系。

大概是因为见过不少历史人物的本尊吧,我更倾向于叙述往事,而不是臧否人物。中国人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个人好恶,做道德人品的判断。另一方面,学问公器,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标准的。在我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学问家,在历史学方面首推陈寅恪,在文艺批评方面当属钱钟书。如此评价他们的第一人,似乎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

至于大思想家,那是一个也没有的。不必以思想体系去要求他们,陈、钱都是谨守分际的学者,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对任何思想体系都抱着怀疑态度。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不用说是实证的,钱钟书先生的文艺批评也是十分具体的。事实上,对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追求,往往是长期浸泡在宏大叙事话语的结果。
以为思想大于学问,有思想比有学问更为重要这样的判断,人为地把思想和学问对立起来,分出高下。我看到一篇比较钱钟书与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大意是钱钟书有学问没有思想,维特根斯坦很少读书却是思想天才。
且不说这种随意比较本身相当可疑,令人有关公战秦琼的感觉,而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更加苛责:“知识人的特征其实就是具有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的人。批判精神表现为主动发现问题与揭示问题的精神,主要体现为意向和勇气。
批判能力是他的知识结构、洞察力与创造力的体现。用这个标准,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还算不上知识人身份,充其量是个知道分子。他的所谓学识渊博只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玩意,放弃自己的时代责任和担当,体现了一种油滑的犬儒人生态度与卖弄渊博的儒家文人心态。
那种掉书袋式的注释的学问,如果说在传统治学方法上还有点价值的话,那么现在在电脑、互联网时代连个大点的U盘都不如”。话说到这份上,我真是无语,只能相信作者恐怕从来没有读过《管锥编》了。
勇气用来激励自己可以,去评判别人则多半不着边际。或许是从小学习雷锋、刘胡兰没有学明白吧,总有人习惯用英雄的杠杆要求别人。从道义勇气的角度去评判钱钟书那一代知识分子,仅仅是看上去大义凛然而已。关于钱钟书研究的是冷冰冰的死学问,没有思想价值,或者说他是继承乾嘉之学,逃避现实,缺少勇气等等,和那些没怎么读过他的书却一味追捧他的话语一样可疑。
这种评价的背后,是以有思想理论,对现实有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为前提的。持此逻辑的人,看不到学问乃至思想,往往是无用的或者说与时代现实无关的。
需要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相当淡薄模糊,所谓亡国遗民的忠诚,更多是对于前朝。从民国时过来的知识分子,长期不被当成自己人,如果没有功名心,沉默与边缘化实在是最合理的选择。仔细读一下过去一甲子多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那些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热血青年,或者是在党内有自己思想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主人翁意识,这是那些被认为是旧时代人所不具有或者不敢具有的。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是在海外游学多年,精通若干门外语的,而主要著作都是以文言文写成。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到《柳如是别传》,从《谈艺录》到《管锥编》,百年白话文在这里了无踪迹。其实无论从治学方法乃至日常生活习惯,两位先生都是深受西方影响之人,绝非食古不化、崇尚国学的冬烘先生。不过学问的起点,可能真是在于旧学的根基。这个根基的断裂,倒不必归咎于白话文,更多是世事播迁中其他因素所致。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大半是主义先行,概念大于研究。引领风潮的学者,留下的多半是通论。像陈寅恪先生和钱钟书先生这样毕生沉浸在细节中的学者,数量不多在当时影响也不大。他们在九十年代开始成为传说,固然有当时的具体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是不可复现的。
从世代上讲,陈寅恪是新文化运动时人,钱钟书则是后新文化运动一代,但他们都是新旧交替时节旧学新知兼备之人。陈寅恪先生的“不中不西,不今不古”虽然有自谦的一面,却也道出了事实。
他上承乾嘉,又留徳多年,对兰克史学方法论了然于胸;晚年从个人遭际考察时代的着眼,更与西方史学战后由政治经济向社会史、个人史倾斜的变迁多有契合。钱钟书先生的术业我所知不多,不敢妄议。他博闻强记、精通中外典籍,自然也是考证十分扎实,然而中西互证互文的方向,应当更多是来自西方比较文学的方法吧。
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从牧斋暨同时代人的诗文中考察河东君行迹,阅读之广泛、梳理之细密,非常人所能及。比如通过钱柳互相赠诗,两人的相遇与相爱情景得以复现。钱钟书更不用说,“管锥”一语,就出自“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他自己也自谦是“识小积多”。《管锥编》一书是见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之集大成。书里使用多种语言、无数典故,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读的。但是这部书本来就是研究著作,不是给一般人读的。
陈寅恪考证杨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子,连钱钟书先生都以为“琐碎”;而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最常被人诟病的也是碎片化、缺乏理论。然而两人在本专业内几乎从未被这样批评,后辈学人对他们的景仰多出于其学养之深厚与不可企及,这种景仰与坊间的追星完全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陈寅恪和钱钟书思想性的批评和近一个世纪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脉相承。有一种戏说:留欧美的重视学问,留日的倾向主义。陈寅恪和钱钟书自然都是在多研究些问题那一边的,历史学也好,文艺学也好,都是具象的,不需要高屋建瓴的理论创新。
不过他们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陈先生治史,求真求实;钱先生论文,要在审美。史学家的问题意识里,终究不免现实关注,何况陈先生有着很强的“天水一脉”文化传承意识;审美意识需要更多的超越精神,于当下本应保持距离。
文艺批评说到底是门无用的学问,钱先生虽然没有专论,但他应该是同意“凯撒的归凯撒”,从来没想越界做什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正是因为不同,所以陈先生关于杨贵妃的考证应该是与原本出自胡人的唐朝宫廷道德风俗有关,而钱先生似乎未曾看到这一层深意。
陈寅恪先生因为名气大,还是颇受优遇的;钱钟书先生因为谨慎,也没有过多被整。不过在运动频仍的年代,日子都不好过。陈先生最终在“牛衣对泣”中死去,钱先生也经历了女婿的自杀,在“记愧”文中自嘲怯懦。《干校六记》自不待言,《洗澡》在我看来也是可以当纪实读的。二位的同代人在后半生留下著述的,多半是活得长、身体好,进入八十年代后还能够动笔的。能够在艰难时代不曲学阿世,以笔写心,留下属于自己的巨著者寥寥无几。
钱先生在学部(社科院前身)交游并不多,是一个神秘的话题人物。他学问和才气太大,七十年代初在河南干校就成为一个传说。我在七十年代末随父亲去他府上,默默地看见钱先生是怎样世情练达,嬉笑反讽,眼高于顶,根本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他极具幽默感,语多讥刺,对晚辈却很温和。我从小不怵名人而且多嘴,大概问过不少傻问题吧,钱先生总是很耐心也回答得很暖心。我至今没有请名人签字的习惯,但我很珍视钱先生签名赠我的《宋诗选注》。在一个晴朗的夏日,费孝通先生、杨绛女士、父亲和我坐在南沙沟客厅里,每人手里一把大蒲扇,听钱先生独白。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他其实没有谈话对手,更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钱先生不以诗名,二十多年后,我才读到《槐聚诗存》,窥见他内心的另一面,沉痛只是偶尔写在诗里: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当代著名新儒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多年的刘述先先生于2016年6月6日晨逝世,享年82岁。在网上读到一篇刘述先先生访谈自述平生,其中提到他的父亲刘静窗与张遵骝的交往:“我父亲在北大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张遵骝,他是张之洞的曾孙。
张遵骝是学历史的,专长在佛学,钱穆先生、熊先生都教过他。牟宗三先生当年没钱,还靠他接济。他后来主要跟从范文澜,范文澜著作中有关佛学的部分,主要就出自张遵骝之手。张遵骝解放前在复旦任教,解放后才移到北京”。
1954年熊十力先生自北京移居上海,张遵骝先生写信给刘静窗,为他和熊十力牵线,熊刘从此交往颇密,在一起谈儒学佛教,其中的手谈部分被刘述先之弟刘任先保存收藏在阁楼里,安然度过文革风暴,出版为《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
刘述先回忆他的父亲1949年曾经想走而没有走,只是把他和堂哥送出去读书。从此刘述先一路顺风顺水,读书、任教、留学,学成后在美国和港台任教研究,卓然有成。熊十力与刘静窗留在上海,虽然有幸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里受到大的冲击,但也无处著述,只好在孤独与沉寂里度过余生。
我以前只知道张遵骝先生是熊十力的弟子,不知道他还曾经受教于钱穆先生。他三十岁就已经是复旦大学副教授,但是除了帮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里面的佛教史部分,没有自己的著作。所以张遵骝先生的学问见识怎么样,现在除了回忆已不可考。
然而对同时代人一般评价相当苛刻的钱钟书先生曾经说他“博究明人载籍,又具史识,蒐罗而能贯串焉”。张先生和父亲的交情在文革后期好到可以经常辩论,因为父亲是资深党人,张先生在辩论中就会时不时引用马恩列斯,信手拈来,往往能够说出在第几卷第几页,当时令我目瞪口呆,如今想来颇为荒诞。
因为没有文字流传,张遵骝的名字如今早已被遗忘,似乎也就是我时常提起这位我少年时的启蒙长者。我在网上搜索,竟然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只有一张“国立复旦大学副教授”的名片,作为文物保存下来了。不过在30年代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张先生际遇还是相对平稳的,我搜索到张遵骝的一位同学,不知其名,只在网上看到照片和墨宝。
这位先生相貌清癯,写一手好词好书法,却因为抗战期间给美军当过翻译,镇反时被押送回浙江原籍劳改。1951年去香港的大门还没有关,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香港,不久后张爱玲也是走的这条路。
他在故乡似乎已没有亲人,孤身一人做了十多年农活,在三年困难中和村里一个时常照料他生活的寡妇结婚,相依为命。他的案子到70年代末才平反,晚年他在浙江一所高校里教英文。
他教过的学生,30年后还对他感激不尽。我就是从他的一位学生的博客里读到了他的生平,还有一首词:“万斛柔情,都付与镜中花月。勘破了诸般色相,但余凄切。孤塚埋妻魂梦杳,天涯有子音书绝。剩萧条白发一慈萱,分艰孽。亲故断,尘缘灭,心力瘁,生涯竭。任儿嬉狗吠,靦颜偷活。冷炙残羹和泪下,荒村野径吞声越。看年年寂寞走江乡,何时歇“?
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人,未必要通古今之变,但不可没有同情之理解;未必要宏大叙事总结历史规律,但不应缺乏对个体生命与内心的关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是一个远远没有说完的话题。每一个个案都有不同的情境,有人令人尊敬、有人值得同情、也有人不必原谅。
需要避免的,恰恰是从抽象的思想高度或者勇敢程度轻易评价。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亲身经历了那么多变化,多到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忘记了上一代人的艰辛。我们甚至往往意识不到,忘记历史会让人做出怎样错误的评价与判断。





![钱瑗和杨伟成 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3/42/3425c64764ac784a1ff129a6953b1ca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