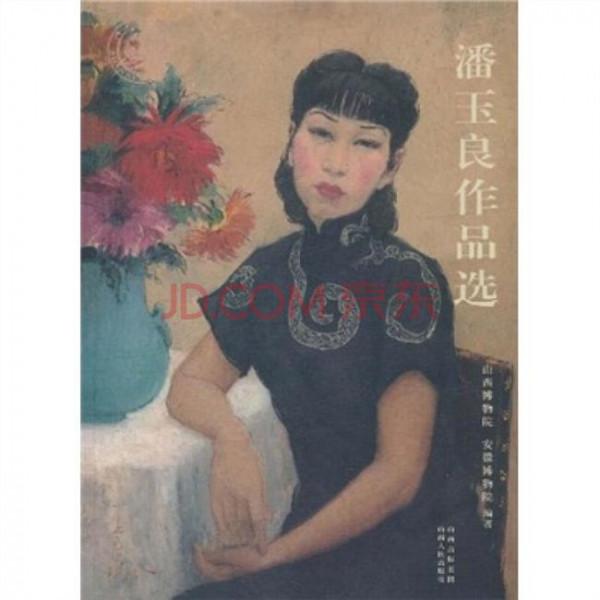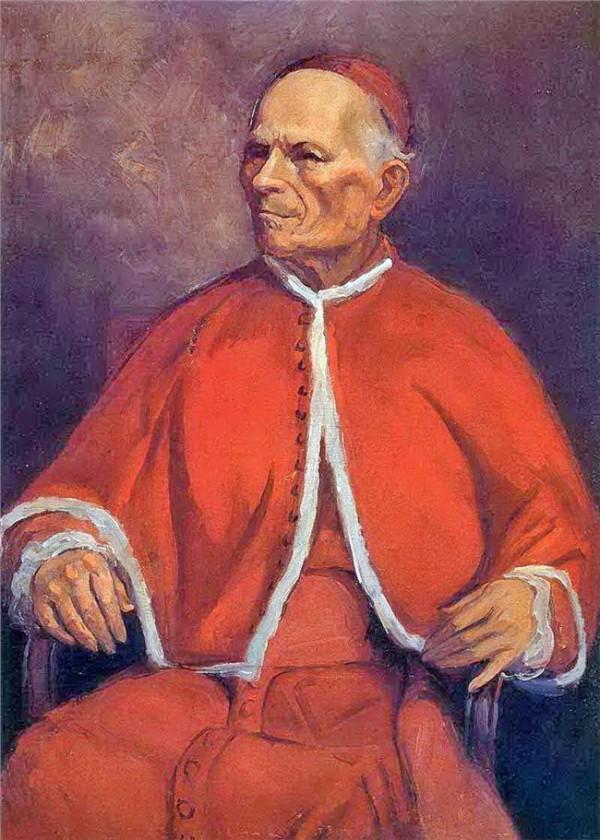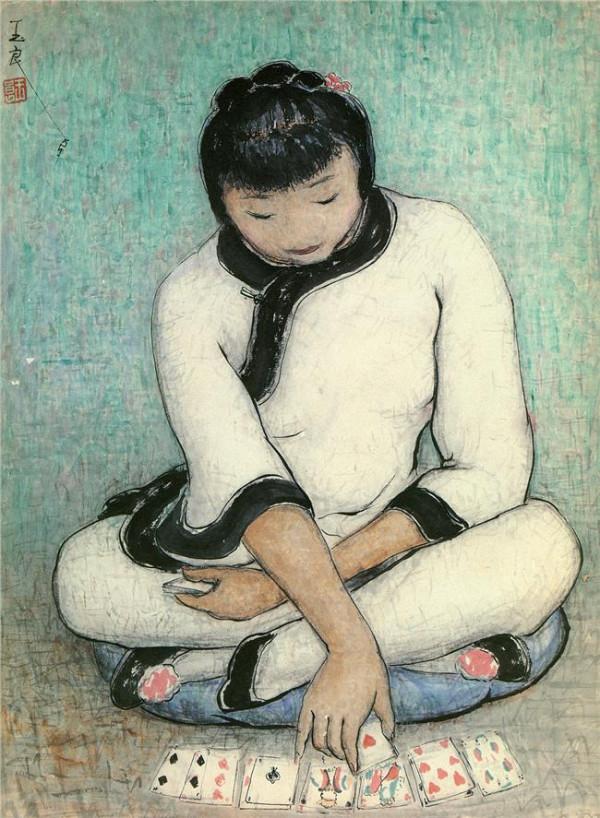潘源良歌词 潘源良的“葬月”与小说《雪狼湖情种》
〈葬月〉是音乐剧《雪狼湖》第二幕的歌曲之一,音乐剧在1997年公演,同名小说《雪狼湖》在1998年正式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葬月〉的内容是记述小说第六节〈情种〉的狱中故事。
有人提出「葬月」应改成「月葬」,理由是歌词中的「我」,根本不是埋葬月亮,而是在月夜下把自己的内心埋葬,故以「月葬」更为合适,然而,辅以小说内容,「葬月」亦有其意义包含其中。虽然人与月相距甚远,但月是形而上的,是可看的实体,所谓葬月、把月亮掩埋,则有想把形体束缚舍弃的意味及象征性。

狱中的友人石头曾对胡狼这样说,有肉体有躯壳,就会伴随痛苦,胡狼本身长期处于束缚状态,住在公园兽笼,被关进拘留所,然后是四年牢狱生活,环境的拘束,「给我依靠倾诉唯有身边几块墙/给我窥看天际唯有是零落破窗」,形体必然的衰老,「残留在面上风霜」,是对于胡狼自由的限制,亦是他无法超越的部分,「这世界只得这样/请准许将我心/在月夜下埋葬/就此抛弃这冷冷世上/飞到星河新生方向/拥抱明月/再哭笑一场」,胡狼对于禁闭空间本来没有特别感觉,而最后令他爆发成〈葬月〉歌词中的激烈情感,是因为恋人宁静雪。

「人都有一颗会漂移的心;这颗心,不会停在时间的河流上。」
抛弃形体限制,可有两个解读,一是意志颓唐,甚至死亡倾向,一是转而追求心灵解放,歌词中呈现出较消极的面貌,小说的胡狼则倾向于解放心灵。在囚禁的最后半年间,宁静雪已没有再来信,胡狼认定是她等不及自己出狱,而另有归宿,歌词中「当初一切欢笑全数变得很抽象/他朝一切希冀全数就如是妄想」 ,他的欢笑和希冀就是宁静雪,如今失落了,衍生出「身边只有孤单」、「寂寞尽情膨胀/却似觉很应当」的感觉,虽然曾有「飞到星河新生方向」的呼告,但整体上对于即将告别的牢狱显得十分冷淡,因为「束绑只有束绑/如何破解也一样」,而寂寞的膨胀也仿佛是应当的,对于世上的无权无情无理感到不能承受,那么离开牢狱与否,对于胡狼来说也就没有分别。

月亮的阴晴圆缺,被古人视为月亮的死而复生,小说中的胡狼曾想自沉湖底,「孤独地跟池底的沉淀物躺在一起」,就在满月的夜晚,看到红星花,改变了初衷。红星花要在小盆生长,「盆子愈小,越能逼出花来」,一株红星花尚能坚强如此,作为一个人也像没有颓丧的理由,于是放弃轻生念头,祈愿宁静雪能得到幸福。
满月象征重生,胡狼在当下释怀,比〈葬月〉的消极无奈,呈现一份积极,但再想一层,月的圆缺是周而复始的,今夜满月也会再次缺失。
「对于这头属于蛮荒野地的生物来说,一旦没有铁笼的保护而投身纷乱人世,自由,或许只是跟死亡等同的东西而已。」《雪狼湖心愿碎片》
小说中胡狼对赤猴的话,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总结下来,即使〈葬月〉表达的无奈孤单,与《雪狼湖情种》一节表达有所不同,但贯切了潘源良填词的风格。无独有偶,潘源良在1994年写的〈望月〉也是关于狼和月,而当中亦有相似之处,〈望月〉「就算哭笑中豪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对月/就算这世情难料」,〈葬月〉「拥抱明月/再哭笑一场」「月光/请听我诉说寄望/若果/这世界只得这样/请准许将我心/在月夜下埋葬」 ,〈葬月〉更像是〈望月〉的深化,由与月共饮,到埋葬内心于月下,就像一步步进入自我封闭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