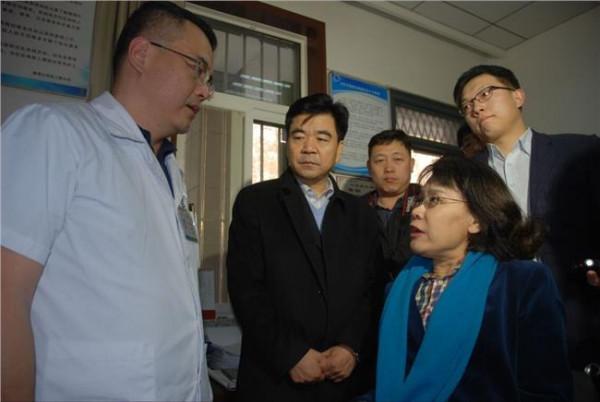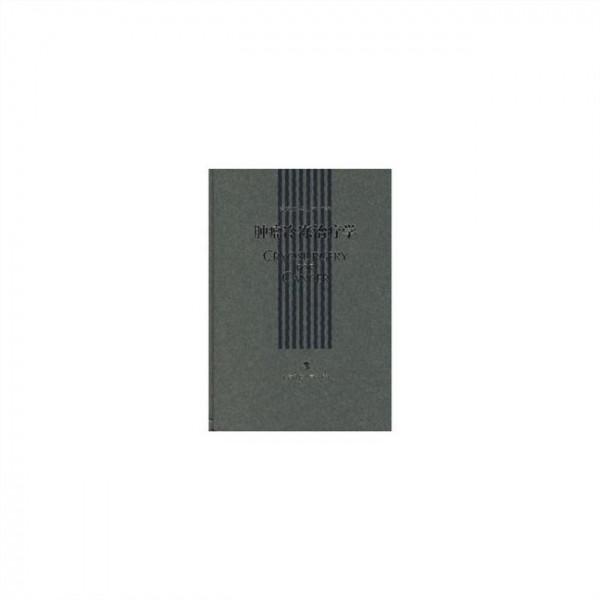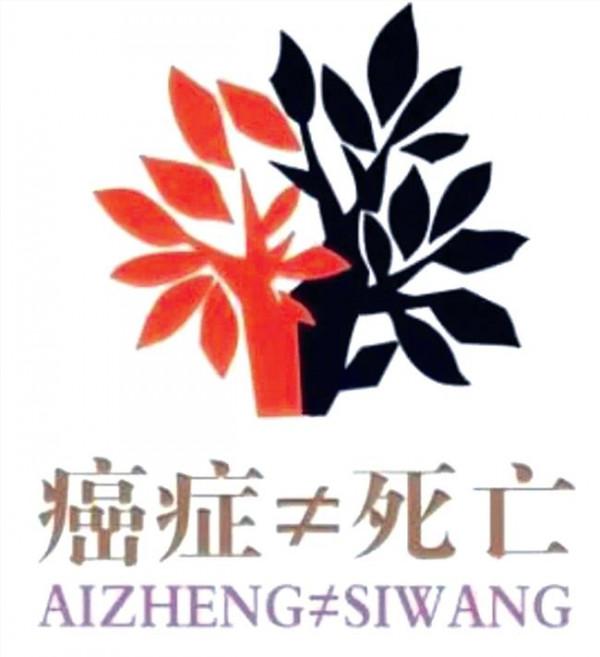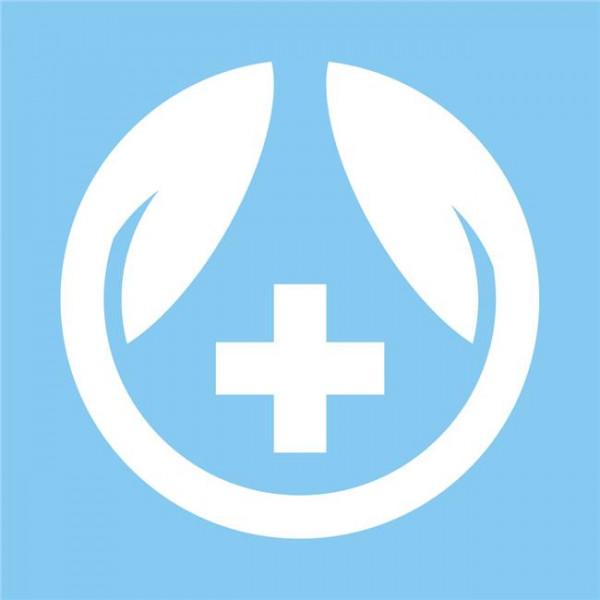徐克成简历 徐克导演 从老怪成长到老爷的历程
“我一直没有长大过,我还是一个孩子,这是很好的感觉”,这是徐克在2008年釜山电影节大师班讲座开始的第一句话。他由衷地热爱自己的童年,因为在那个阶段,他结识了电影,自此有了一生中最纯粹的快乐。
1951年出生在越南的徐克,家里有众多亲戚兄弟姐妹,一共二十多人,每天都是在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喧哗中长大。直到7岁,他可以摇摇摆摆地跨出家门,生活的天地宽阔起来,虽然彼时世界之大、战世之乱,于他,也不过都是一个个游戏。
“我们在街上玩,路边沟里积了很多水,小孩就在里面游泳。”西贡的家附近有两个戏院,“孩子的游戏就变成想办法钻进戏院里,每到开场前观众开始进场,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拉着人家的手进去。有些大人不喜欢,有些大人也无所谓,一进去就立刻躲到角落里看电影”。
无独有偶,另一位电影大师吴宇森在香港,也几乎同样尾随陌生人混电影看,还曾因为被抓到蹭票,而被打得鼻子流血。小徐克也是战战兢兢,“戏院里的人很厉害的,会拿手电筒照躲起来的小孩。不过后来守门的人都认识我们这群孩子了,如果有时观众不多,就让我们进去。”
“蹭电影”的乐趣不仅是刺激,也不仅是混进去的小孩绘声绘色地把内容讲给其他小朋友听,其高潮是讲完故事后的“演电影”,“我们会扮演电影里的角色,我记得那时戏院放了很多印度歌舞片,常常跳舞唱歌,于是那条街的小孩子都变成印度歌舞片里的人物;等开始放《哥斯拉》时,整条街的小孩又都躲起来,觉得这个城市都要被怪物入侵了”。生活的虚拟,电影的真实,从那时起,徐克看待世界的眼睛就不同了。
不知道是小朋友中的哪一位,第一次带来相机,不但记录下孩子们扮演逃难、做游戏、载歌载舞的照片,也让拿起相机的徐克发现自己的天赋,“那时候很多人一起拍,我的朋友拍的都是人。我拍的都是奇怪的东西,但我觉得我拍的很有趣。
我意识到原来可以通过相机制造自己的世界,从此我不会抗拒科技”。这些照片后来被街道上一家摄影器材商店的老板发现,他竟然主动问徐克们要不要用8CM摄影机拍东西,“然后我们这拨10岁11岁的小孩就开始拍电影,每天放学后跟家里说,我今晚不回家了,去拍电影”。
某天清晨的黑泽明
徐克的中学是在香港读的,离开西贡那些小伙伴,他的日子过得百无聊赖。1964年的一天清晨,他独自坐车,路过香港的丽声戏院时,熟悉的戏院场景让他想起带给自己无限快乐时光的越南。“也许,进入戏院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吧”,抱着这样的心情,他下了车。
那天,戏院早场电影是黑泽明的《用心棒》,“开场时只见三船敏郎的背面,加上早土反文雄的配乐,我整个人呆了,方才发现原来电影可以如此的酷”。本是以找寻童年记忆为开始,却意外发现银幕上的电影这样有深度,那次震撼让徐克久久难忘,从此他养成一个习惯,“喜欢一个人早上去看没有观众的电影”。
1967年,中学毕业后的徐克也面临未来选择的问题,身边同龄人多在父母期望中走上做医生、工程师、律师等前途光明的职业,徐克却迟迟不能决定。他还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坐巴士,朋友问他未来打算做什么,徐克心里不停问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像童年一样一直生活在开心的环境里吗?”这时,巴士戏剧性地再次经过丽声戏院,那个清晨里看黑泽明《用心棒》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说,我想拍电影”。
在唐人街办电视台
徐克幸运地获得去美国学电影的奖学金,先后在南卫理工会大学及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修读,并且很快就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洗片的工作。“所谓洗片就是把拍摄记录片的胶片放在机器里洗,虽然是很机械的工作,可洗片旁边就是剪接室,剪接师在里面忙着把画面和录音合起来”。
纪录片拍的都是当时美国各种游行示威,有一次徐克“被迫”连续两天反复听一个人演讲的录音,快要疯了,他忍不住对剪接师说,“你让我试着对一对嘴吧”……由此他变成剪接师的助手。
在学校里,徐克也坚定地贯彻什么都做的理念,比如他打灯的技术一流,“我当时帮一个教育电台的儿童节目做,儿童节目一般灯光都打得亮亮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够气氛,就先在主要光源的地方打了一排灯,其他地方就补,其实比正常的打灯还简单一点,可是节目组很喜欢”。
毕业后,他和朋友合拍了一部四十五分钟的有关美籍亚洲人的纪录片《千钟万缝展新路》,也曾在纽约的那个地唐人街报纸作编辑,而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和当时的伙伴创作了唐人街街坊电视台(CTTV)。
“那是30年前的事情,唐人街有很多废弃的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三楼是我们的办公室。当时我们觉得,唐人街的许多华人移民,语言上不通,经济上不好,职业可选择性不高。我亲眼看到有些老人只能对着讲英文的电视台,可能什么都听不懂,但依然每天看;有些妈妈在制衣厂做工,一天十几个小时,对儿女根本照顾不了;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所以无论老人、小孩、工作的人,回到家都情绪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把唐人街的家庭弄得开心一点,当时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舞台话剧,做新闻访问,尽量制造更多的娱乐带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