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谈西安事变 【十一艺节】谈现代京剧《西安事变》的艺术创作
【十一艺节】谈现代京剧《西安事变》的艺术创作
抗日 民族 西安事变 个体 民族伦理
滚动快讯
韩睿
王 馗
叶剑英在其《访西安办事处志感》中有诗云“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透过历史的风烟,将波澜壮阔的民族事件,展示在抒情的笔调中。窗前风雪轮回,故人早已离世,而已经浓缩成历史符号的“西安事变”,却因为时光荏苒,逐渐地成为民族危亡之际历史的透视镜,不断地折射出更加多彩的人生和更加丰富的心灵。
任何一个与此相关的人,都因为这个“危局”,而显示出对于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抉择。显然,“抗日”“民族”“公义”是这个时代命题中,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的重要道路。
现代京剧《西安事变》正是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捉蒋危局,用史诗的笔触来展现民族抗日的大伦理、大道德、大智慧。在人们不断地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行纪念的时候,这部回应时代诉求的艺术作品,显然要将西安事变中的人与事,进行一次重重的渲染和张扬,展现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追忆和体认。
所谓的伦理,即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对于“安内”和“攘外”的民族伦理。众所周知的“攘外”和“安内”实际是特定政治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考量,真正能够对这个二元对立的话题有所回答的,只能是历史。因此,经过70年,甚至是更多的时代考验,抵抗强敌外侮、争取民族独立,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选择的道路。
对于中国人而言,“攘外”是民族自立、民族自强的必要条件,“抗日”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对于那段民族记忆的代名词,正显示了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来对于生存危机所保有的警惕和激励。
因此,现代京剧《西安事变》所牵涉的每个历史人物,当仁不让地成为“攘外”这个主题的鲜明注脚。剧作消减了脸谱化的表达方式,试图还原历史真实,让那些历史中反面的群体和个人不再出现在舞台群像中,正表达出对这个大伦理的绝对尊重。
所谓的道德,即是在时代长河中对于“个体”和“民族”的家国道德。“西安事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者那里众说纷纭。其难点即在于这个事变中的每个个体充满着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即在于这个事件实际成为每个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博弈。
正如剧作所展现出来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权力与派系的角力,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分歧,中外各种势力存在着依存与毁灭的选择。
所有这些都交集于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因此,“危局”能否翻转,既决定于个体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决定于每个个体的趋势走向,当然最终便成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中的历史走向。剧作试图通过个体的伦理选择,来彰显民族团结的道德理想。
无论是张学良、杨虎城在日寇不断进犯中,自觉而主动地选择了抗日道路;还是周恩来临危受命,力挽狂澜,通过侃侃而谈展现政治立场;抑或蒋介石分析情势,被动放弃旧有筹谋,都共同指向摒弃前嫌、兄弟携手的民族理想。这个理想实际强调的是对于民族观的大道德。
所谓的智慧,即是在历史变迁中对于“私德”和“公义”的人生智慧。正如剧作开篇即用国共战争渲染了西安事变前的形势,这是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现实;紧接其后的则是日寇进逼之时的学生运动,这是家国动乱之际的社会状态,这些点染正烘托出纷纭变幻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群体所发出的时代诉求。
在此基础上,个体或群体如何选择?是选择置外侮不顾而持续地内斗?还是选择将民族利益超越于私人积欲之上?实际呈现的是对于“公”与“私”的郑重选择。
剧作每每将个体的“私德”放置在“公义”面前,不断地考量着彼此的权重。张学良是在学生们痛诉家破人亡的请愿运动中,引发了对于沦丧乡土的怀恋;杨虎城是在政治形势分析中,放弃了个人偏见;蒋介石是在内部派系纠结、兵谏困扰中,选择了符合时代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剧中周恩来亲赴蒋介石住处,明白地将个人对于蒋介石生死的态度表达出来,如同张学良评价自己与蒋介石之间那种“政见之争宛若雠仇”,作品将周、蒋私人的雠仇毫不遮掩地张扬开来,同时又让二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相逢一笑泯恩仇”,成功地展现了个体私欲让位于民族大义的情怀,在严肃的时代和民族使命前,张扬其个人超越于时代、党派、政治的大智慧。
在这部作品中,剧作者拨开历史的繁复变幻,消减人物的钩心斗角,化繁为简,从宏大的历史篇章中,挑选出西安事变期间最核心的张学良、周恩来、蒋介石、杨虎城、宋美龄等几个人物,通过彼此之间的思想变化和关系纠葛,刻画出翻转时代危局的步履和达成民族共识的诗心,将属于中国传统以来文化精髓的大伦理、大道德、大智慧,透过直接明了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来。
特别是京剧和现代戏的叠加,并没有让《西安事变》成为话剧与演唱的结合,相反创作者们努力用京剧的本体艺术,特别是音乐唱腔,浓墨重彩地表达剧中人的情绪、思想,实现诗化再现。
每个人物都有集中抒情的唱段,每个唱段都有展示京剧板式音乐的华彩结构,加上流派艺术的渲染,该剧的唱段实现了可听、可唱、可以流传的艺术效果。
现代京剧的创作,每每囿于革命京剧的创作藩篱,无法拓展出丰富的舞台表现。而重大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亦每每囿于历史真实,无法生发出可亲可感的舞台形象。这种创作上的局限,决定了京剧现代戏的舞台创作极具挑战性。而该剧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洗练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的情节故事予以形象地展示,正显示了创作者对这一藩篱的有意突破,在该剧不断地进行戏曲化和个性化的提升之时,该剧在京剧现代戏的题材创作和技法处理上必能带来大的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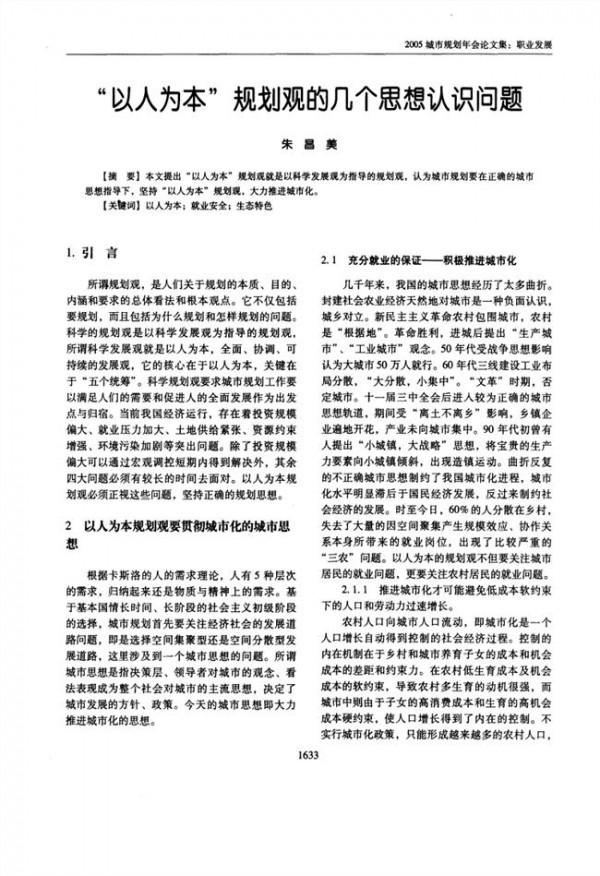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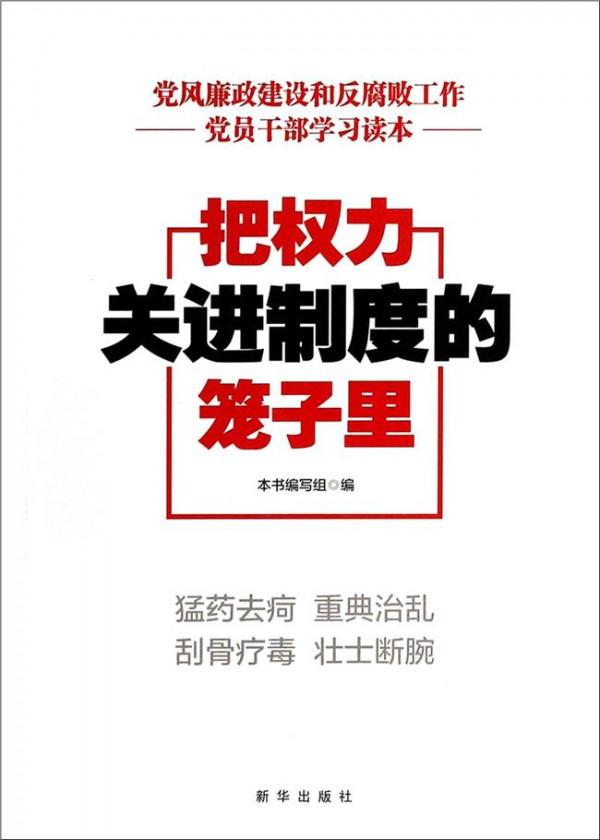
![>谢春涛讲稿 谢春涛管党治党十六讲 [管党治党十六讲]民主集中有“原则”](https://pic.bilezu.com/upload/c/59/c59d395ff1fd6cf462dfcfce3bfc6c1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