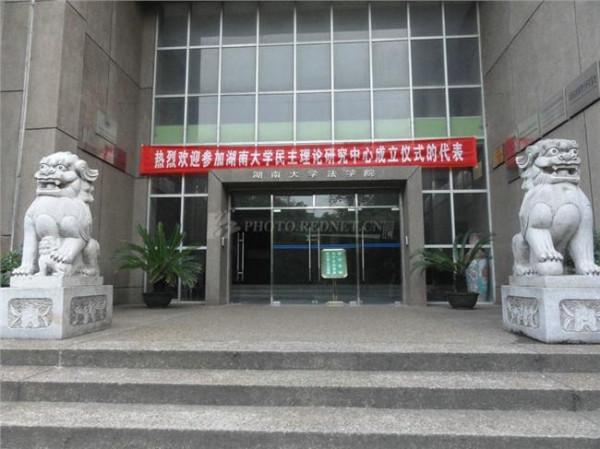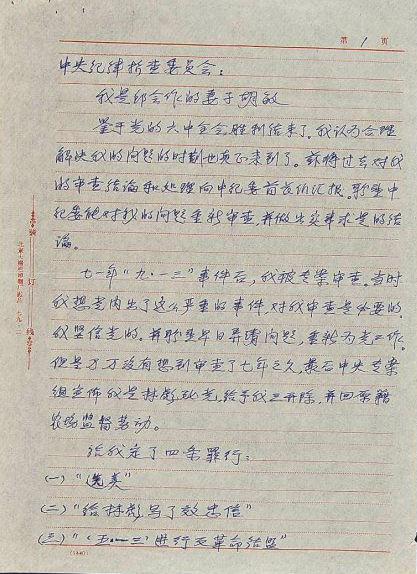邱兴隆的夫人 邱兴隆:一个刑辩人的愉悦、郁闷与痛苦
虽然我早在1988年即获得了律师资格,但在此后的10余年中, 我从未有想过自已会要做律师,哪怕是兼职律师。因此,虽然我有过不短的下海经历,但上岸后,还是走上了当老师与做学问的回头路,而丝毫没有动过做律师的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让律师资格证尘封了那么多年,应该无外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眼高手低,多年来养成了抽象思辨的嗜好,醉心于形而上的思考,视所谓学术为阳春白雪,而瞧不起律师这一下里巴人的职业;其二是,生性孤傲,不善处人际关系。而律师,尤其是当下的中国律师,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话,是难以立身的。
我做律师始于兼职,而且事出偶然。在“转会”湘潭大学后的2011年秋的一天,我正给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授课。一位女性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来到了我的课堂外,称她那本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丈夫是我的校友,前不久因受贿2万元而被拘捕。
她找我是想让我为他提供法律帮助,因为她丈夫曾告诉过她,我是他师兄,是一位刑法学家。听其道完原委,我走回课堂,问在座的有无做律师的学员。当时有不下10人举了手。但是,当我再问有无愿意为我的那位校友免费提供帮助者时,竟无一人再举手。
望着课堂外那对充满信任与期待的母子,我当即作出了一个几乎是出于冲动的决断:启动我那尘封了10多年的律师资格证,注册兼职律师。这样,我的律师生涯以免费为我的这位校友辩护而开始。
一晃10多年过去了,我的律师之路没有中断过。尽管偶尔也受理过民事代理业务,但基于对刑事法的专业偏好,我主打的一直是刑事辩护。回眸这10余年的律师之旅,几多愉悦,几多郁闷,几多痛苦。
我之作为刑辩律师的愉悦,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集中在三个时刻:
其一是,当我的委托人起死回生之时。10余年中,我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可能处死刑的案件不下30起,包括部分被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其中,最终有一大半没有被判处死刑或者由二审改判非死刑立即执行。尽管我知道,这些人的起死回生绝非我一人之功,但是,我为自己的努力到了肯定而欣慰。
毕竟,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作为一位死刑废止论者,在死刑的废止尚未成为现实之时,能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努力,挽留更多的生命,自当为尊重生命的理念得以在具体案件中践行而愉悦。
其二是,当我的委托人得以无罪开释之时。10余年来我经手辩护的案件数以百计,最终被决定不起诉或者被判无罪者逾30人。尽管我也知道,他们的重获自由,也不只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其中当然包含有我的贡献。做为律师,还有什么比在自己的参与和努力下让自己的委托人洗清了冤屈更值得愉悦的?
其三是,当我对案件证据、定性与量刑等的独到见解得到了司法机关认同之时。曾几何时,作为学者的我对现行司法实践抱怨颇多,总认为实践顽固地抵制理论。然而,当我以辩护人身份实实在在地涉足具体的案件时,我才发现,学界存在许多盲点,既存理论无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这迫使我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将其用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所提出的没有法定理由的“提外审”所获得的口供因取证地点不合法而应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实体刑法意义上的有利被告论与民间高利贷非罪论等,不但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了采纳,而且,在学界或者特定区域的司法界形成了相当的影响。
而这实际上都是源于具体案件的辩护。由此,我获得了作为学者所必需的素材与灵感,当然也因自己做出的理论贡献得到认同而深感愉悦。
说到郁闷,也是常有的事。而其中最甚者,莫过于如此三个时刻:
其一是,当作为辩护人的法定权利受阻之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查阅案卷,本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人的权利,而且,得到了新律师法的进一步确认。然而,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权利的实现往往阻力重重。以我的经历,侦查阶段尤其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虽然并非总是无法实现,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的会见只不过是有名无实。
因为这样的会见大都是在侦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得询问案情。而且,侦查人员在场名为见证实为监视,律师的哪怕是有名无实的会见权的实现,竟然要以受到监视为代价,岂能不令人郁闷!
至于阅卷,尽管在审判阶段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都不再是大问题,但是,有的检察机关给律师阅卷设置障碍的事,也时有发生。
通常的表现方式是,有的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让阅卷,而在起诉到法院后,也不移交全部案卷,而只移交证据目录与部分证据复印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辩护人的我往往会因庭审前对案卷材料掌握不全而在庭审时被动。郁闷的是,每遇此等情形,当我向检方提出查阅全卷要求时,都被检方理直气壮地拒绝。其理由是:刑诉法只规定提交主要证据目录与主要证据。
其二是,当执业活动遭遇不合理的执业规范的妨碍之时。本质上说,辩护人与当事人之间是基于协议而产生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既然是合同关系,自然应该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然而,至少在刑事辩护的收费问题上,意思自治是难以实现的。
因为一方面,律师法等禁止刑事辩护律师做风险代理,即使当事人有此等要求与希望,辩护律师也无法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既存的刑事辩护收费标准普遍偏低,而律师为辩护所付出的劳动完全可能是极其巨大的。
这样,在许多情况下,刑辩律师所付出的努力与其所实际获得的报酬难以成正比。我曾有过为一个案件复制、查阅200多卷案卷材料、做出近20万字的阅卷笔录、并连续出庭20多天的经历。
然而,如此大的付出所获得的律师费与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的收费几乎相同。律师的职责与良心不允许我拒绝受理此等重大复杂案件,但办理此等案件的付出与收费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衡让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劳动无法得到认可。为此,我不得不为律师执业规范如此歧视刑事辩护而郁闷。
其三,当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与尊重之时。按理,辩护人应该是最值得当事人尊重与理解的人。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为辩护所做的努力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但是,也遭遇过当事人失信、无理取闹乃至恶意投诉的尴尬。
基于失信而拒付律师费者有之,因未达到其一厢情愿的目标而要求退还律师费者有之,因退还律师费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歪曲事实真相向律师协会投诉者,也有之。每遇此时,我虽然可以因自己问心无愧而泰然处之,但是,我也不得不为如何处理与当事人的关系而郁闷。
至于说痛苦,首当其冲的是,当我的委托人虽经我竭尽全力辩护但最终仍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之时。也许是受自己已经根深蒂固的废止死刑论的影响,在我看来,我所辩护的被告人没有一个是该死的。因此,我总能煞费苦心地其找到免死的理由。
但是,最终仍有近10人未能逃脱被处死的厄运。在最高人民法院回收死刑复核权之前,我曾做过抢下留人的努力,但是,我的委托人最终仍难免一死。在最高人民法院回收死刑复核权之后,我曾不只一次促成受害方与我的委托人的亲属达成和解,并让受害方向法院出具对我的委托人予以从宽处理的书面请求,但是,我的委托人最终还是被最高法院认为,虽然认罪态度较好并能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但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宽处罚,并被核准死刑。
每遇此刻,我所承受的痛苦总是难以言状的,我甚至会认为是自己的无能或者失职才没有留住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鉴此,大凡可能判处死刑或者已被一审或者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现在我总是望而祛步,哪怕是我觉得依法、于理均不该判处死刑的案件,哪怕是当事人家属明示或者暗示,“只有能把命留住,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我还经常因为作为学者的身份与作为辩护人的立场的冲突而痛苦。作为学者,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我有我既有的或者应有的看法,但是,作为辩护人,我不得不在具体的案件的辩护中回避或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持有利于我的委托人的观点。
虽然我总会站在辩护人所应该有的立场为自己的这种作为开脱,但是,又总会为自己作为学者的品格被自己毁损而痛苦。我甚至经常为学者与律师是否可以兼容而自扰。这也是我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虽然留下了不下数百万字的辩护词,但只发表过3篇所谓学术论文的原因所在。
其实,作为刑事辩护人,我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受到来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排挤、打击和藐视。在法庭上,我曾遭遇过与我女儿同龄的女公诉人以屁股相对的无礼,也遭受过曾经是我学生的法官的呵斥。在法庭外,我曾经不只一次遭遇过来自侦查机关诸如监控电话之类的威胁。每遇此刻,我总会为都是法律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痛苦,更会为辩护律师的地位乃至人格的卑微而不堪其受。
刑事辩护是一项折磨人的事业。它可以让人顷刻登上愉悦的顶峰,也可以使人顷刻达至郁闷的极点,还可以将人顷刻抛入痛苦的深渊。
刑事辩护也是一项满是遗憾的事业。它无时不在印证我那句“没有遗憾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格言。但是,它固有的残缺美,又总激励着我为弥补这样或者那样的遗憾而不倦地努力。因为我始终坚守着我那个“明知是一种遗憾却不予弥补才是真正的遗憾”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