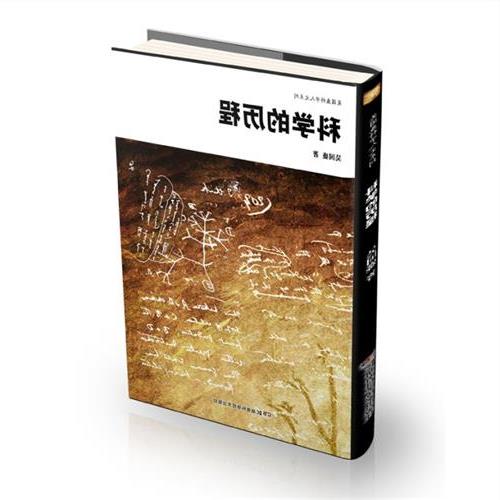科学通史吴国盛 吴国盛:学习科学史的意义
今天,不大可能有人问科学有什么用了。约四百年前,科学的作用远未像今天这样彰显,但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近代自然科学已经一步步向世人显示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
其实,这位哲人还有另外一句关于知识的名言同样值得引用:“读史使人明智。”在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我们不再对身边的科学表现出惊奇,甚至已经对科学无动于衷,而恰恰在此时,我们需要回顾科学的历史,因为读史使人明智,阅读科学的历史可以使科学时代的人们变得深思熟虑、深谋远虑。
科学是引人入胜的
学习科学史可以增加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科学史有助于理科教学。历史故事总是使课堂教学变得有趣。我们在儿时谁没有听过几个科学家的传奇故事?阿基米德在浴盆里发现了浮力定律后,大喊大叫着跑上街道,赤身裸体地告诉每一个人他终于发现了;伽利略为了证明落体定律,把一个木球和同样大小的一个铁球从比萨斜塔上扔下,结果是同时着地的,于是反驳了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认为重者先落的理论;牛顿在一个炎热的午间躺在一棵苹果树下思考行星运动的规律,结果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下来打中了他,使他茅塞顿开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在外祖母家度假,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烧水壶的壶盖被正在沸腾的开水所掀动,结果发明了蒸汽机……
这类科学传奇故事确实诱发了儿童对神奇的科学世界的向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能够诱发儿童热爱科学、向往科学事业的传奇故事,对于正规的理科课程学习并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倒是相反,某些以讹传讹的传奇故事对于深入理解科学理论还是有害的。传奇故事往往过于强调科学发现的偶然性、机遇性,使人们容易忽略科学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极端艰苦性。
除了传奇之外,科学史所能告诉人们的科学思想的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对学习科学理论肯定是有益的。当我们开始学习物理学时,常常为那些与常识极为格格不入的观念而烦恼,这时候,如果了解一下这些物理学观念逐步建立的历史,接受这些观念就变得容易多了。科学家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古怪”地思考问题,他们建立“古怪的”科学概念的过程很好理解而且引人入胜。
以“运动”为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呢?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说,运动有两种,一是天然运动,一是被迫运动。轻的东西有“轻性”,如气、火,它们天然地向上走;重的东西有“重性”,如水、土,天然地向下跑。这是天然运动,是由它们的本性决定的。
世间万物都向往它们各自的天然位置,有各归其所的倾向,这个说法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轻的东西的天然处所在上面,重的东西的天然处所在下面,在“各归其所”的倾向支配下,它们自动地、出自本性地向上或向下运动。
一旦物体到达了自己的天然位置,就不再有运动的倾向了,这时候只有外来的力才能迫使物体运动,这样的运动是被迫运动。地面上物体的运动都是受迫运动,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最低处所。受迫运动依赖于外力,外力一旦消失,受迫运动也就停止了。
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这些观念当时从常识的角度似乎觉得很自然,很有道理,可是近代物理学恰恰首先要破除这些观念。“运动”观念上的变革首先是由伽利略做出的。伽利略从一个逻辑推理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设想一个重物(如铁球)与一个轻物(如纸团)同时下落。
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当然是铁球落得快,纸团落得慢,因为较重物含有更多的重性。现在,伽利略设想把重物与轻物绑在一起下落会发生什么情况。一方面,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更重的物体,因此,它的速度应该比原来的铁球还快,因为它比铁球更重;但另一方面,两个不同下落速度的物体绑在一起,快的物体必然被慢的物体拖住而不再那么快,同时,慢的物体也被快的物体所带动比从前更快一些,这样,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最终达到一个平衡速度,这个速度比原来的铁球速度小,但比原来纸团速度大。
究竟哪种说法更合理呢?各有各的道理!但它们之间却不一致。伽利略据此推测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有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从逻辑上讲,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途径是: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所有物体的下落速度都相同。
科学的进步并不完全是靠逻辑推理取得的,伽利略这位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创造者,并未满足于逻辑推理,而是继续做了斜面实验。他发现,落体的速度越来越快,是一种匀加速运动,而且加速度与重量无关;他还发现,斜面越陡,加速度越大,斜面越平,则加速度越小,在极限情况下,斜面垂直,相当于自由下落,不同物体的加速度是一样的。
当斜面完全水平时,加速度为零,这时一个运动物体就应该是沿直线永远运动下去。斜面实验表明,物体运动的保持并不需要力,需要力的是物体运动的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更新!
伽利略没有能够直接对落体运动进行实验,因为当时准确的计时装置还未出现。伽利略发现摆的等时性时是用自己的脉搏计时的,足可以说明当时科学仪器的缺乏。斜面可以使物体下落的加速度减小,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观测,在此基础上,伽利略最终用“思想实验”由斜面的情形推到自由落体和水平运动的情形。所谓的比萨斜塔实验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伽利略本人的著作里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这个关于“运动问题”的科学史故事,对读者深入学习牛顿力学知识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回顾这个观念更替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观念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这比直接从概念、定律和公式出发去学习牛顿力学当然要生动有趣得多,而且印象也深刻得多。
追究科学史的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在“知道”(Know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之间做出区别。为了掌握一门科学知识,我们大多不是从阅读这门学科的历史开始,相反,我门从记住一大堆陌生的符号、公式、定律开始,然后是在教师和课本的示范下,反复做各种情形下的练习题,直至能把这些陌生的公式、定律灵活运用到处理各种情况为止。
但我们真地“理解”这些知识吗?那可不一定。我知道一位非常年轻的大学生,他高考的物理成绩几乎是满分,但是在兴高采烈地去大学报到的旅途上,他却一直在苦苦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从轮船和火车上跳起来时,仍能落回原处,而轮船或火车在他跳离的这段时间中居然并没有从他脚底下遛走一段距离,他在轮船上试了好几次,轮船一点儿也没有遛走的意思。
然后他又想起,地球时时刻刻都在转动,而且转速极大,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跳起来落不回原地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直到他读了一本有关科学史的书,懂得了牛顿第一定律的真实含义,他才恍然大悟,痛骂自己愚昧无知。
这个故事可以说明“知道”与“理解”的区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位年轻大学生的故事正是我自己早年的经历。有了知识并不等于理解,在深入理解物理定律的本质方面,科学史是有作用的。不幸的是教科书大多不谈历史,如果有也只是历史知识方面的点缀,诸如牛顿的生卒年月等等,很少史论结合,以史带论的。
科学是怀疑和批判的
也许是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教育界盛行的依然是分数教育、技能型教育,这种教育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培育了不少科学神话,树立了不正确的科学形象,形成了对科学不正确的看法。首先是将科学理论固定化、僵化,使学生以为科学理论都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其次是将科学理论神圣化、教条化,以为科学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后是将科学技术化、实用化、工具化,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
破除科学神话,纠正不正确的科学形象正是科学史的重要使命。
当代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带来了高等教育严重的分科化,学问先分文理,理科再分成数理化生,还有更细致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等等。分科教育很显然是为了造就专门人才,但在中学和大学低年级,通才教育是更有实际意义的。
只有少数人将来会成为科学家,但即使对于他们,狭窄的专门训练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力。在教科书中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术语、新公式、新定律面前,学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真理,学习它、记住它。
久而久之,历史性的、进化着的科学理论被神圣化、教条化,人们不知道这个理论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们还要相信它是真的。这种教条的态度明显地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但在科学教育中产生这样的态度又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学生不知道一个理论源于哪些问题,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其中一种并称之为科学理论,学生也不知道这种理论是可错的,并非万古不变的教条。
结果是它不自觉地剥夺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于科学发展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的印象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享受着真理的位置,达尔文之后生物学上对进化论的发展在普通教育界一直是模糊的,仿佛它已进入了绝对真理的行列。久为传颂的是达尔文主义所经受的诘难以及对这些诘难所做的成功驳斥。
那是在1860年的英国牛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刚在上一年出版并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学术界内部亦有分歧,达尔文主义的著名斗士赫胥黎坚定地捍卫进化论,遭到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的讥讽。他责问道:赫胥黎先生,我恳请指教,你声称人类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这究竟是通过您的祖父,还是通过您的祖母呢?面对这样的恶意中伤,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进行了成功的驳斥。
这段故事一直作为捍卫真理的典范来传颂,然而,如果从进化论本身的缺陷以及面临的发展角度看,威尔伯福斯主教的责问有相当重要的科学意义,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通过特殊遗传而积累有利变异的能力,它与竞争规律以及所出现的有利变异一起在自然界中积极地起作用。
”达尔文其时,细胞学说刚刚建立,遗传学尚未开始,这样的“能力”也就是在进化中起作用的遗传因子尚未出现,主教的讥讽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回答。今天,进化论已经过了新达尔文主义进入了综合进化论时期,威尔伯福斯的问题可以回答了,其作为恶意中伤已变得毫无力量,而这恰恰是生物学的进步和进化论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
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发展的、进化的。几乎没有什么比科学史更能使人认识到这一点了。自然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相互联系的方面,在按学科分块的教科书中肯定得不到体现,而科学史却能够给出一个综合。我举热力学第一定律为例,说明科学史何以能够体现科学的统一性。
这个定律又称为能量守恒定律,就我自己的经验,从教科书中始终未能获得关于这个定律的完整理解。从历史上看,它首先来自运动不灭原理,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力学本身的发展,人们在18世纪即发现了机械能的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原理的最终确立有赖于许多领域里相关研究的出现。首先是热与机械运动相互转换的研究。然后是化学和生物学上的研究。第三是电学和磁学的研究。各路人马都在奔向一个伟大的原理,在提出或表述能量守恒原理的科学家行列中,有美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姆逊,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俄国化学家赫斯,德国物理学家楞次和赫尔姆荷兹,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法国工程师卡诺,英国律师格罗夫,丹麦工程师柯尔丁;还有德国医生罗伯特·迈尔,他几乎是从哲学上明确地导出这个原理的。
这么多人大致在同一时间里提出同一科学原理,真是科学史上罕见的事情。
如果不是科学史,我们肯定无法理解“能量”这一概念对于人类理解自然现象的意义。“能量”概念提醒我们自然科学的统一性,提醒我们不要深陷在各门学科的技术细节中,忘记了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人类建立一个关于外在世界的统一的整体图像。在学科分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尤其需要这种统一的图像。
科学是最富人性的
今天,我们对许多科学的东西耳熟能详,我们觉得许多科学道理理所当然。但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熟知”往往并非“真知”。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都逃避了理性的反思,反而成为一种盲目的东西。这应该引起高度警醒。科学史可以帮助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和人文意义。
在诸种科学神话中,关于科学家的神话也许是流传得最广的。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家被看做在某一方面有惊人的天才,掌握了与自然界进行对话的神秘钥匙,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低能儿,而且表现得离奇古怪。有些故事也许是真的,但不可把这看做科学家的本质特征。
由于专注于某件事情而忘了周围的一切,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并非只有科学家如此。另一方面,科学家在结束他的研究工作时,他与常人一样,而且在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和从事艺术宗教活动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