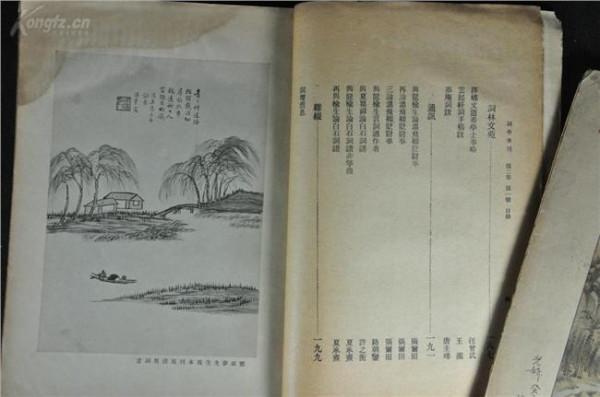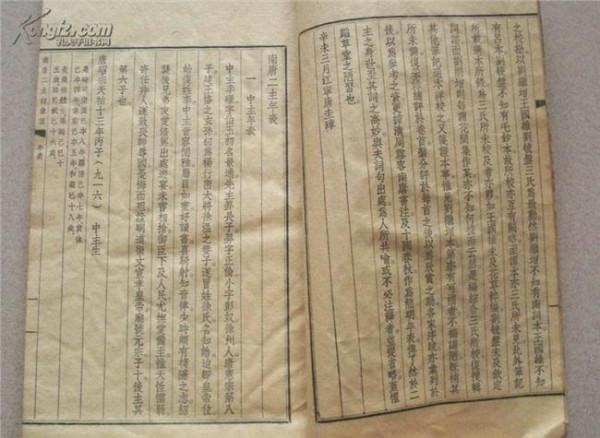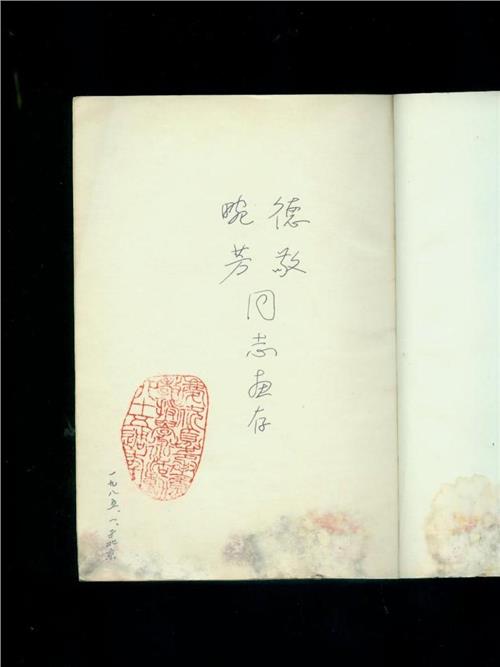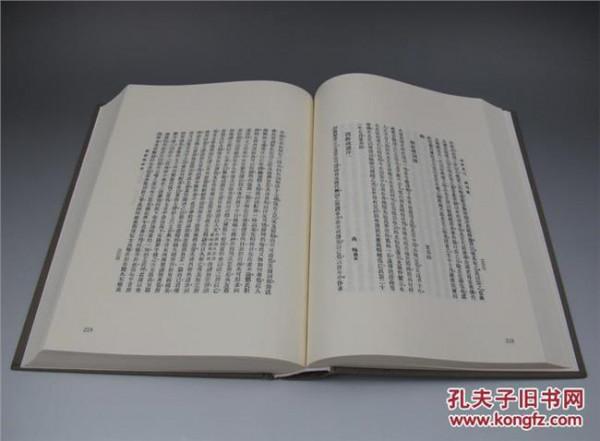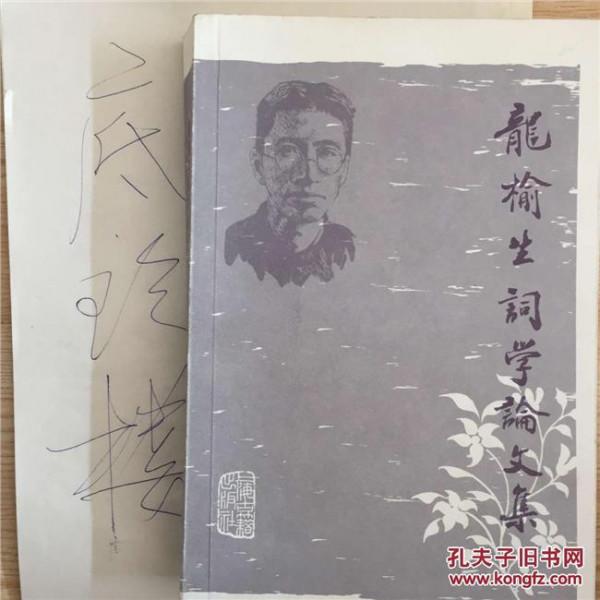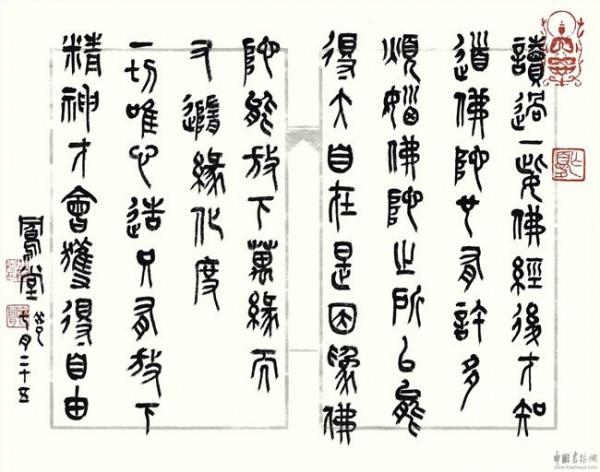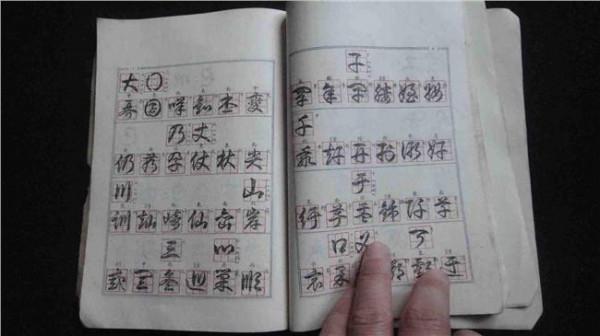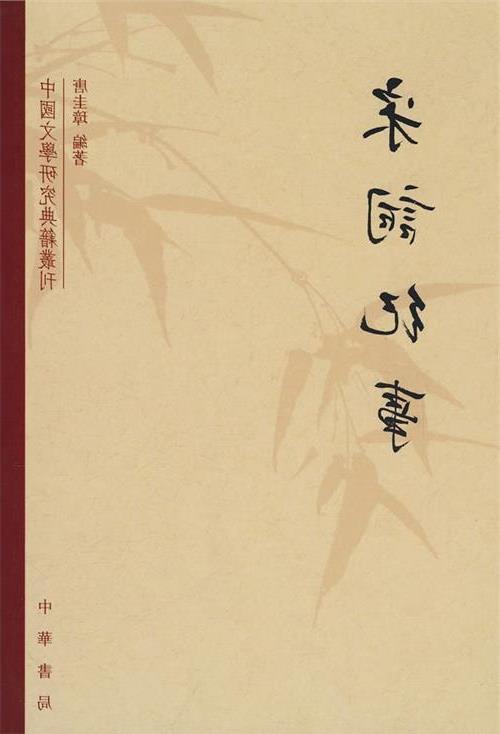夏承焘词学谱系 唐圭璋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源流和谱系
尝语余云:仆亦金陵词弟子也。’可见朱氏学词之师为端木氏,王氏则在师友之间。”则端木�一王鹏运一朱祖谋的词学传承得以清晰勾勒出来,而“金陵词弟子”云云,则隐然具有金陵词派或金陵词人群的意味。王鹏运从端木�学词当为其官内阁中书之时,今存端木�批点张惠言《词选》及手订《宋词十九首》皆在这一时期完成。
端木�并将《宋词十九首》持赠王鹏运,而后来王鹏运在《碧山词序》中也曾转录端木�批语,则王鹏运对端木�词学的认同,确实是不容怀疑的。
而所谓王鹏运与朱祖谋“在师友之间”,乃是因为“二人同校词,同刻词,志同道合,一往情深”,其关系之密切,也非常人可喻。 次看朱祖谋同时期的词学交往。唐圭璋说:“朱氏又与况周颐、文廷式、郑文焯为治词好友,彼此互相切磋,蔚为风气,成就俱卓绝一时,为海内所称道。
”唐圭璋将龙榆生在《清季四大词人》中的“王鹏运”易为“朱祖谋”,应是王鹏运的年辈稍长,而且曾是朱祖谋的词学导师之故。不过,就像王鹏运与朱祖谋之间兼有师友关系一样。
况周颐也曾在内阁中书任上与端木�、王鹏运以词相唱和,并将当日唱和作品刻有《薇省同声集》,似乎也有亦师亦友的色彩,只是况周颐与其虽为同僚、年辈较后而已。端木�对况周颐督责甚严,如虚字问题、声律问题等,俱有提点,备载于况氏《蕙风词话》中。
则端木�与况周颐之间,就词学传承而言是否需要隔着王鹏运,也是一个疑问。 朱祖谋与况周颐的关系颇为密切,不仅在况周颐官内阁中书时,两人多有切磋,一时并称“朱况”,而且朱、况二人曾合刻有《鹜音集》。
文廷式与王鹏运交往较多,朱祖谋《望江南》评文廷式词“拔戟异军成特起”,在晚清别树一帜。郑文焯晚年退居苏州,与朱祖谋也是“朝夕过从,谈词不倦,即偶然小别,亦书札往还论词无虚日”。
明乎朱祖谋与同时词人之交往情况,就知道唐圭璋所说“彼此互相切磋,蔚为风气”,非虚语也。 再看朱祖谋之后流变的词学谱系。在晚清五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文廷式与况周颐中,王鹏运与文廷式都卒于1904年,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卒于1926年,朱祖谋卒于1931年。
王鹏运与文廷式因为去世较早,对清末民初词学的影响相对较小,郑文焯与况周颐虽并有时誉,但论词坛影响与组织能力,朱祖谋则更为突出,加上朱祖谋去世最晚,所以其对民国年间词学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唐圭璋曾一一探及在朱祖谋影响之下的词学发展情况。 由于朱祖谋曾任广东学政,文廷式也少长岭南。广东词风遂不能不受其影响。
如叶恭绰虽从家学而言,三世治词,但受朱祖谋与文廷式的影响便颇为明显。叶恭绰主事完成的《全清词钞》最初即是以朱祖谋为总编纂的,只是因为朱祖谋去世而由叶恭绰接续此事。而陈洵更是得朱祖谋扬誉而闻名词坛。
龙榆生“问业朱氏,孜孜不倦”,是受教晚年朱祖谋最多的词人。唐圭璋说:“朱氏喜其学有根基,因将所学于师友之词学以及一己学词之心得体会,悉以示之;对于历代词家之特色,亦指陈详明。”朱祖谋临殁,更将平日所用之砚授之龙榆生,传承衣钵之意甚为殷切。
龙榆生在三十年代初与叶恭绰合办《词学季刊》,其中也包含着弘扬朱祖谋词教的用心。师从龙榆生学词者又有周泳先、朱居易等。 夏承焘也承教朱祖谋甚多,尤其在笺释梦窗词上,受朱祖谋指点更为直接。
此外,夏承焘《论词绝句》能自成规模,也与朱祖谋的鼓励有一定关系。夏承焘问业的林�祥也曾受教于朱祖谋。杨铁夫曾从朱祖谋学梦窗词并致力阐释梦窗词,关于梦窗词的诸多笔法,多由朱祖谋一一指明。
刘永济也曾自道曾从朱祖谋、况周颐学词,赵尊岳则是况周颐高足,唐圭璋虽然未曾亲接朱祖谋教诲,但以私淑弟子自许。其为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详为笺注,“注解”之外,博征诸家评笺,弘扬疆村“浑成”之旨,甚为明显。
在唐圭璋的勾勒之下,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已经宛成格局。夏敬观在端木�批注本张惠言《词选》后曾有识语云:“清咸、同间,金陵词人在京朝者,先王父《篆枚堂词》、何青士丈《心庵词》先出,而子畴《碧瀣词》继之,半塘、疆村并问业于丈。
疆村晚年尝语余日:‘仆亦金陵词弟子也。”’看来,这一谱系不仅有词人的“夫子自道”,而且源流固自分明的。 然而,如果把唐圭璋论及的词人按照谱系,略作整理的话,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年龄的差异不一定构成明确的“代”的差异,何况这一时期的词人年龄的差级并不一定很大,而且学词有先后,更削弱了这种年龄上的差级。
加上这一时期词人与词人之间的传承并非单一,而是以错综的情形居多。
如此要清理谱系,就必然存在着取舍的角度问题。 若以“金陵”的地域来考虑,将著籍金陵及其曾在金陵工作或者追随金陵词学的词人,按照谱系整理,从咸丰、同治年间算起,则以夏壤、何青士居前,端木�继之,然后由王鹏运而传之朱祖谋,朱祖谋既自称“金陵词弟子”,则“金陵词派”的说法虽然在地域而言有欠周密,但从学理上说,却是可以成立的。
朱祖谋之后,就是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或学习的吴梅(词得力于疆村遗民)、乔大壮(素遵古老之教)、陈匪石(请益于朱疆村先生)以及辈分稍晚的唐圭璋、卢前、任中敏、夏承焘等了。
当然具体到唐圭璋,师事的老师还包括仇�、汪东、蔡桢等人。为求直观,兹大致根据唐圭璋的表述,略述谱系于下: 夏�、何青士――端木�――王鹏运――朱祖谋●端木�、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朱祖谋――吴梅、林鸥祥、乔大壮、陈匪石、陈洵、叶恭绰、夏承焘、杨铁夫、刘永济、龙榆生●况周颐――赵尊岳、刘永济●吴梅一唐圭璋、卢冀野、任中敏、赵万里●仇�、汪东、蔡桢――唐圭璋●龙榆生――周泳先、朱居易●林�祥――夏承焘●文廷式――叶恭绰●王国维――赵万里 毋庸讳言,若全面考量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上面列述的显然不够全面。
但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词学也大体包蕴其中了。唐圭璋由一己之经历见闻,上下梳理,左右横推,并以朱祖谋为基点,勾勒出晚清民国的词学谱系,其在现代词学史上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四、王国维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潜流 王国维在20世纪词学学术史上具有突出的影响,但因着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对其《人间词话》的解读、研究也以“同情之了解”的居多,若以批评为主的评论在其学术史早期,不仅不多见,而且也不大为人所关注。
最早以批评为主流的文章应该是朱光潜的《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朱光潜在文章中虽然也将《人间词话》视为“近二三十年”中文学批评的“最精到”之作,但对其“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重要概念,大体是持否定的态度。
不过,朱光潜否定的,有的属于概念阐述的不够妥当,如隔与不隔;有的属于概念名称略有纠葛甚至矛盾者,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唐圭璋的《评人间词话》虽然也肯定王国维“议论精到”,但也主要是批评其中“未尽当者”。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