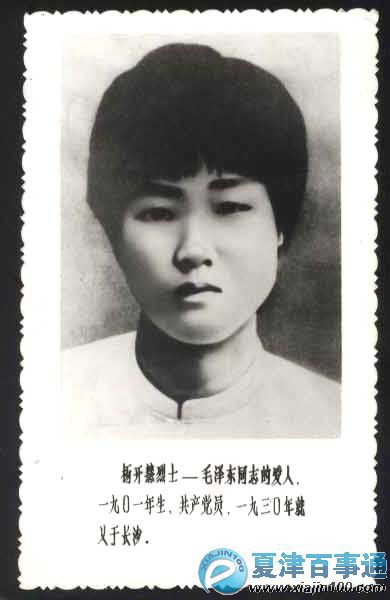杨开慧烈士遇害受刑经过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 党 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 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 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
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得一塌糊涂。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
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坦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
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
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
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