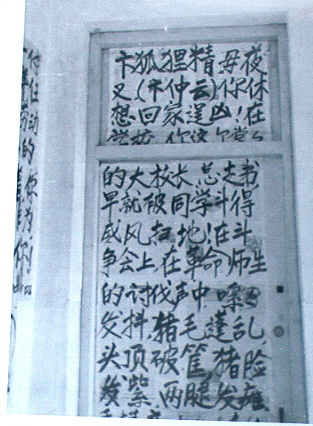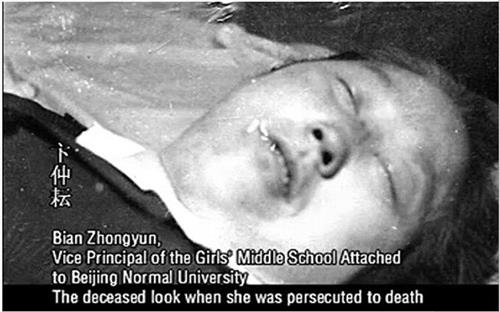刘亭亭卞仲耘 刘少奇女儿刘亭亭忆旧: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话说,如果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么敢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3个月后,在江青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着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鲁豫:您爸爸妈妈见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候?
刘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时,旁边围着许多群众,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妈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们的人逼着我们小孩站在旁边看,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佩服我妈,她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他们把我父母隔离了,我爸找不着我妈,腰一下就弯了。他们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还打他,打得我爸扶着窗台走路。有时我爸出来吃饭,我们就假装洗手和他说几句话。
有一天,突然来辆大卡车,通知我、刘源和刘平平去学校,要把我们一小时内送回学校。当时我们特别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别。他们不让我们去,全拉走了。第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学校,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到中南海门口,不敢说想见父母,说要见我们的小妹妹。我们也想了其他办法,比如写信要我们的书啊字典什么的,都是希望爸爸妈妈在送出的东西里能给我们写点什么。
没多久他们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队,他那时16岁。我姐姐被抓走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她在洗衣服。忽然就来了几个人,问哪个是刘平平?我姐说,我是。人家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当时觉得突然,但也没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转头跟我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后来我们每天等她回来吃饭,摆着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没再回来。
鲁豫:您那段时间哭得多吗?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着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回答令她泪盈于睫:“因为相互信任。”爱和信任,在最混乱、最残酷的季节里,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