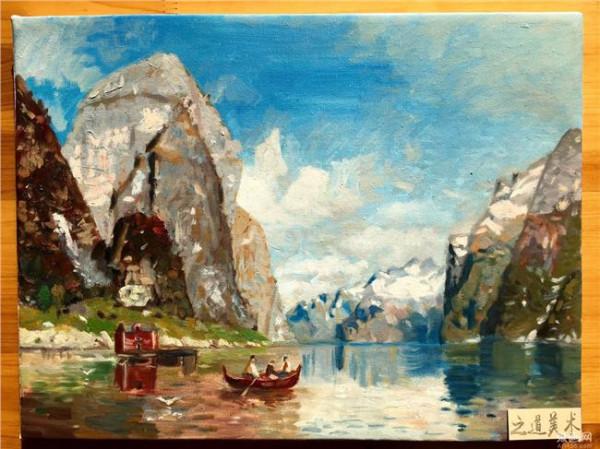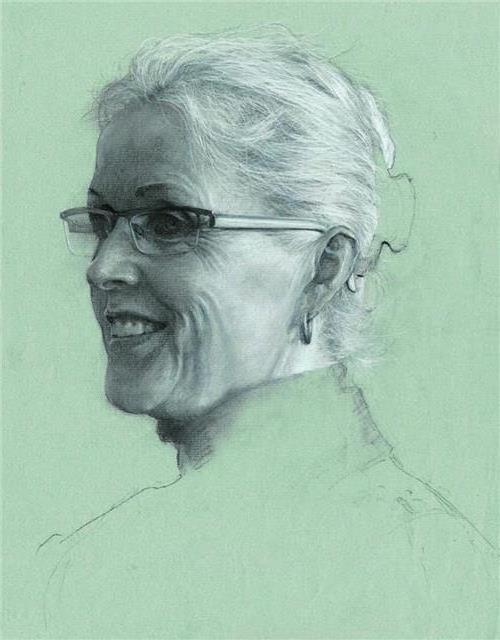徐芒耀专访:油画表现语言中的思考
时间:2009年9月
地点:北京华侨大厦
采访/文字:乌蓝
记者:徐老师,我们简单聊聊您的从艺经历吧。
徐芒耀:好的,60年代,我考上了浙江美院附中,毕业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教学机制全部处于停滞状态,分配工作也暂停了。一年之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入卫生防疫站宣传科工作,搞卫生宣传画工作,也参加了不少大型展览,整个专业还算没有荒废。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大学招生。我很幸运,我考上了中国美院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全山石老师和王德威老师。后来有机会去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法国是所有油画爱好者与专业画家的梦想之地。
机会不是人人都有,从84年到86年夏一待就是两年多。这期间我对绘画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国后,我又回到浙江美术学院,直到98年。之后,我被上海师范大学作为人才引进调入,一直到现在。这就是我的学艺和从艺的经历。
记者:您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有没有受谁的影响啊?
徐芒耀:我对绘画的热爱也许是天生的吧,父亲早年教授中文,后来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我家里没有人搞绘画。影响我走上绘画这条路得有两位,一位是丰子恺,另一位是我的大姨父郭勤初。我家祖籍石浙江桐乡崇德的,与住在石门湾的丰家是姻亲,两姓之间互有婚配。
算起来丰子恺应该是我父亲的表叔,也就是我的爷爷辈了。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到丰子恺家去过,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考上美院附中的时候,父亲特地带我去登门拜访。丰子恺听说我考上了美院很是高兴,当即送了我一卷画。
不过我当时还小,后来在美院附中学习的也是学院派的路数,接受的都是苏联式的绘画基础训练,学习表现造型、表现明暗、色彩感、空间感、重量感。丰先生的画作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更谈不上珍爱,渐渐地那卷绘画也就不知所终了。
我的大姨父郭勤初,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他是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的美术编辑组负责人,笔名毛毛,当时《儿童时代》的小读者都知道他。过去上海的住房很紧张,我的外婆、姨妈一家和我们家都住在一起。姨父晚上总是在家里画插图,我就趴在桌子的另一边静静地看。
到第二天早晨,我都能把他画的插图默画出来。从幼儿园开始,我画的画就总是得到老师的称赞,并且经常被选贴在壁报栏中展示,这种鼓励更是无形之中增添了我的作画欲望。
小学毕业时,我的画画水准在班上已是首屈一指了。后来入卢湾区少年宫,继而考入市少年宫绘画组接受指导。所以说最初引发我对绘画兴趣的并不是我的父亲,虽然在我后来的成长道路上,父亲对我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也给了我无数的鼓励,这些都留在了父亲给我的一封封家书里,那时候我在杭州念美院附中,父亲的信也曾给我的附中同学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大概是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开玩笑似地对我说:“我看你蛮喜欢画画,要是真喜欢,你就拜姨父为师吧。”姨父很严肃地让我选择:“你真的喜欢吗?喜欢我可以教你。但是我告诉你,我最讨厌没有恒心与毅力,学业上半途而废的人,你要想清楚,要是决定学的话,以后哪怕碰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好好想想吧,过两天我再问你。”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不再与我提起此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到了第三天中午,我正靠在门边看着窗外发愣,我其实正着迷于窗外的流云千变万化的模样,看一只猫无声地走过,然后又消失。
我总是这样,观看入神时忘记身之所在。母亲早就发现我的这个习好,她总说这孩子做一件事情很容易沉迷进去。我正看得入迷的时候,姨父走过我的身边,开始发问了:“芒耀,你想得怎么样?”我说想好了,跟你学。
“你既然决定了以后就不能打退堂鼓了”,姨父说完,转身在柜里拿出一叠道林纸和一叠新闻纸,一共200张,“你每天完成当天作业之后就得画画,每星期必须完成一张素描,还要临摹一张连环画”,这是姨父给我布置的作业。从此以后,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我就一头扎进画笔与画纸之中。
小学毕业后有两年的时间,我一直接受姨父严格的绘画训练。姨父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毕业后也教过书。他当时要求我在素描作业中注重以明暗表现体积。这两年中,每星期一张素描一张连环画临摹雷打不动,到了星期天他按时检查。经过这个阶段的学习过程我自感进步显著,后来我到美院附中后,二年级下学期在素描上出现的一次飞跃,一跃成为全班第一,这不能不归功于姨父的精心培养和科学的技艺传授。
还有一件对我成长影响重大的事情是全苏美展。对于油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该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是1957年,我刚开始跟姨父学画,上海举办了全苏美展。画展上看到油画丰富而逼真的形象与空间的塑造让我惊叹不已。那幅让我驻足良久的画是《列宁在全国水电化会议上的讲话》。
列宁在台上讲话,下面群情激昂,桌子、椅子、宽大的幕布,甚至群众中的吸烟者,那冒着青烟的烟蒂,画面上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的视线。那种色彩和质感让我激动,让我痴迷,我站在画前反复细看,直至闭馆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油画家。当时风行中国的苏联油画给我确立了这样的目标,要画画就要画这样的画。我热爱写实绘画。这是我心之所系,我决不会放弃它。
记者:那么除了前面您谈到的两位老师以外,在您的生活和学习中,还有什么人或事给您的印象最深刻呢?
徐芒耀:在中国美院上研究生期间的两位老师,全山石和王德威老师。王老师是马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高才生,当时为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全老师早年留学苏联,所以我们学习的路数仍然是苏派油画。苏派油画的特点是以色彩与素描的最佳程度的融合为根本,苏联画家造型能力强,他们中多数运用大笔触塑造。
大块大块的笔触在画布上的相交,往往会呈现出其不意的奇妙的色彩效果。所以苏派油画要求造型与色彩极具感觉的交融。尽管19世纪的俄罗斯油画是受到法国学院派绘画的影响,谢洛夫和列宾都曾多次赴法学习,但俄罗斯民族生性豪放且热情开朗,所以苏派油画不似法国绘画的那种典雅细腻,而是纯朴、厚实,更贴近民众生活。
全老师也很优秀,浙江美院很重视他,我们国家也很重视他,我十分敬重这两位导师。
学习期间,我在基础技能与创作能力方面有所进取,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一生难忘这两位恩师,不忘他们对我的栽培。还有我的一个法国朋友伊维尔,在学习传统技法上给予我很多帮助。
记者:您曾经到法国留学,这为您油画创作的发展及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请您简单谈谈相关情况。
徐芒耀:我刚开始接触触油画时,那时人们都说“可远观而不可近视”。到了法国以后,我发现,那儿的画远近都经的起看,为什么我们的油画近看就看不得呢?我喜欢欧洲的传统油画,但在法国极少有人了解传统油画技法,于是我做了大量的尝试。
法国是一个艺术比较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画风都可存在,没有人会干涉你。法国19世纪学院派绘画原作我看到后,顿时觉得这种手法更适合我。面多那些作品我心动,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当时,我通过博物馆里作品的学习,更多地去体味这些19世纪的传统绘画。
后来,我找到了伊维尔先生,他是一位法国幻觉写实派画家,他对传统油画材料很有研究,他曾经在中国举办过关于油画材料的学习班,很多中国画家通过学习都受益匪浅。
在巴黎美术学院,所有的学生都指定要修材料课。我没有修过完整的材料课,于是我就向我的法国同学讨教。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室里都有一个小工作间,学生可以随便在那里做油画颜料,为画布做底。因为法国的公立大学都是免费教育,所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工作室的绘画材料,学生是可免费取用的。
我在那里学到了制造达玛尔液态调色油、发光油与油画颜料等技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我今天能恰到好处地使用油画材料大有帮助,这一切是我出国之前一无所知的。
我选择性地学习绘画材料的使用与画面制作技术,经过反复梳理寻找最合适于自己的绘画风格与表现形式。鲁迅先生讲“拿来主义”,我很欣赏,但是拿来要消化。我在法国探索研究期间,画风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记者:1987年您创作了《我的梦》,这是您从巴黎回来以后的第一幅油画创作,它一举荣获了“首届全国油画展”金奖,自此您开始采用这种颇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表现手法。这是否与您在法国的学习有关?
徐芒耀:这很有关系。从法国学习到现在,我的绘画表现方法和思考与以前大不相同,画风变得更深入一点,更细腻一点,欧洲传统油画的味儿更足一点。《我的梦》创作构思形成时,我思忖梦中发生的事件不管是否合乎逻辑,在梦中都觉得真实可信,醒过来才觉得荒谬可笑,但梦已经结束了。
我在画面上制造荒诞比较节制,我要强调的是现实场景中瞬间突然产生的荒诞感。可以说《缝合》系列与《我的梦》是有共同点的,在这两个系列中我想探讨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我的梦》表现了人与坚硬实体的关系,而在《缝合》系列中,我是用绳子将人与人、人与物串起来,极具侵犯性的画面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当然这也是充分利用了我的写实技法,把这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在画面中营造出来。
而我画这个系列还有一种心理,也就是针对一种言论,这种言论认为,既然照相机已可以把我们眼之所见记录下来,那么写实的绘画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我正是要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幻觉和梦境是照相机无法捕捉的,但画笔可以记录,而且它从某一方面也表现了现代人生存的内在焦虑,甚至是某种真实中的荒诞。
记者:您这种风格的形成,皮埃尔•伽龙教授对您有很大的影响吗?
徐芒耀:现在绘画,太像了就不是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受到了马格里特和达利的绘画以及卡夫卡小说的影响。法国有位油画家叫巴尔丢斯,是位波兰人。我觉的他很有风格,我的画是有点像他,但我不可能从那里学到他那种风格。
我要的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我是把传统的办法、材料拿过来,这样,我的画就与19世纪学院派的风格很接近了。现在欧洲的画家批评19世纪学院派的画家,认为他们的画太完美了,我的看法与他们是相反的,完美为什么是缺点,完美有时也是优点,这个应该辨证的理解。
记者:那么您又为什么要做出今天的选择?是什么促使您放弃了这种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创作?简单谈谈您对自己艺术风格转型的体会。
徐芒耀:我的变化是必然的,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感觉。我突然感到,我是通过画面不断地在“生产”怪念头。绘画离不了思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我的思考,当想象力枯竭了,维持一种既有模式去不断制造是没有意义的。艺术创作要勇于探索,而勇于探索是建立在敢于放弃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要放弃一种自感成功的模式。
1991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再度应邀赴法,那对我创作转变而言也是一个诱发因素。从艺术史中我发现,无论是从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还是近代以来的一系列艺术变革,往往是由于视觉方式的变化而诱发了视觉表现的重大革命。
我不是说我个人就会在这样的探索中有什么巨大的发现,但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在艺术领域中,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前赴后继,不断挖掘那些崭新的视觉体验,并以此为基础扩大着视觉艺术的表现力,前辈们以他们的成果在充实着美术史。我想我应该努力在视觉方式上有所改变,有所突破。
记者:您作为一个艺术教育事业的领导人,您是如何看待教育态度的?
徐芒耀:在学生教育方面,我认为应该注意因材施教。一个艺术团体的领导,应该考虑学生的多样性,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非常同意毛主席的这个观点。“百花齐放”,群花都可以自呈美的一面;“百家争鸣”,什么是好的,让大家来选,什么艺术形式都可以存在,不可以不喜欢就打击它。我很敬佩邓小平,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才华,我们现在谁都不愿意看到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这样,我们才能丰富我们的绘画。
记者:谈谈您今后的艺术探索方向。
徐芒耀:人生命很短暂。前面二十多年探索,我在法国学习了几年,四十岁之后知道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不会轻易丢弃自己多年研究的积累,也许是年纪大了,想画得轻松一点,不可能像学生一样面面俱到。我会在画质量的提高上有新的探索。
也许我会将荒诞的成分进一步加强,或者尝试其他的视觉方式,比如从鱼的视角,或者以马的视角来表现观看,因为它们的眼睛是分在两边的。很新奇的想法。但追求新奇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时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平面的形式创造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以形式的不断创新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艺术终会有穷途末路的一天。
相比那些在艺术领域边缘开疆拓土的艺术家,我更愿意在油画的领域里,做得精深,做到极致。我愿意把这作为我的艺术追求。
徐芒耀——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1945年出生,上海人,祖籍浙江侗市崇福镇。197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文革后第一届艺术类研究生),师从王德威与全山石教授。1980年毕业后留油画系任教。
1984年由国家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学院选派赴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入皮埃尔.伽洪教授(Prof•Pierre CARRON)工作室研习现代具象油画。1991年11月至1993年1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法国,在巴黎国家装饰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1998年调离中国美术学院,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至今。曾在法、美、英、比等国及港澳地区与国内举办个人画展和联展,部分作品被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
1945年 生于中国上海。
1966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1980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
1980年 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获银奖。
1984年 至1986年赴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进修。
1987年 首届中国油画展,获金奖。
1990年 美国《芝加哥国际画廊邀请展》。
1991年 至1993年作为访问学者受邀赴巴黎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研修。
1995年 比利时《中国当代写实与後现代主义油画展》。
1997年 12月至1998年3月应法国CYAL色彩协会之邀前往进行学术研讨活动。
1998年 调离中国美术学院,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
2001年 应欧洲色彩协会诚邀出席色彩研讨活动。
2002年 8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国际造型艺术协会会员和世界华人造型艺术协会秘书长。
2004年 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特聘研究员。
2005年 加入中国写实画派创作群体,作品参加第二居中国写实画派画展。
2006年 作品参加第三届中国写实画派油画展为《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评委,油画作品《开模》参展为《全国小幅油画》评委。
2006年 出版《徐芒耀素描精品集》。
2007年 5月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从军为主任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签约,开始题为《新四军》的历史画(油画)创作。
2008年 参与中国写实画派大型赈灾义拍《热血5月.2008》巨幅油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