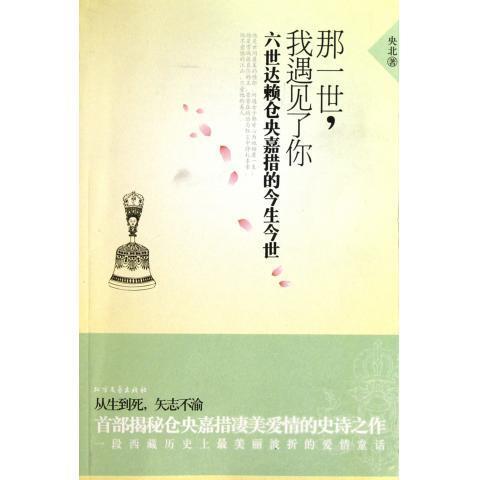洪烛的书 洪烛:和仓央嘉措结伴作一次人间的巡游(组图)
洪烛《仓央嘉措情史》(《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东方出版社
和仓央嘉措结伴作一次人间的巡游
—— 为洪烛《仓央嘉措情史》 写序
陆健
洪烛的新书《仓央嘉措心史》,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6千册之后很快售罄,不到到半年就三次印刷,说明市场需求旺盛;续写的《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仓央嘉措情史》,在诗人笔下又已完成,应是洪烛言犹未尽、激情再度燃烧之表现。这位当年的“文学白马王子”,腕力雄沉、出笔如戟,再度显示其不凡的才情。
洪烛的才情、毅力,熟谙问题之多样,在文学圈里素享其名。日有新篇,动辄万言,绝非浪得虚名。
2009年我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评委,为获奖作品、洪烛的《我的西域》撰写的颁奖词如下:
“洪烛是一位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作家,少年即有文名。20多年来笔耕不辍,新作迭出,且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质量水准线上,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的西域》是其近年游历、探访中国西部之后的一部力作,它的厚重、独特,主要基于诗人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对信仰、理想的重塑。
这于平民化立场的过度提倡引发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之现世精神状况无疑是一种反驳的努力,浸透着对自然和历史的尊重;二,集中体现了诗人细致绵密的创作思维特点。
敏感、敏锐,穿透力强,和西部的苍茫辽阔恰成对应。所以《我的西域》的成功,既是人力为之,又有某种“天意”;三,诗人对叙事元素与抒情元素的平衡掌控适当。故事不粘滞,颂赞得体——准确勾勒出了现代人的访古朝圣之姿、之态、之幽情。”。
《我的西域》是洪烛2005年参与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疆之行的结果。当时我也在那次万里行团队,感受新鲜亦有所悟,七天行程得诗十首,可洪烛令人惊愕地竟写出一部厚达数百页的诗集,其文思之敏捷可见一斑。
《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是洪烛2012年一次时近一周西藏观光访问引发灵感、时近一年写作的结果,诗情漫漶激荡,优美优雅,大气磅礴,无论题材的选取还是诗意的传达,都堪称一次文学创作的奇迹。
我也曾有过西藏圣地之旅,也曾拜读过《仓央嘉措情歌》,被那缠绵悱恻的诗句感染,触摸过那颗柔软温情的雪地里的热度,却终于一个字也没写下来。这是一种命运。我没有找到与仓央嘉措连接的通道,我不是那个合格的表达者。
现在看,当初我对仓央嘉措的理解是世俗的、狭隘的。我们对一个诗歌(文学艺术)题材的确具有选择权,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题材是否选择你。显然,洪烛来了,洪烛写了,洪烛把仓央嘉措内心的光明和苦痛的纱巾揭开了,让仓央嘉措再次来到人间,或者说,洪烛陪同仓央嘉措又作了一次人间的巡游。
这是一件神圣而艰难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次壮举。首先,仓央嘉措的定位问题。他是一位达赖喇嘛,因为种种原因被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安其位”,他化作一位“情圣”与一个世俗女子私会,最后郁郁而死。
这种做法显然犯了佛教大忌,因为他是作为转世灵童而继达赖之位,无法辞职,无法禅让,他不作喇嘛,就说明转世灵童的“不灵”,可被认为是“滔天大罪”。这是对藏传佛教教主位置传承的带有根本性的质疑,当然为教会所不容,必欲置之于死地。
仓央嘉措心里怎么想我们只能猜测,因为佛教自印度、尼泊尔传入,藏传佛教乃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的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体系。在印度,与佛教同源,甚至更早期的有奎师那大神,奎师那大神具有统摄宇宙的能量,他高于一切神,且是以无数种表象(面相)显现在物质世界中。那么即使是奎师那,以一个“情圣”的面貌出现于世间又何尝不可?
同时我们是否可以猜测,仓央嘉措“私会”的并非玛吉阿米一人,“玛吉阿米”其实是天下众生的一个代码?仓央嘉措是以挚爱“一个人”的方式来向所有人“布道”,来表达他对天下苍生的怜悯、恩宠、记挂?这正是一种更广博无私的为眼光相对短浅的教派人士、世俗政府所不懂所排斥的大襟怀、大爱啊!
我想,有了这些认知与联想,洪烛才能进入他的艺术创造。就像洪烛的创作谈所说:“仓央嘉措诗歌可作双重理解:既像写给女人的,又像写给佛的。既像情歌,又像道歌。我的《仓央嘉措心史》也追求这种效果。既像歌颂爱情,又像歌颂信仰。也许爱情本身就相当于一种信仰?也许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大爱?”(见《仓央嘉措心史》14页)
这本诗集的写作,采用了作者与仓央嘉措的双重视角。应该说这是最便于“达意”的视角。因为《仓央嘉措心史》书写的是仓央嘉措的心绪、情绪、心灵,是《仓央嘉措情歌》的内容和仓央嘉措尚未说出、尚未写完、尚未披露的东西,是《仓央嘉措情歌》的扩充与细化版。
需要向那位“情圣”的内心深处继续开掘,把“情歌”绵延不已的空谷回音继续回收,以当代读者便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进行演绎。当然,先要对作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大幅度提上,对自我的现世的情感世界进行净化,和仓央嘉措尽可能地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写作的可靠性才有可能。
这对于一个侧身于滚滚红尘、俗气冲天的生态环境中的诗人是困难的。洪烛“想象着自己就是仓央嘉措,正在苦等姗姗来迟的姑娘。”(见《仓央嘉措心史》)他做到了。殊为难能可贵。
为了避免两重视角的相互错位打架,避免读者在阅读中由于作者自我身份的时而“闪入”而产生“异物感”,洪烛多以仓央嘉措的口吻说出,把自己的身影尽量隐藏其后,效果颇佳。当然,作者身形不能彻底隐没,彻底隐没便彻底成了仓央嘉措的代言,使人产生错觉。适当地“淡入”与“淡出”加入了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这也是必须的。具体情景,大家可观赏《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此处不再举例。
《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语言亦可称道。时下多数诗人的诗歌语言,句式西化,节奏变化迅疾,以适应跳荡的思维与奇异的意象,体现其作品的独特性。洪烛的部分作品也是如此,如他的长诗《母亲》。
在《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中,洪烛的思绪推进是相对缓慢的,内容——故事、细节——的表述是徐缓的、层层递进的。其意象是“对生”的,如很多树叶的生长形态,如《如来佛》:“风来了,你没来,你没来却***来了。
风没来,你来了,你来了又***没来。水不在,山在,没有水,山再高也等于不存在。山不在,水在,只要水在流,你就与我同在。来一次,就不要空手离开,采一朵野花头上戴。如果连一缕香气都不愿带走,来一千次也等于白来。别人说你来过了,可我还在盲目地等待。等待也是一朵没有主人的野花,如果你不爱,没关系。它就自怜自爱。”
又如《佛的手里有什么》:“你希望佛的手里有果实,其实,只有种籽,把它种到土地里,才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你希望佛的手里有鲜花,其实,只有落叶。开始总是一瞬间,结局才意味着永恒。你希望佛的手伸向你,其实,伸向每一个人。即使长出一千只手,也满足不了你的索取。你看见佛的手空空如也,其实,没有才是万有。你看见佛的手里有什么,都不是佛所有,而是别人的寄托。”
妙手偶得的还有这首假托智者之口歌颂美女的《先知与无知》:“别人把我叫作先知,遇见你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人,怎么造出来的?真说不清楚。你也把我叫作先知,离开你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么美的人原来也是一个梦。谁造出了这个梦?真说不清楚。我把自己当作先知,梦见你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是梦见了你呢,还是梦见了一个梦?你是一个人变成的梦,还是一个梦变成的人?”
这种情况在《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诸多篇章中屡屡发生,近乎一种“常态”。我们细细思考、打量,是否还有比这更适合于这部著作的内容表现的语言?答案是可能没有。
其来源、出处,往远处寻,《诗经》有之,如“罗敷”篇;如“鱼游池之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桃夭》)。
向近处找,从洪烛的作品中找,《我的西域》中不乏其例:“那是女人胸口的雪山,雪水化作乳汁,浇灌远处的沙漠。那是哺乳期的雪山,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婴儿,想起那种早已遗忘了的渴。是的,每一个婴儿的舌头,曾经是一片最小的沙漠……”
《我的西域》证明着洪烛的文学雄心:“我要骑一匹已绝种的马:汗血马,去当代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西域,见一个浑身沾满花粉的人:香妃。请她教我如何与蝴蝶打交道,如何酿蜜,或如何炮制一味比中药还要管用的香水……”这种雄心又通过《仓央嘉措心史》发扬光大。洪烛,从“我的西域”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我的西藏”。
由此似乎可归纳为,《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语言表达是其内容所要求的,是诗人洪烛在以前的创作中操练成熟的语言。调整心态、选取题材、精耕细作,在重要的作品中达到自己艺术创造的极致。
我相信《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的写作,就是洪烛向自己的写作能力极致的一次挑战。他使我们看到一片成功的炫美辉光,同时预示着更大的可能。
当然,按照文章惯例,我们似乎也要给挑些毛病出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洪烛太能写了,文情英迈,他的脑袋里的开关好像极其灵敏,稍稍触动便文思泉涌。似乎他从仓央嘉措几十首诗歌中延展出来的文字过多了,有点要“尽其欲言”了。
仓央嘉措作品的最耐人寻味处在于我们听到他文字结束后那空谷回音的“回音”,是文字之外的东西,并且那回音是一种回环着“向上”的音频,向着天空空旷处。洪烛的文字在距离我们头顶比较近的地方似乎还可以“回环的时间”再稍短些。诚然,这绝对是苛求,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他有着更高、再高的企盼。
长期以来,洪烛是我的一个榜样,日磨夜砺,大江湍流,水滴石穿,就像诗人评论家李犁评价的,他像“一个活着的诗歌烈士”。我曾写诗《钉子户洪烛》以赠,如下:
“洪烛放出话来/作定了文学的钉子户/即使四面坑坑洼洼/开发商的眼睛吐出蛇的信子/他也不搬迁/他白天在农展馆的/那个中国文联大楼里办公/回家他飞快地跳上电脑/写诗、畅销文化读物,经营博客/创造三千万个点击率/他写《我的西域》,就真的/背个双肩包,一路往西/停下来,径直铺开那/让人嫉妒的食欲,在饭桌前/埋头苦干,风卷残云/然后一边走一边/在小纸片上勾勾画画/从喀什回来,我写了10首诗/他写了400首/ 牛!
他是怎么和成吉思汗/结伴同行的?“月亮背面的荒凉”/ 独一份给他去畅游?/
洪烛是个独行侠嘛,什么灵感啊/美女啊,从来不跟朋友分享/假如他的脸上出现阶段性朗润/那准是他的邻居有了艳遇/“洪烛兄弟,有没有结婚打算?”/ “随缘吧!随缘吧!”洪烛的笑/ 是那种无辜无奈加一点无所谓/的笑。他的文学野心,从不昭昭/像推土机一样干活/洪烛——钉子户、殉道者、炼金术士/非把自己的骨头炼成钻石不可/真炼不成,也得炼成一块结石。”
佛祖圆寂,留下了舍利子。而结石,我愿意理解为我们凡人的舍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