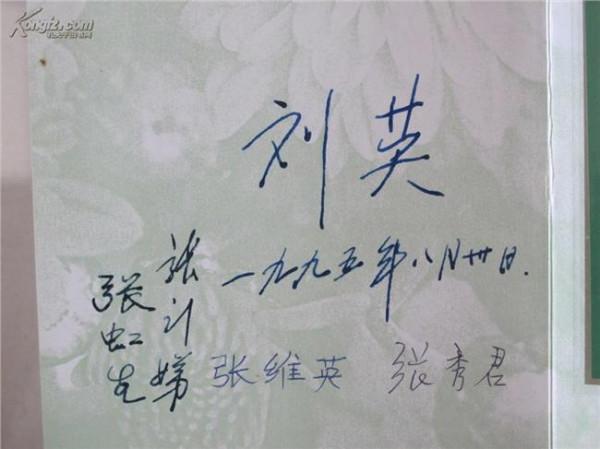刘立福评书画皮 评书《聊斋志异 画皮》(上)
山西太原府某县,有位姓王的,是个秀才。这位秀才是长兄,有个弟弟,人们都叫他们王大郎、王二郎。哥儿两个也不过就差个两三岁。这位王大郎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王二郎呢,也不过就是二十一、二岁,哥儿俩全都娶了媳妇儿啦。二郎的媳妇儿娘家姓什么,咱们不知道,这王大郎啊,娶妻陈氏,是一位贤慧的女人。
别看王大郎是个秀才,广人性可挺糟,怎么糟呢?最喜欢追女人?走到街上,只要瞧见有个美貌的妇人,或者是姑娘,他必须要评头论足,满嘴里头胡说一气!别管跟谁走在一块儿,就说:"兄弟,你没瞧见?前边过去这女人多好!
啊,你看,身量儿,模样儿女可惜就是一样儿,脚大一点儿!"其实,人家脚大脚小可碍着你什么啦!他的品行虽然不好,可是他媳妇儿陈氏为人很好,多少也识些个字,知书懂礼。为了自己的丈夫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只要是夫妻俩坐到一块儿呀,没有短了劝他,劝他怎么样!
他不听啊!他不但不听,瞅冷子还跟太太瞪眼:"得得得,别说啦!你这嫉妒都出了奇啦!一提起来,就是这件事情,一提起来,就是这件事情,我的行为不好,与你什么相干?没缺你吃,没缺你穿,不就完了吗?你天天儿唠里唠叨,你唠叨什么?你!"碰巧喽就许把陈氏打一顿,威吓一顿,就因为这个,夫妻二人常常拌嘴打架。说什么大奶奶也打不过拌不过他呀!只好就是忍着。
再提王大郎的兄弟王二郎,您别瞧哥儿俩是一母所生,"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呀,同大郎的性情是大不一样,为人极其忠厚老实,一点儿不对的事情,人家也不作。哥哥的所作所为,二郎一点儿也瞧不上。亲弟兄,他有这些个不好的行为,是不是应当得劝劝?劝他,他也得听啊!
你跟他一说,他把眼一瞪:"你不用管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做这事情不好,不好碍不着你!"几句话就把二郎给噎回去啦!气的二郎常自个儿在自个儿屋里头掉眼泪:"怎么遇见这么个哥哥!
所作所为,一点规矩的地方儿没有,说劝劝他吧,他还拿出作哥哥的派头儿来申斥我!这怎么办?遇见这么个哥哥怎么办!"幸而自己的太太呀,人也挺好。劝解:"得啦,虽然是亲弟兄,说着听呢,更好;不听,也只好慢慢的劝解吧,反正咱们说过啦!
"日子一长,二郎不愿意再受哥哥的这种委屈,跟自个儿的太太一商量:"咱们搬出去吧!我实在没法子跟他一块儿住啦!这是咱们自己在屋里说,别的不可惜,可惜咱们的嫂子,挺好的人给了他啦!
你说,你能指出咱们嫂子哪点儿不对来!一派正气,规规矩矩。对咱哥哥,说也不听,劝也不听,一来一瞪眼,分明是他的理由不对,嫂子的理由对,我要说几句稍微有点儿护着嫂子的话呀,他还回话来,能够把嫂子臊的恨不能要自尽……""那么怎么样?""干脆呀,咱们搬开!
决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住啦!"二奶奶一听:"这话可也对!挺太平的日子,为劝哥哥,三天一抬杠,两天一拌嘴的,挪开呀,也好!
"二奶奶同意了二郎的办法。先跟嫂子说说,嫂子没有意见:"那也很好,省得让兄弟跟他生这些个闲气!"跟大郎一说,大郎这么一听啊:"噢,打算要跟我分家,行啊,分家就分家吧!你翅膀不是长硬啦嘛!
好,单过就单过!分,咱们就分!"大郎一点头,二郎马上跟他定日子分家,立好字据,哥儿俩一个人一处房子,一人几十亩地,虽说分了家,吃喝也都不算为难。分家之后,哥儿俩还住在一条胡同儿里,大郎住在偏着东边一点,路北。二郎呢,偏西边一点,路南。相离着也就是两三个门儿,俗语儿就叫斜对门儿啊。从这儿,就算各过各的。谁不碍谁啦!
单说这位王大郎同几位朋友公立了一个文社,为的是没有事的时候,大伙儿都凑合在一块儿说说讲讲的。有一天他在文社聊来聊去,聊的天不早啦,少说也有三更天左右啦!"吓,这天可不早啦!自己只顾得撒开了一通足聊,闹的这么晚!
明儿见吧!明儿见吧!"有在文社里住着不走的人,就说:"别走啦,热热闹闹地在这多聊会儿,索性在这儿住下,天亮再走得啦!""不不不,我得回去!好在我离家不算十分远。"王大郎出了文社,正赶上大月亮天儿,通亮通亮的。
他回家这条路是东西的道,两旁边不是坟地就是树林子,他走着走着,忽然间这么一抬头,噫?就见由起大道的北面儿,从一个小岔口儿里出来了一个女人,走道儿一扭一扭的,似乎已经走不动的样子,手里头提溜个包袱。
她走出来往西一拐呀,还往前走。王大郎在她后边儿呢,相离着也就五十来步远,在后头瞧着她后影儿,心想,我可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个姑娘啊,是个媳妇儿?瞧她这身子倒挺窈窕的,可不知道她的相貌怎么样?这么办,往前赶一赶,看看她到底长的什么样儿?心里想到这个地方,把脚步放快,往前就追。
噌…赶到窜过这个女人,顶这么两三步远啦,回过头来趁着月光这么一瞧,吓!别提够多么好看啦!是个少妇,顶多也就是十八九岁,手里头提溜一个包袱,走的慌里慌张的。
看明白啦,把自己的脚步可就放慢啦,就在人家后边儿走啦,离着不怎么远。一边儿走,心里头一边儿嘀咕,哎呀,说话这天可就顶四更啦!你说一个年轻的少妇,也没有人跟着,哪怕你骑个小驴儿呢!
连个小驴儿都没有。这是上哪儿去哪?是由婆家上娘家呢?还是由娘家上婆家呢?年轻轻儿的,一个人走黑道儿,这事情怪啊!这个妇女一边儿走,一边儿往旁边扭脸儿,左瞧瞧右看看。不用问啦,多一半儿是个私奔的妇女!
看这样子可象!哎呀,长的可真好啊!她要是个私奔的妇女啊,这么办,我赶过去一哄她,就许能把便宜哄到手。能够吓唬她的地方就吓唬她,能够哄她的地方我就哄她。对,就这么办!心里想到这个地方呀,把脚步放快,又窜到人家前边儿来啦!
窜到这妇女的前边儿有两三步远的工夫,走着好好儿的,瞅冷子这么一回身:"哎,这位大嫂,您请留步,请留步!"这女人吓一跳,紧跟着人家就站住喽:"你有什么话说吗?""是,我问问您哪,天都到了这么晚啦,您也没有坐车,也没有骑着牲口,独自一人打算到哪儿去呢?""这可奇怪啦,你也是个走道儿的,我也是个走道儿的,你过来这么冒冒失失地问我!
唉!我要有什么忧苦之事,你能分忧吗?你能给我解愁吗?既不能给我分忧,又不能给我解愁,你是什么意思哪?""噢,不不不!
大嫂,您可别那么想,平素有这么句话呀:世上的人哪,就得管世上的事。我也不敢说我是一片好心,您看,这地方儿除了树木,就是坟莹;也别管您这是由婆家上娘家去,也别管由娘家上婆家吧,保不住呢,就许找不着道儿啦!
天这么晚,您的心里头能不害怕吗?您提提您的婆家或是您的娘家在哪儿住,我任什么事没有,我好送您一程啊!把您送到娘家也好,或是把您送到婆家也好!大嫂,我这是一片至诚的苦心,我……我这是为您着想,大嫂,您可不要多心!
""噢——"这个女人点了点头,又端详了端详这位王大郎。"咳!要提起我的事情来呀,不管谁听见哪,也得替我难过!
""是的,是的!大嫂,您这不是还没说哪吗,我就觉乎着有点儿难过啦!您可以谈谈,谈谈!""唉!跟您这么说吧,我苦死啦!我娘家爹爹,在我幼小儿刚一懂事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去世啦!不怕您笑话,我们是个贫寒人家!
我就是一个娘,我这个娘对于我……就因为日月不强,没吃少喝,好狠的心,她贪图人家的银钱,就把我给卖了!买我的这个主儿,是个趁钱的人,花言巧语把我哄过来之后,一点儿都不知道疼人!
这还不算,尤其是他大太太对于我……唉!谈起来,就叫人心里难过!每天价,黑下骂完了,白日骂,白日骂完了,黑下骂,骂上了气,瞅冷子过来乒乓打我一顿!就这么过下去,大爷,我这个人非叫他们生生给折磨死不可!
实在受不了啦!我也不怕您笑话我,得了便,我就偷着跑了出来,您算,一个偷跑出来的女人,敢在白天走吗!要让他们给追上,我还活的了啊!""哎哟,啧!咳!这么说起来,原来是受苦受难的一位大嫂!
哎呀,太残忍啦!这么好的人,他就忍心这么样蹂躏您!大嫂,刚才您已经谈过啦,爹娘是没有喽,真格的喽,就没有个三亲六故吗?您要有个三亲六故,婶娘家呀,大娘家呀,或者是姑姑家,要不然是姨家呀,您想一想,在什么地方儿,您指个地点,也甭管是离这儿远近,也甭管我跟着受多大的累,救人救到底嘛!
我把您送到亲戚家去,省得您哪在外边儿这么漂流着!""咳!听您这么说,可能是刚才我跟您说的这话您还没听清楚,没告诉您吗,三亲六故一概都没有啦嘛!
""什么样的亲戚都没有?""没有!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别管我死在什么地方儿,也比让他们把我折磨死强的多呀!""噢,大嫂,说起来可真是太苦啦!"您别瞧王大郎嘴里这么说,心里头哇,蹦……一通儿乱蹦,这份儿高兴啊!
哎呀,嘿!这便宜算叫我捡着啦!这个人算归了我啦!行,亲的近的一概没有,行,哈哈!再跟她一套弄啊,碰巧就许行了!脑筋这么一动,嘴里头跟着就往外说:"大嫂,亲戚也没有,连个至近的朋友也没有,真叫是苦哇!
这个……大嫂,要不这么办,您哪……您哪……这个这个……哈哈!
哈哈!大嫂,您说这……""这位大爷,瞧您这样子,您一定是很慷慨的人,您既想救我的性命,有什么话您就直接地说出来吧!""是的,大嫂,我不敢冒冒失失说,大嫂,人心隔肚皮呀,作事两不知,我说出我这个打算来,假如大嫂您要是信啦,知道我是个好人,知道我这是诚心诚意救您,这还好,假如您一多想,我这份儿好心可就当了驴肝肺啦!
""哎呀,这么一说起来,您有顾虑?""对了,对了!
我顾虑的就是这个地方儿!""您可别看我岁数儿小,我可不是胡里胡涂的妇女,您为我着想,诚诚实实的救我,我哪儿能够把您错想哪!有什么话您只管直说吧!""哎,是的,是的!
幸而……哈哈,遇见大嫂您这么个明白人,稍微胡涂一点儿呀,这话简直我还不敢说。刚才我要说什么呢?大嫂,我要跟您说这个,您看,您看,就由起脚下说,往前再走,走不了多远,就到我家啦;天呢,己经这么晚啦,您脚也不大俐落,再说走了半夜也累啦!
您……您不如跟着我……到我家里去休息一晚上,顶到明天哪,您慢慢儿地想,也可能想起来您远一支的,也许还有个亲戚,或是再远一支的,也许有个本家,只要您一想起来,别管离这儿有多么远,我一定把您送到您的亲友家。
啊,大嫂,我是这么个打算,可不晓得您的想法儿怎么样?""哎哟,这么说起来,您可真是一位诚实的君子!
""哎,那您太夸,您太夸我啦!君子这两个字我虽然不敢当,可我的确是个好人!日久天长,您慢慢品……""这么说起来,叫您分心受累啦!我这么亡个孤苦伶仃的人……我这儿谢谢您啦!
""啊,不不不,不客气,您甭客气!好吧,大嫂,咱们走吧!我给您拿着包袱,您拿着怪累的!""不用,也没有什么要紧东西,我自己拿着吧!""好吧,好吧!"吓!
王大郎心里头蹦……一边儿跳哇,一边儿心里想:哎哟,想不到哇,这样便宜事,楞会让我给赶上啦!行,这就顶九成儿啦!我拿话再稍微一引导她,就得上我的圈套!心里这么想着,高高兴兴地,没有多大工夫儿,就来到王大郎的门口儿了。
到门口儿,用手一推,街门就开了,虚掩着呢。怎么?家里头归里包堆就是他太太跟一个老婆儿,没别人,连他才三口儿,住的又是两个院子,她们住在里院儿,北房,前院儿有东房,西房。他出去的时候,有个回来的早,有个回来的晚的,这街门呢,也就虚掩着,一推就开,为的是方便。
王大郎推开门进来,往旁边一闪身:"大嫂,您请吧,您请吧!这就是我家!"紧跟着这女人就进来啦!他回身把门推上,慢慢儿地把牵关儿牵好了,该顶的顶上,该锁的锁上。全都拾掇好啦之后,就奔东屋来了,这东屋是里外间儿,王大郎先进到屋里,在桌子上摸,摸着火纸笸箩,敲石取火,吹着了火纸,把屋里的灯点着了。
这女人跟着也就进来了。先找个地方儿,把她提溜的这个包袱搁下,往两旁边儿瞧了瞧,这王大郎笑嘻嘻地,那份儿殷勤就甭提啦:"大嫂大嫂,您请坐吧,够累的啦!
再说脚也小…… 坐这儿,快坐这儿歇会儿!""哎哟,我瞧这样子,这是前院儿吧?""对了,这是前院儿书房!""您这后院儿谁住呢?""后院儿……这后院儿是……是这个……哈!
后院儿是我的内人在那儿住!""噢,您有太太!""对……对了!
""那您不把我带到后院儿去,带到这屋里来,这是怎么意思?""不不,我这也是为您着想啊!……我们贱内常常地好串门子,嘴不严,她要知道我把大嫂陪到家里来,她就当作一件希奇事情啦!
保不住跑到街坊家,张家长、李家短的这么一说。人多,嘴就杂有呀,往外一吵嚷,传来传去就许传到您家里去。到这时候儿这个祸呀可就大了!我,我是好心,我不怕,我为了救人,说到哪儿去,我也有理!可是大嫂,要把您弄回去,您想,能够轻饶了您吗?没有这个事,还天天打、天天骂哪!
一有了这个事,您得受多大的痛苦哇!我不是为您着想吗?为了这个,我就没敢把您陪到我们后头去,不敢让我们内人知道!""噢—— 您想的真是太周到啦!
""那是您夸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哇,未曾办事得防备后来。""是的,我也没个亲的己的,但分儿有个亲的己的,我不也就投奔到那儿去了吗!幸而遇见您这么一个仁德的君子,把我带到您家里来。
唉,这么一来,不定得在您这儿叨扰多少日子哪!""那没有关系,您住多少日子我都乐意,这么说吧,反正我对您决不变心就是啦!""今后常年的在府上叨扰您,穿您的衣,吃您的饭,我也有点儿居心不忍……恩……我打算……我是打算这个"说到这儿,这女人脸上一红一白的,羞羞答答。
王大郎这么一瞧,心里头蹦……又这么一通儿乱跳,心说:有边儿!
行啦!大功已成!这女人说,"大爷,我跟您说出这句话来,您可别笑话我……您要是不嫌弃我呀,我……我打算给您……给您作个偏房侧室,您……""嘿……哈哈!"书要简言,这位王大郎今天就在这屋安歇了!
一连就是四五天,俩人吃在这屋里吃,喝在这屋里喝。吃饭的时候儿,她是不是自个儿上厨房做饭去?是她做饭去。她拿准了这个时候儿啊,容老婆子作完了饭啦,伺候太太吃去啦,火也腾出来啦,她赶这时候儿来,快快儿地一做,做得啦,偷偷儿拿回屋吃去,就这么着又过了好儿天。
这家里头,太太连前院儿都不去,说不知道还可以,外头院儿屋里头多了一口人,这老婆儿能不知道吗!俩人在这屋里说话的时候,能够净小声儿嘀咕吗?绝不能够吧!说话声音一高,保不住就让老婆儿呀见啦!这老婆儿一注意呀,好!
仔细一看,咦!嘿!我们这位大爷可真有两下子,这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呀!啊?瞧样子他们俩非常的亲密、亲热,这老婆子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陈氏啦:"太太,报告您一件事情,可了不得啦!""哟,什么事呀,你这么大惊小怪的!
咱们家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唉呀,太太!也不知道咱们大爷从什么她方儿勾了一个小媳妇儿来!长的这个漂亮啊!看样子大概到今天哪,怎么也来了顶十来天啦!"陈氏这么一听,当时就把脸气白啦,哎哟!哎呀!大郎啊,大郎!怎么劝你,你是怎么不听啊,你这种行为也太难啦!唉!长叹了口气,当时又把火儿压了下去,没理这茬儿!
又过了两天,王大郎到陈氏屋里来啦,进屋来,沏了碗茶,坐在旁边儿喝茶。这位陈氏可实在憋不住啦:"你既来到我这儿啦,夫妻嘛!我看出这是利,我就告诉你这是利,我瞧出这是害,就得告诉你这是害,利害要分明。真格的啦,可惜你念过那么些个书,你怎么连利害都分不清呢?"说到这个地方呀,这陈氏才问他:"我问你件事!
""什么事?你说!""前院那个女人在咱们家住了几天啦?""啊……""这个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啊……""你为什么始终不告诉我呢?"王大郎到这时候也不能不说啦:"她是这么回事,我呀,为了救她!
那天,定更来天,在道儿上看见她啦!拿着个大包袱,据她说呢,她是受不了大婆儿的打骂才跑出来的,她说的挺可怜,人有侧隐之心哪!
故此我让她在咱们家住下啦!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唉!你想黑夜之间,天才定更,她一个女人家,从天黑到定更能走多远?可能就是咱们方近左右的人,既然是方近左右的大户人家的姨太太逃跑出来,还拿着一个挺大的包袱,那包袱里头不是金银就是珠宝,人家家里头人也丢啦,金银珠宝也丢啦,人家能不找!
纸里头还包得住火吗?万一叫人家家里人得着信啦,说在谁家谁家哪,人家找了来,把你一告,你又是个秀才,作出这种没理的事,难道说就不惩治你的罪名吗?到那个时候,咱们寒碜不寒碜哪!
啊,要是依着我说呀,你可别想我这是嫉妒,赶紧把她打发出去,她爱上哪儿上哪儿。
再说,你知道她是好人是坏人哪,万一要是坏人呢,咱们不是留下祸害啦!"王大郎不但不听劝,倒火儿啦:"这事情啊,干脆,你少管!"良言难劝异心人,忠言逆耳啊!他要是个好人,作错了这么一点儿事,您拿好话这么一劝他,忽然悔悟:对了,人家为我!
他还很感激你,说你劝得对,这是真正的好人。这个王大郎,你跟他说这种话,他听不进去呀!不但所不进去,他说出来的话呀,别提多难听。把嘴这么一撇,眼睛这么一瞪:"得啦,得啦!
嘿!我呀,很佩服你,太太,惹出祸来我顶着!你这不叫多余吗,你少说这些个!"他一边叨唠着,一边站起来,一甩袖子,从屋里出来啦!陈氏也没办法,心里说,你呀,糟吧!反正我说这些话完全为你,谁叫咱们是夫妻哪!别说是这么些年的夫妻,就是一日的夫妻吧,我也不能不管你,听不听在你吧!再说王大郎,从陈氏屋里出来,心想:哈!你这不是嫉妒吗?从这儿起,我不上你屋里来喽!把陈氏的金石良言,完全当耳旁风啦!
横是又过了这么个三五天啦,这天吃完了午饭以后,王大郎感觉着浑身有点不合适。象是病了似的,想出遇溜达溜达。出胡同儿,往南,走出来也不过就是几十步,走着走着,忽然间由南往北,来了一位老道。可有年岁啦!光着头,没戴帽子,绾着一个发绾,头里这儿早都卸了顶啦,四方大脸,寿眉多长,一部的白胡须飘散胸前,脸上红中透润,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穿着一件半旧的道袍,两只高腰袜子,穿着两只双道梁儿的洒鞋,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
看样子真是仙风道骨哇!王大郎正跟这位老道走了个对脸儿,老道瞅冷子一抬头哇,瞧见王大郎啦,人家把拂尘这么一抖,"无量佛!"这位老道单掌稽首,一念无量佛,王大郎就一楞,是跟我有话?刚这么一瞧,这位老道一伸手:"这位先生,您稍微站一站!
""噢,您有话?""对了,对了!""您有话请讲吧!""哎呀,咱们素不相识,不过是在这儿偶然相遇,我既看出来啦,就不能不谈哪!""是是,您要说什么?您看我有什么不相当的地方?""不是别的不相当,我看着阁下,面目之间,有一股煞气,必有妖物缠身!
您这些日子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可以跟我谈一谈。""啊……噢,哈哈!"要遇见年轻的老道,冲他这么乐,人家就许躲开啦。
怎么?他这种乐法儿不是好乐呀!王大郎心里想什么呢:来啦!当老道的惯会来这一手儿,瞅冷子猛古丁的碰见一个人,就拿话吓唬他,你有这个吧,你有那个吧,你有什么什么奇遇啦!这是想借事生端,不是要给我念经,就是要给我作法,想法儿蒙钱啊!
甭弄这一套!王大郎想到这儿,就冲老道一阵冷笑,人家老道那么大年岁能不懂!老道也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哈哈!先生,你这一笑,我也明白,你把我当作世间蒙事的老道啦,是不是?""不不不,您哪,也是好意呀,可有一节,我没有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情!
再说,我还是个秀才,哈,非理之事,我决不敢作!道爷,您就不必多想,我谢谢您哪,您受累!""哈……" 俩人从这儿一分手,王大郎往南,老道往北,刚一转身儿,才走了两三步,王大郎就听老道自言自语念道:"唉!
可惜!可惜这个人哪!死在眼前还不醒悟,真正是奇怪哪!"王大郎一听,心里一哆嗦:死在眼前还不醒悟,不用说,他是说我,刚才他说我有妖物缠身,还打算要给我降妖捉怪,我一阵冷笑把他给驳了,故此他才有这种话!
恶鬼?可哪儿有恶鬼哪!是不是我带到家去的这小媳妇儿是个恶鬼?这……不能……决不能……哪儿有这么体面的恶鬼呢!
老道的话叫人纳闷儿,万一她要是个恶鬼可怎么办?……对,这么办,我到家里偷偷儿进去呀,想法儿偷偷儿看看她有什么动静。想到这地方儿,走起来可就快啦,噔……放开大步,往家里这么一通儿跑。
来到自己家门口儿,上台阶儿,拿手一推门,门关着呢!找根棍儿拨了半天,也没拨开。大晴白日的,里边上上锁干嘛呀!"开……"刚要嚷开门,又一想:使不得!我打算偷偷儿地瞧一瞧嘛,要大声儿一喊,叫她听见,她出来给我一开门,不什么也瞧不见了吗!
这怎么办?想了半天,王大郎往旁边一瞧哇,右首墙底下有一个狗洞:得,从这狗洞钻挝去吧!钻了半天,蹭了一身脏东西,好容易挤过来啦!过来之后慢慢儿慢慢儿的放轻了脚步,直奔前院儿这屋来了,来到屋门口儿这么一瞧,心里说:怎么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啦?这个呀我非瞧瞧不可!
把脚步更放轻啦,悄儿悄儿地走到窗户跟前。来到窗户跟前,用手蘸唾沫抠开一点儿窗户纸,闲一只眼睁一只眼,顺窟窿眼儿这么一瞧,可把王大郎给吓坏了!
怎么回事?可要了命啦!那位漂亮的女人没啦,就在窗户里头站着一个恶鬼。高里下,足有一丈多高,红头发,蓝靛脸,睁着对大铃铛眼,咧着个大嘴,龇着大牙!这只手哇,捏着枝画笔,床上头搁着一个颜色碟儿。
不用问,什么画笔呀,碟儿啦,碗儿啦的,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是那包袱里头包来的!就见它一骗毛腿上了床,左手按着什么,右手就拿这笔呀,袜点颜色儿,在这儿画人皮哪!
就在床上铺着一张美人皮,就是那小媳妇儿的样子。左画画这儿,右画画那儿。画着画着,把笔搁下,紧跟着把颜色,碟啊,全都拾掇起来搁在一边儿,拿手这么一伸哪,把他画的这张美人皮就提溜起来啦,象抖落衣服似的,叭叭这么一抖落,把皮披在自己身上,披在身上之后,眼瞧着,忽——这么一下儿,身量儿就矮下去啦!
再这么一瞧哇,还是挺漂亮的这么一个小媳妇儿!拿手捏捏左边的脸,捏捏右边的脸,拿起桌儿上搁着的镜子,左照照,右照照。
这个时候,王大郎在外头哇,吓的差点儿没咽了气!打算转身要走,不成啊,站不起身儿来啦!腿肚子直转筋!怎么办?爬呀!慢慢儿往前爬,爬,爬,好容易才爬到刚外狗洞那儿,一边儿哆嗦着,一边儿从狗洞又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