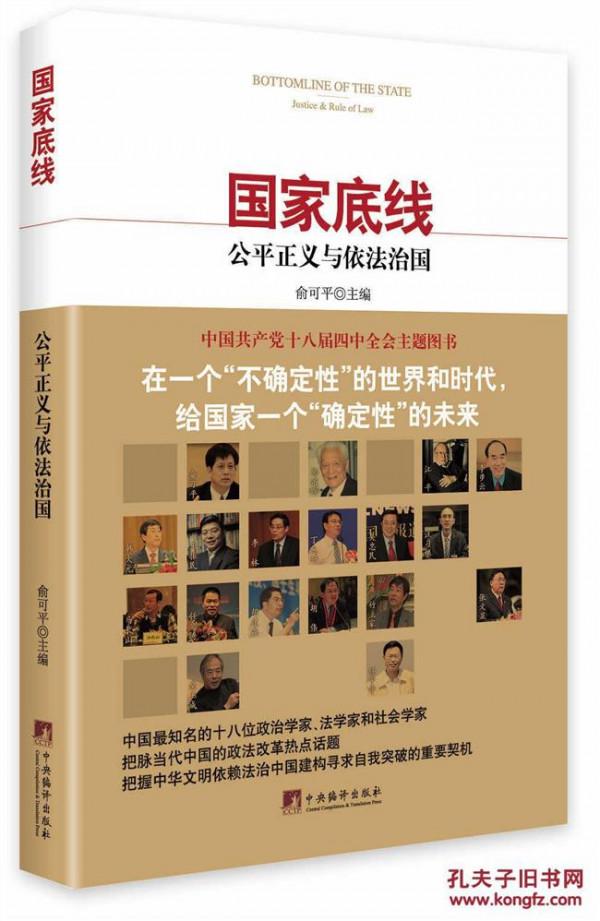葛兰西国家 论葛兰西与新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
尽管对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对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消亡作出过大量的论述,但马克思并没有创建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多由一系列片段的、不系统的哲学思考、当代历史分析、报刊文章、偶发事件的评论组成。
[1] 以至于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列菲弗尔评论道:“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2]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这种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在研究领域中显得相对沉寂。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有了根本改变。
以两位政治理论家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的争论为契机,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兴趣,并由此引发了国家理论的三次复兴。[3] 在此进程中,葛兰西的思想得到了重新发现和激活,或者说葛兰西写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著作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葛兰西到新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展开、验证并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解释力。
一、葛兰西的国家理论
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凌驾于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强调市民社会(体现同意功能)凌驾于政治社会(体现暴力功能)的重要性。在葛兰西看来,制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力量,而在于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世界观”的接受。因此,问题在于统治阶级如何取得从属阶级的赞同,从属阶级又如何才能推翻旧秩序,建立人人都能享受自由的另一种秩序。[4]
艾伦·伍德指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武器,“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标示出了斗争的新领域和新形式,它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不限于针对它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指向它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5] 迈克尔·哈特也认为,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的民主方面都集中在市民社会的多元机制,以及这些机制为政治社会亦即国家的统治提供的输入渠道或途径上。[6] 因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观不同,葛兰西不再将市民社会限定于经济基础领域,而是将之归于上层建筑领域。
市民社会所包含的“不是‘所有物质关系’,而是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生活’,而是整个精神和智识生活”[7]。博比奥认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这一界定,主要受惠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在《法哲学原理》中,作为直接伦理分解环节的市民社会包括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对所有权、人格等的保护;以及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述两个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不仅包含经济关系领域,而且还包含它们自发的或自愿的组织形式,即法治国家中的社团及其最基本的规章制度”[8]。
基于这一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葛兰西同时拓展了对于国家的理解:国家既是统治阶级权力扩张的一个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弱化和瓦解从属群体的一个强制力量(政治社会)。[9] 国家不仅仅是暴力机器,而且还包含了文治教化。
葛兰西指出:“对国家的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 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领导权)。”[10]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具有整体意义,它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政治社会,它经常被规约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机器,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其二为市民社会,包括教会、工会、学校等各种组织和公民生活中的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也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政治社会实施的是直接性的强制性权力,而“‘市民社会’是一个进行旨在获得整个社会舆论的意识形态—文化的或伦理—政治活动的地方”[11],通过知识和道德等手段,取得对大众的思想意识的领导权,从而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大众的自觉服从上。
①
与列宁主义意义上视政治领导为领导权的本质要素不同,葛兰西更偏向于智识与道德领导权。[12] 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不仅包含统治阶级通过他们的智识、道德和政治领域的实践对被统治阶级“积极同意”的动员,其中包括系统考虑大众的利益和需求,也包含必要时在次要问题上作出妥协以保持支持和团结(但不会牺牲根本利益),即通过建立和再生一个集体意志、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来确保智识和道德的领导。
此外,正像暴力因素是制度化于一个镇压机器体系中一样,领导权也结晶于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机器体系并以此为中介。
事实上,尽管它们肯定发生于政府系统,但是领导权的行使在其狭义上大多数出现在国家之外。葛兰西认为,首先,它们出现在市民社会或者被称为私人的领域中,比如说教会、工会、学校、大众传媒或政党;其次,它们被知识分子转变为现实。
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阐述意识形态、教育人民、组织和统一社会力量并且保证统治集团的领导权。[13] 因此,葛兰西认为,不能将国家仅仅等同于强制性机器,也不能将国家职能仅仅规约为暴力职能,“国家具有教育和塑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使‘文明’和广大群众的道德风范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继续发展,从而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新人类”。
“市民社会无须‘法律约束’或强迫的‘义务’就能运转,但是照常可以带来集体压力,并且通过风俗的演化、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道德风尚等产生客观效果。”[14]
考虑到葛兰西写作和思考的特定历史背景、如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在1920年的失败、俄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美1929—1932年经济危机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科技变革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多重影响[15],我们有理由把葛兰西对国家及其领导权的独特理解与苏联以及西方发达国家革命道路的探索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密切联系起来。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
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16] 在葛兰西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展,俄国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发育成熟,其统治主要还依赖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的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
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它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候,才发觉自己仍面临有效的防御工事”[17]。这意味着东西方的革命策略应该是不同的,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国家应该是正面攻击的目标,在发达的西方社会,正面攻击的目标应该是市民社会。
借用葛兰西独特的表达方式,上述第一种攻击可以称之为“运动战”,即集中力量在瞬间打开统治集团防线的缺口,使革命力量迅速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直捣并攻克堡垒,最后夺取政权;第二种则可以称之为“阵地战”,即采取文化攻势形式的持久的堑壕战。[18]
20世纪60年代末由葛兰西著作的重新发现所引发的“葛兰西热”,对当代的女权主义、福科的分析以及后现代主义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就国家理论而言,普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成了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