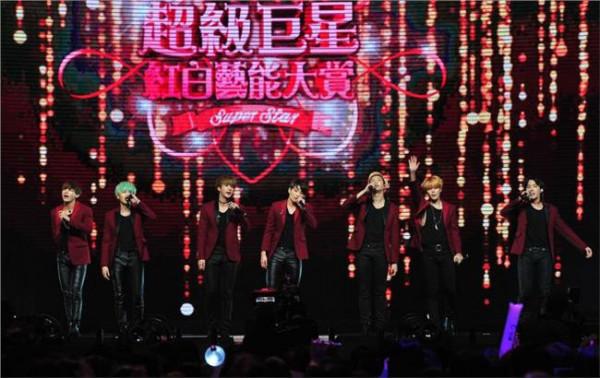权延赤的父亲 沉寂许久的作家权延赤
权延赤曾经声名大噪,而一部由权延赤小说《酒神》改编的、全国各电视台轮番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狼毒花》却没能使销声匿迹的权延赤再度声名雀起。尽管权延赤的大名已没了“惊鸿”的能量,但在电视剧片头出现权延赤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就免不了偶尔“一瞥”。“权延赤”顾名思义:延安孕育,赤峰出生。弹指间该是已过花甲之年。
权延赤生命盛年数十部作品中有一两部引起了轰动。尽管如此,这么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权延赤作品的评说并不完全一致,褒贬不一。
那几年,权延赤成了“大腕”,成了“名人”,只要他去参加什么活动,准被排在“在座的有”之行列。但凡有资格上台讲话的人,大都送给他一堆不算肉麻却也叫我们这些“闲杂人等”听了起鸡皮疙瘩的恭维话。下了场,权延赤便会被崇拜他的文坛小生、才女、媒体记者们东拉西扯地当“道具”拍照片、签字留念。
殊不知,权延赤并不在意“领导”们的评价,更记不得谁与他合了影,他给谁签了名。因为前一场酒的作用还在,他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被酒浸泡得眼朦胧,心朦胧,情也朦胧,大脑空空,荣辱皆忘。
我是在二十几年前先看了他的作品后才认识权延赤这个人的。读他的作品时,我是那么佩服他,他的气魄和他生动、鲜活的语言,以及飞扬跋扈的文字。看他喝酒,觉得他特汉子。酒场逢对手,从不玩虚掺假,因此是逢喝必醉,酒醒便写,写罢再喝,一派豪放文人的架式,一种无拘无束的活法。
权延赤热情豪爽,在部队虽一辈子当“战士”,却交了许多朋友。他衡量朋友的第一标准就是——你敢豁出命来喝酒吗?喝,便是友,他会诚心诚意地待你;不喝,你的名字便会随风而去,就这么简单。想和他成为朋友吗——请豪饮!这么一来二去,年复一年,权延赤像块吸足了酒的海绵,再往里倒一两酒都如同倒进一斤酒的效果,只要沾酒,就足以使他酒水四溢,翻江倒海。
权延赤出名后,“朋友”的数量剧增,酒局越来越密,绯闻自然也越传越邪乎。对此,他不以为然,依然用那沙哑却不失“响亮”的大嗓门在公众场合声明:“随便说,说有多桃色就有多桃色,你们不说我自己说。”
其实,权延赤为人坦荡、直率,很多“绯闻”都是他自己“吹”出来的,真有点像《狼毒花》里描写的男一号常发叔。他明明是夸大其辞地谈他的初恋,不厌其烦地谈他的婚姻,谈他的爱妻,谈他的娇女,人们却当“段子”听。一个家庭所经历坎坷和磨难,从他嘴里说出来便充满了戏剧性,令人喷饭。
客观地说,权延赤写得真比说得好。他写《我与妻子》一文深情款款满目沧桑,一个没有几十年婚姻的人是很难写出那种感受的。从他《我与女儿》这篇信手拈来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他十足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人们凭经验认为“家事宁万事宁”。这话在权延赤身上并没应验:家倒是安宁无事,其余万事均不得宁之。随着他作品的不断问世,随着他“功成名就”地“下海”,法院的“传票”就没完没了地接踵而来,他不仅成了当年中国文坛官司最多的一位作家,也成了深入海底至今没能上岸的作家。
那些涉及法律的,法律尚且难于判明的,法律边缘的,法律以外的,常常闹得他焦头烂额难于自制。权延赤说,我决不畏惧法律,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对付那漫长、拖沓、消耗性的“战事”。他常说“我要想当原告,有的是官司可打。”权延赤也确实挺大度,吃亏上当的事没少干,坑他害他的人也遇到不少,但他总是借酒消愁,自说自话,从不真正与人为敌。
权延赤曾是职业军人,部队两次授予他二等功臣称号,他说死说活给“辞”了;他还曾是专事写作的“创作员”,组织上根据他的贡献,决定给他增加100元“创作费”,他一次也没领过。权延赤真的是当了一辈子兵,因此他“复员”了,而不是“转业”。
这里的缘由他笑话似地说给大伙儿听过,因为他自己都不在乎,朋友们也就跟着当笑话一听了之。如今他经商也有十几个年头儿了,依着他的性格和为人推断,他一准赔多赚少,只顾关照朋友了。今年偶然在广州见到了权延赤,看上去没啥新面貌,倒是有了新气象:喝水和喝酒反应一样,喝啤酒和喝白酒一样,喝不喝一样。
我问他,到“海”里扑腾了十几年,用生命去体验的时间和成本都到了极致,啥时重返文坛呢?他哈哈大笑。他的样子让我一下子又想起《狼毒花》里的常发叔,想到他笔下的一批英雄将士。顿时觉得他挺可爱,顿时觉得他在文坛曾独领风骚挺了不起,顿时觉得英雄决战岂止在战场呢?
多少年前,权延赤用笔,撩去了笔下人物的面纱,同时也把包裹自己的衣衫撕扯得分寸全无,像个立体透明人一样被朋友们敬着爱着追捧着并数落着。其实,他只不过是在众多以摇笔杆为生计的人中的普通文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甘于承认只会写字而改行经商的文人。
权延赤个子很高,但并不属高大威猛型,如果他站在那里不说话,似乎可以用眉清目秀略带儒雅来形容他的外表。有人说他长得像“林彪”,有人说他像“阿Q”,我说他像他笔下的常发叔。若仔细琢磨他那副尊容:一身醉态,一腔激情,一脸天真。谁也不像,就像他自己。(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