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陶渊明 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
汉人何休在《公羊传解诂》中指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① 这句话在后代影响很大,人们都把它理解成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传统的经典阐释,也视为对古代民间歌谣的发生背景的合理说明。
如果从逻辑上来推理,既然古人早就把“诗言志”确立为诗歌的开山纲领②,既然古人早就认识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③,何休所说的“饥者歌其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一条古典诗学原理。然而我们把《诗经》以及汉乐府等先秦两汉的古典诗歌作品检索一过,却发现“饥者歌其食”的现象非常稀少,由“饥者歌其食”生发的作品数量与“劳者歌其事”之诗相比,简直少得不成比例。
先看先秦诗歌的情形。
《诗经》的《国风》虽然作者不明,但其中无疑包含着较多的民歌。可是这些民歌虽然不乏涉及人民生活贫苦的内容,却很少有“饥者歌其食”的描写。《秦风·权舆》云:“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前人解此诗为国君薄待贤者,至于其生活质量下降④。
虽说其主人公并非劳苦人民,但总是个“饥者”,此诗勉强算得上是“饥者歌其食”的作品。不过这样的作品在《诗经》中甚为罕见,它对“其食”的描写也过于简单、抽象,缺乏审美价值。
在《诗经》中咏及饮食且描写得稍为具体、生动的作品,并不属于“饥者歌其食”的范围。例如《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朋酒斯飨,日杀羔羊。”《小序》解曰:“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
”⑤ 意谓此诗是叙述周室兴起的过程的,故诗中所写的饮食当为周室贵族所享用。现代学者也解此诗为“记载农夫遭受剥削的长诗……收获是被贵族们享用着”⑥。所以此诗中详细描写的饮食都与“饥者”无关。
与此类似的如《小雅·伐木》中的“陈馈八簋,既有肥牡”,《小雅·鱼丽》中的“鱼丽于罶,鲂鲤。君子有酒,多且旨”,《小雅·瓠叶》中的“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等,也都是描写贵族生活场景中的饮食。
这种情形在《楚辞》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例如《招魂》中描写宴饮的一段文字:“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敉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几乎把当时的珍贵食品尽行写入,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分明是在楚国王室宴饮盛况的基础上所作的夸张描写。
再看汉代诗歌的情况。
汉乐府中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照理说不会缺乏“饥者歌其食”的内容,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东门行》中写主人公的穷困之状:“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又写其妻之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这倒是与“饥者歌其食”有关,但是过于简单,无甚深意。
汉乐府中描写饥者之食最细致的作品首推《十五从军征》,诗中写一位从军数十年的士兵返乡之后的生活情景:“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不但写出了生活的简陋艰辛,而且成功地烘托了孤苦无依的凄凉晚景,感人至深。然而诗中的食物自身仅是语焉不详的“饭”和“羹”,而且这样的作品在汉乐府中也是寥若晨星。与先秦的情形相似,汉代文学中比较细致的食物描写也都与贵族的生活有关,而且不见于诗歌而见于辞赋。
例如枚乘《七发》中关于饮食的一段:“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搏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
熊蹯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与上文所引的《招魂》如出一辙。《七发》本是虚拟吴客游说楚太子的夸饰之辞,所写的当是汉代楚国贵族的饮食,它与《招魂》相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情形似乎与何休所说的“饥者歌其食”大相径庭,那么为什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在诗歌中基本缺席?我猜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贫苦百姓来说,他们虽然因缺乏食物而对其非常关心,但是当他们在诗歌中说到食物时,却没有什么可以具体描写的内容。
既然身为“饥者”,能够到口的食物当然数量稀少、品种单调,而且粗陋丑恶,毫无审美价值。这样,即使他们想在诗歌中说说“其食”,又有多少话可说呢?即使是《十五从军征》那样生动真切的作品,诗中所写的食物仅是用野谷子煮成的“饭”和用野菜做成的“羹”,这么粗陋的饭食,其自身又有什么值得描写的呢?不但如此,身为“饥者”的穷人即使展开想象的翅膀,也难以写出什么美好的食物来,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此类生活经验。
那么,为什么在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歌中也同样缺乏有关食物的佳作呢?他们享用的食物可是非常丰富呀!这可能与诗歌自身的文体特征有关。一般说来,古典诗歌是以简洁为趣尚的。所以铺陈排比地描绘丰盛的食物,只适合于辞赋类作品,上文所举的《招魂》与《七发》就是显例。
如果要以之入诗,就只能用简约的写法。试看《诗经》中的两个例子:《小雅·正月》云:“彼有旨酒,又有嘉肴。”《小雅·车舝》云:“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一正一反,都是说丰盛的饮食,却只有“旨酒”和“嘉肴”两个词汇。
更主要的原因是,古典诗歌的根本性质是抒情而不是体物,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指出:“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虽然今人或以为“陆机关于诗赋的‘缘情’、‘体物’的论述,我们应当看作是一种互文见义的说法”⑦,但两种文体的功能毕竟是各有侧重的。
也就是说,体物主要是赋的功能,而诗歌的特质则在于以情动人,正如钟嵘所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虽然“春风春鸟”等也都是“物”,但它们所以能入诗,仍有待于“感诸诗者”的性质。
至于“楚臣去境”云云,显然都属于“缘情”或“言志”的范畴。“饥者歌其食”是饥饿这种生活境况激发创作诗歌的冲动,虽然其中的“食”是一种“物”,其整个创作过程的性质仍是“缘情”。
所以,在诗歌中咏及食物,并不能产生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只有描写“饥者”与“食”的关系的作品,就像汉乐府中的《十五从军征》那样,才能达到读之恻然心动的境界。
所以这种效果显然不是贵族生活中的饮食主题所能具有的,即使酒池肉林或长夜之饮,也不可能构成动人的诗歌内容。在萧统所编的《文选》的诗歌类别中,专设“公?”一类,收曹植、王粲等人的同类诗作十四首。
“公?”就是王公贵人举行的宴会,宴席上的食物肯定十分丰富,但是这些以“公?”为题的作品却很少咏及食物。在曹植、王粲、刘桢三人的同题诗中,曹、刘二诗一字未及食物,仅有王诗中有“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二句写到饮食,像《诗经》一样仅用“嘉肴”、“旨酒”两个抽象的词汇来概括丰盛无比的酒菜,在全诗中根本不算警策。
由此可见,饮食题材在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歌中也是无足轻重的。
既然“饥者歌其食”和贵族的丰盛宴席都不能生发出多少好诗,那么饮食类题材在诗歌中还能不能有所发展呢?按逻辑来推理,能够寄托这种发展前景的诗人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他既非赤贫的“饥者”,也非富贵之人;二、他热爱普通的日常生活,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在古典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决非富贵之人,但也不是经常挨饿的“饥者”。陶渊明曾写过《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有人说这是“借漂母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门事也”⑧。但是陶诗中咏及衣食不周的地方甚多,可证他确是深知饥饿的滋味的。
不过饥寒交迫并不是陶渊明的生活常态,因为他毕竟出身仕宦家庭,自身也曾几度出仕,退隐后家中仍有童仆,平时又经常饮酒,所以他的生活虽然穷困,但尚未到赤贫的程度。于是,在陶渊明的诗歌中,饮食便具有了新的审美意义。
陶诗中最引人注目的饮食当然是酒,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他说到酒时总是笔带感情,如“春醪解饥劬”(《和刘柴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携幼入室,有酒盈尊”(《归去来兮辞》),莫不如此。
陶渊明也常在诗文中说到其他食物,主要是粮食与蔬菜,前者如“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十二首》之八),后者如“好味止园葵”(《止酒》)、“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之三),有时也两者并咏:“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二首》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在吟咏这些普通的食物时同样笔带感情,这说明陶渊明真心热爱平凡的生活,从而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饮食也满心喜爱。当陶渊明吟咏日常生活的情趣时,普普通通的饮食也便具有特别的滋味,请看下例: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此诗为陶诗名篇,后人赞赏不已。
南宋陆游最喜首二句:“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⑨ 清初王夫之则最喜“微雨”二句:“‘微雨从东来’二句,不但兴会佳绝,安顿尤好。”⑩ 其实此诗全篇皆好,“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二句也堪称从古以来抒情意味最为浓郁的题咏饮食的佳句。
诗人所咏的饮食是极其普通的家酿和园蔬,但诗人是怀着愉悦的心情和珍爱的态度来吟咏它们的,它们不但是安宁的温饱生活的象征,而且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饥者歌其食”的结果是粗陋悲惨而令人不悦,贵族文学中对饮食的铺张扬厉写法的结果是华侈奢靡而使人厌恶,那么陶诗营构了一个全新的温馨可喜的饮食类意象。就饮食这种特殊题材在诗歌中的地位来说,陶诗所达到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唐代,随着诗歌高潮的到来,诗人观察生活的视野日趋广阔,他们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意味的能力日趋高强,饮食题材也较多地受到诗人的关注。王维、孟浩然等人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传统,照理说应该对陶诗吟咏饮食的写法有所因袭,不过王维半官半隐的身份使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带着士大夫的雅致情趣,其诗中的饮食也随之雅化,如“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游化感寺》)、“松下清斋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等,颇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
孟浩然倒是货真价实的隐士,但是他的诗风尚清虚而不尚质实,所以诗中对饮食的描写颇有虚拟化的倾向,比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裴司士员司户见寻》)、“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过故人庄》),一写有客来访,一写做客农家,诗中的食物却是一成不变的“鸡黍”,几乎成为待客食品的习用语了。
在盛唐的大诗人中,李白在描写豪奢生活涉及饮食时也多为虚写,例如“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行路难三首》之一)、“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梁园吟》)等,而回忆他在长安任翰林待诏时的豪华宴会则干脆只用一句“象床绮席黄金盘”(《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读者连黄金盘中盛着什么食物都不得而知。
倒是他在浪迹江湖时所咏及的粗粝食物反而较具审美意味:“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菰米饭本是田家所食的普通食物,但经李白一咏,则格外显得晶莹皎洁,与月光下的洁白瓷盘交相辉映,构成一个极其美丽的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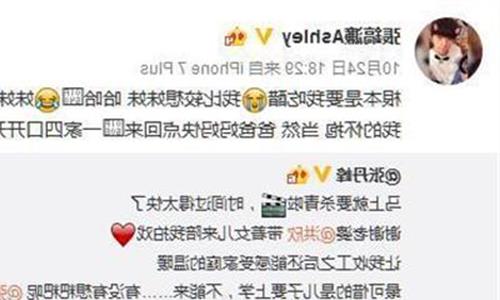





![《古文鉴赏辞典》电子书[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b/fc/bfc1cc73ed6902ee1aae25f3da27d3a1_thumb.jpg)









